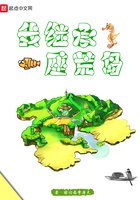彭城,太守府,朱成瑞睁大眼睛,不可置信地问道:“你说什么,路却他跑了?”
他他...他娘的抛下三百万两的巨债跑了?朱成瑞觉得心快跳出嗓子眼,他额头青筋猛烈跳动着。
白旗低头道:“路公子留下手信,托小人交给大人。”
朱成瑞面色青紫地展开手信,“舅舅亲启,孝和已归长安,望舅舅保重身体,勿念。另,静待他人送钱上门。”看完手信,他觉得自己要晕过去了,他已经预见自己凄凄惨惨的牢狱生涯,原因就是欠了三百万两官银。
就在朱成瑞苦恼之际,忽然来了好几批人马,他们都是正当年的小伙子,精力充沛,牵着装满乌木箱子的马车来到彭城太守的府邸门前求见彭城守。朱成瑞自然听到外面热闹的声响,立刻出来一看。
只见四五十位领头者一齐道:“我等奉主人之命,还钱而至。”
“还钱?”朱成瑞有些惊讶,想到了路却的信。那些领头者已经把马车上的箱子搬下来,他们道:“路公子借钱救济,现我们已经渡过难关,还钱而至,多谢路公子。”
朱成瑞命人把那些箱子搬了进去,总共五十八箱,来自四十五批不同地方的人马,再打开箱子一看,里面是亮晃晃的黄白之物。朱成瑞立刻让人清算箱子里的银两。
朱成瑞手里还拿着路却薄薄的信,问道:“是不是三百万银两?”
“不是。”计曹掾史摇头。
“不是?”朱成瑞惊道,心想路却那混小子私吞了一些?
计曹掾史眼中也是惊讶,他道:“是三百十一万两。”
计曹也是掌管郡城财政的,平日也算处变不惊了的,但他还是很惊讶,他是第二次见到这么大的银两往来,第一次是朱大人的外甥来从财库里提走了三百万官银。
朱成瑞有些想笑,又有些气...这竟然还多了十一万两。他提起毛笔,想写封信寄往长安,想训斥路却一顿,但真落笔时,心中一叹,又变成了一封普通家书——“今年将归,甚念长安。”
五墟。
南岁引虽然惊才绝艳,但在伤未好之前就拔剑,使得她的伤又重了许多。
几乎每时每刻,她体内的灵气紊乱,都会有新的伤痕出现在她的身上,看起来天道想要折腾死这个病患。
王涂在一边提心吊胆地看着,一面想着她到底会不会死,一面想着她要是死了它应该为她挖一个多大的坟。挖的大了不好,容易被盗:挖的小了也不好,容易消失。
就在它这么没良心地想着的时候,南岁引慢慢地把手按着地,已经露出骨血的手在乌黑的地面映衬下显得格外恐怖,只有淋漓的坚硬撑着她没有倒下。
她勉力想站起来,但还是倒了下去。
重重的一跤。
她好像睡了一觉,但意识却仿佛还是清醒的,她还记得埋骨荒野的感觉,所有的一切都离她有些遥远,山是沉默无言的。在地下,她听到一株草破开地面的声音,带着无数新生的喜悦。
心里那粒仿佛枯寂的草籽突然开始萌动。
南岁引的眼睛落在乌黑的泥土上,哪怕天劫已经过去,这片土地再也不会有任何植物能够生长了。这是死亡的气息。
她放开对体内灵气的控制。
灵气疯狂无情地肆虐一通,使得人的脸色苍白如雪,三天后才终于散去。
灵气终于散去后,南岁引睫毛微微一动,哪怕是遭受这样的痛苦后,她眼里还是冰雪般的冷凝。她的痛苦好像对她而言不再是痛苦,她只想要活。
她耐心很好。
所以,她开始重塑道基。
既然道基尽毁,那就重塑一个道基。
这一次,她在心中的那座山上随意埋下的草籽要萌芽。
天下没有修士能说明白重塑道基这个过程的痛苦与艰辛,因为从未有人重塑道基。人们并不相信道基能被重塑,道基在他们脑海中就是玉石,打断了,就是断了。不会再长出来的。
南岁引不相信人们的话。既然人病了会好,树黄了还会再青,那么道基毁了也可以重塑。她在山上看人间,虽然觉得无趣,但她也知道人世间的很多道理。有的道理,她不信不尊。有的道理,她知道却不守。她只守她自己愿意做的道理。
南岁引看着自己的道基再长出来。这个过程的确很像断骨重长。那骨头不是旧的骨头,它是带着昔日的旧影却又有新的形状,它从她的道心上长出来,从痛苦与坚守中挣扎着出来,新骨与她的身体不是很协调,摩擦配合了一天一夜,还是不合。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放弃新的道基,要么放弃旧的形体。南岁引没有思考地就在磨合的关键时刻,很自然放弃旧的形体。
身体除了那块新的道基都被重塑。
这一次是真正意义上的重头再来。
南岁引休整了十一天后,终于勉强能够行走。王涂因着它在南岁引昏迷期间干的蠢事而有些尴尬,十分难得地主动提出要帮忙:“其实老夫可以现出原形,驮着你走。”
“不用,我喜欢自己走。”她一直都是个自信独立的人。
“老夫一天前去外边逛了一遍,很多人找你,一是因为圣人令,二是因为你杀了白眉王,他为人豪爽,追随他的英豪众多,他们要找你复仇。”王涂说着,瞥了眼南岁引,它觉得应该在当时就把那四个逃走的白眉王手下杀死,但是南岁引的道理很奇怪。
欠了的要还回去,没有欠的就用不着还。南岁引道。所以,他们放走了那四个人。
现在,白眉王死了,那四个人把消息传开,他们又得撞上为白眉王复仇的众人。
天下成名最快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名人,杀了他。有名的程度看死的那个人多有名。白眉王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人,几乎天下所有说书人都讲过他那双白眉。南岁引没想成名,她只杀人。
她杀了一个名人,名动天下的白眉王。
自此,那日后,南岁引名动天下。
于是,有许多人想来杀她。
王涂一点都不想被那么多人追杀。它语气深深,非常遗憾:“我们应该在那时就把那四人杀死的。”
南岁引走的很慢,像是神游天外,但她一直都在听。
南岁引道:“他们那时没有动手,所以不杀。动手,就杀。”南岁引面对这种恩怨杀戮总能理的很直白,无论是谁要杀人,都要做好被反杀的准备。
天下修士是,她也是。只不过,有些时候,会像蚂蚁一样杀不光。
王涂并不信她这种不符合现实的话,心道:“这老怪物当天下人都和她一样吗,天下多的是没事找事,滥杀无辜的人,要不是她有自保之力,那她也是被杀死了也无人知晓的倒霉蛋.....”
南岁引知道王涂和其他人这种想法,但是她不和别人想法一样,也不在乎别人的想法。
他们行了不久,就迎面撞上了寻找他们的人。但很奇怪的,他们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他们像是根本没有看见南岁引一样,与她擦身而过。
王涂惊异地看着他们继续面色着急地在五墟四处找人。
而南岁引则是满不在乎地慢行。她步伐还是简单而坚定,但方向却有些看不透,因为她也不知道她该去哪里。回玄门吗?可是出清平那时的想法到现在已经变了,她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回去,因为山就在那里。她只是并不想这么快回去,但她也不会逃避,毕竟九峰依然青。
“我本可以干干净净地斩断一切,现在却是到这种腻烦的地步。”她心想。
南岁引走的慢,但她耐心好,走的久也不会说半句累。王涂则是受不住了,你不能要求这只良心全无,脸皮极厚的王八蛋陷入与南岁引一样的少年忧虑,它道:“不走了不走了,再走老夫的腿要断了。”
南岁引停下,看着在地上撒泼的老甲鱼,神色极淡。
王涂被她一眼看的心里有些慌,这老怪物渡劫后它觉得她更加危险了,总觉得一个不小心她会入魔,但面上还是很强硬地仗着年纪欺负她:“你看你是人,老夫是龟,你走一步老夫得爬三步,你不累老夫累啊。”
“离开五墟?”
“离开,离开!”王涂高兴叫道,五墟已然到手,但有圣人等着把它们一锅端,现在当然得赶紧溜。等避过风头,再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走这个洞天,这才是聪明人的做法。
南岁引不在意去留,但王涂有意,本着养王八的初始心态,本着自己见他人养灵兽的往事,有些时候是需要给灵兽顺毛。王涂没毛,顺壳也行。
南岁引便拿出进入五墟前刺史们给的五墟铭牌,打入一道灵气,身形一闪,他们已经离开五墟。
留下五墟内的其他修士是找人找疯魔,结果连根毛也没看见,气的牙疼。
彭城,未时,日头正盛,接引者们的府邸里的黄鹂们是迈着高贵的小脚,啾啾自己的羽毛,再是偶尔赏个脸给大家来一段。当然更多时候,它们是很少出声的,这里可是接引者的府邸,一只鸟也该有一只鸟要守的章程,它何时鸣叫,鸣叫多少次,鸣叫多响亮,都有章程。
鸟鸣有章程,接引者们的章程自然更多,更怪。朱成瑞的外甥临走前,远远瞥见接引者们,心底嗤道:“那么复杂完备的章程结果还是给别人钻了空子。”
朱成瑞内心也是同样的想法,他对着吃里扒外的接引者自然不会有好脸色,但又不能不笑脸迎上去,接引者里面的水非常深,人们以为这人毫无背景,说不定就是九姓的某支后裔。
所有接引者的背后都沾着点其他势力的影子。
如果有一个接引者,别人查了他祖宗十八代,还是没查出背后的影子,身份干净的像是白雪。
那只有一个可能,他背后的势力绝不是普通的势力,而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远古传承。
从来没有人能查清接引者里面错综复杂、勾心斗角的线头。接引者们之间就是最为叵测的江湖,最为险恶的人心,阴谋最先发生的苗头在接引者的名字和调任的公文里,血腥恐怖的屠戮也在接引者的公文里埋下伏笔。因此,他们的双耳大多是聋的,双眼大多是瞎的,但他们看上去与凡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能听到温声细语的清唱,听不见人头落地的声音,他们看的见春和日暖的美景,却看不见那些人的真面目。
他们的章程很多,代代传下来如何做接引者的秘诀却只有一条:做好本职,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看的不看。
南岁引从五墟出来了吗?你们有看见过南岁引养的那只无耻灵兽吗?
接引者摇摇头,他们什么都没见过,什么都没听到。
就和从前千千万万次一样,他们这天的眼睛还是瞎的,耳朵还是聋的。
但是,他们没有为南岁引开启通天台。
他们开启通天台的时候不能是瞎子和聋子,除非他们想死。
接引者们目送南岁引离开。
“她看上去很弱小。”一个接引者说,他在考虑把她受伤的消息透露出去。
“我刚才在想我该怎么出手,但我发现,我无论怎么出手,哪个时机出手,她都好像能接住我的攻击。”这种感觉只有在那些从血海尸骨里活下来的人身上才会有。他们对袭击的预判和防备成为同五感一样的感觉。
“仿佛没有什么能阻挠她,打败她。”另外一位接引者说。他想,她注定名动天下。
王涂离开接引者的官邸后,骂道他们的嘴脸真是太丑陋了,竟然害怕圣人而不愿为它开启通天台,它喃喃自语:“圣人怎么了,要是以前,老夫一拳头下去都是坐骑.....”
但是王涂也不想徒步行走在亿万山河间,它望向南岁引,希望老怪物给个主意。南岁引仰头看着云彩,似乎对她而言云彩比在接引者们那里受到的冷遇更值得在意,她看了良久后才道:“还有一个接引者。”
“我们不是找过所有的接引者了吗?”王涂奇怪。
南岁引神色疏淡地笑起来:“每一位刺史都有一位独立接引者。那位接引者只为刺史开启通天台。”她并不是很开心,但她觉得这种时候笑一下会更好一些,她在清平镇上的时候金老板告诉她。“有的时候,冷笑狂笑淡笑都比苦着脸令别人高兴要更好。”她不常大笑,不常狂笑,因此她笑起来就只有疏淡和冷意,独立世俗的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