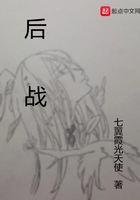年底里最忙,要提早和贺兰国那边的商贾谈好来年开春的大单,南初让她好生看家,自己带着人到贺兰明江去走商了。
没人说教,落得耳根清净,但她也没什么好心情。
主要是因为许乔。
她喜欢许乔吗?许乔挺好,可是许家派人来说媒的时候,她并没有感觉到高兴,只是觉得这是一场普通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能说明她不再是孩子了。
许乔喜欢自己么?他说他喜欢。可是她想不明白为什么。如果说她一定要嫁给他,她只觉得自己像被绑在一块浮冰,觉得惶恐,觉得窒息。
或许恰如南初说的那般,她不懂爱。
那嫁给许乔,她就能明白吗?
想来世间最精明的人也给不了她答案。
今日除夕夜本应该阖家团圆,但南初人在贺兰未归家,梅漪闲里遣散了下人,独自待在二层阁楼。
倚望窗扉外,城下人间烟火醇重像蒸笼上的一碗茶,烟花隔岸绚烂,照暖姑娘的轮廓。
刹那芳华辉映,她觉得很美,但过于无趣。
瞳眸里的光忽然闪动,梅漪想起来什么,她蹲下来,从桌底下拖出一个蒙尘已久的木匣,取出来一样东西,是一只手掌大小的飞鸢。
这只榫卯飞鸢,是南初为自己做的。
她靠在窗前,和儿时一样,她只用取掉飞鸢身上的一个部件,那飞鸢就像被赋予了生命,伴随着阵阵雀子喳喳声,它飞出窗外在庭上久久盘旋,好一阵子才飞进窗里来,停在梅漪的手心。
她笑得眉眼弯弯,将飞鸢又送出窗外,仰望着那飞鸢,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只是这一趟有些意外,那飞鸢刚盘旋了两圈,忽然失去了平衡,它的翅膀开始乱扑腾,笔直地滑翔下坠,竟飞到了院墙外去。
耳边烟火声迸开,她好像听到有人吃痛的声音。
梅漪心里咯噔一下,这飞鸢是黄竹做的,有些分量,从阁楼飞下来,要真砸到人就难过了。
都怪她,那飞鸢的年龄已经很大了,她还糟蹋它。
“抱歉!”她朝墙外喊。
她转身下阁楼,过中庭桥廊,绕正门影壁,到了后街上便四处搜寻。
青石板上没有飞鸢落下的踪迹,来往行人也神色如常。
好像那飞鸢没来过一样。
梅漪疑惑着,身后忽然有声音传来:“姑娘,你在找这个吗?”
她应声回头,与人四目相对。
那是一双好看的桃花眉眼,在烟火的照耀下仿佛盈满了迷离水光,清澈见底。一条发辫铰着银线交织,顺着左耳垂下,披在一身墨沉锦缎上点缀着朵朵银花。
梅漪也是个二八有一的姑娘了,这样被人直视着,她心里不好意思,脚跟不自觉微微后退。
“呃对…是我的…”梅漪说,“那个…砸到你了吗?”
他没有回答,凑近了看着她,将手中飞鸢还给了梅漪。
“我叫贺月。”他说。
“啊?”
“你的名字呢?”
“呃…梅漪。”
墙根下栽种了梅树,腊月尾巴里殷红朵朵托雪盛开,呼吸间都盈满了幽香。
“这个飞鸢砸到你了吗?”梅漪将飞鸢收入袖中,又看着他。
“没有。”贺月的神色很坦然。
“那就好,谢谢你帮我捡了飞鸢。”梅漪又抱拳作揖,扬眉一笑。
没有理由再待,她转身欲走。
刚走出几步,身后传来轻哼。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梅漪顿住,脸色有些复杂。
怎么说呢,她觉得杀人灭口可能有点过,但也不是不可以。
她扭过头,看贺月在那儿笑。
“欸,这个还给你!”贺月递出来一样东西。
梅漪这时才看见他手里一个粉色酒壶,一只白白的软兔子趴在瓶口。
她认出来是她的酒壶,原来落他那儿了。
想起城关露台上剁碎桩子的那只飞刀,梅漪心里有些犹豫,不是很想靠近。
“想啥呢。”贺月走过来,往她手里塞酒壶。
只是梅漪手里刚接过,便被贺月一把拽住了袖子往回府的方向背道而驰。
“你干啥!”梅漪试图从他手里拽回自己的袖子。
“那天吓到你了?我请你喝酒赔罪啊!”贺月回头朝她笑。
这一笑伴着街市里的灯影洒在身上,贺月的一双眼睛里清澈无辜,让谁看了都想要相信。
就好像养了很久的猫对你弯起了眉眼。
梅漪忽然一笑,觉得有些意思,便任凭他拽着自己袖子朝人潮走去。
-
城关露台上,冷风狂躁一茬接着一茬,梅漪只觉得自己人都要没了。
说请她喝酒赔罪的,把她请到露台上喝西北风来了。
“贺公子。”梅漪喊他,“其实你要是没带银子,可以去我家酒楼里赊账的。”
贺月正坐在露台上看着从城下升起的烟火,他转过身来。
“玩过烟花没?”
“玩过啊。”梅漪说。
“怎个玩法?”
“就现在这样,点了火,让它飞到空中,然后它自己炸啊。”梅漪指了指正盛的空中烟火。
“那哪叫玩。”贺月一笑,递给她一根细长的彩杆:“拿着。”
梅漪接过。
贺月拿出了火折子,将她手里那根细彩杆点燃,火苗冒出尖来停留短暂一瞬便熄灭了。
一片黑暗。
什么鬼。
突然,梅漪的眼里一片明亮,是彩杆的顶端有闪烁的星子喷涌,风流云散间光芒照亮了梅漪,就像一捧手心里的太阳。
“这像火树银花。”梅漪笑着挥舞起彩杆来,“不过可以拿在手上。”
她回头,见贺月手里也挥舞起了一朵小小的火树银花。
“你还有呢!”
“多。”
手中一根燃完,贺月将剩的一大把都塞给了梅漪,自己不知何时借着光芒拿出了一壶酒斟上了两杯。
贺月递了过来:“尝尝我自己家酿的酒?”
“不喝,太冷了。”梅漪将一手捂在星火上方取暖。
贺月嘴角一扬,将酒杯凑了过去,那燃烧的星子溅进酒盏里,霎时间似燎原般的蓝幽火焰,燃烧在酒杯里。
梅漪见此,竟笑起来:“你还是个行家啊。”
常见到小案洪炉温酒的,这般直接点燃的,她过去只在古书里见过。
贺月向梅漪举杯:“梅姑娘,这杯,算我向你赔不是了。”
他竟将其一饮而尽,梅漪来不及阻止。
“嘴还好吧?”她哭笑不得看着他。
“你尝尝?”他一边擦嘴,一边示意她将酒点燃,“不凉。”
梅漪有胆量去尝试新奇,她将星火溅进了自己的酒盏里,看着那一窜而起的火焰,虽说杜康古籍里有记载燃酒一说,但她没尝过,心里还有些忐忑。
她看了看贺月,他向她点点头,于是一咬牙,仰头便尽数将其饮尽。
“如何。”贺月一边玩起火星子来,一边问她。
温吞并不烫嘴,但是这味道,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有软绵的口感却泛着沉重的苦味。
梅漪拧起了眉,脸色忽青忽白:“这酒有毒。”
贺月似笑非笑的,像是在等待欣赏她的表情。
忽然,梅漪嘴里的苦味消散,仿佛从胸腔里漫上来说不出名的甘醇气息,像从仙境里落下来的甘露滴落进咸咸的海浪里,一波一波拍打着她的感官。
“好酒啊!”她面色灿然,带着一丝惊艳。
两人相视着,各自仰天笑了起来。
欢笑过后,梅漪忽然开口:“贺公子,你从贺兰中原来的吧。”
“我的发音有这么明显吗?”贺月笑。
“可能发音太纯正了吧。”梅漪笑,“我在棠川这么多年,北魏语学的一塌糊涂,但贺兰语倒学的挺好,认人准。”
边境的棠川城紧邻贺兰,已经颇有他国的风貌,北魏本国与贺兰人群混杂,语言交织使用,辨人的标准就靠发音的细微差别。如果是仔细研究过这方面的人,一开口就能知道是哪个地区来的。
这都是南初教她的,是商贾必备的识人之术。
“你对我有所防备吗。”贺月看着她,“观察这么细。”
“有吗?”梅漪笑,“我不觉得。”
“我倒对你有所好奇。”贺月看着她。
梅漪笑:“何德何能?”
“你,有得罪过什么人吗?”
“问这个干嘛?我们家生意人,处事再好,接触的人多了,得罪的人自然也多。”她拢了拢身上的衣裙,“我不会是得罪你了吧?”
“那倒没有。”贺月向她推起酒盏,“梅姑娘,此行我虽有要事在身,但并非冲着你而来,你大可放心。既然咱们同为好酒之人,今日只作这酒友一叙如何。”
“好。”梅漪也举盏向他,“萍水相逢,我便信你,不谈其他。”
他们从火烧酒聊到黄土窑,从棠州杜康聊到桐城丝绸,从东南盛世聊到灭亡雀国,彼此都从心里赞叹对方的见识。
也不见怪,早年梅漪从小和南初走了不少城邦,人间百态就是她的老师。
酒过三旬,交错之间,烟火泯灭,梅漪先声辞别。贺月一并离开送她回到梅府,此后独自一人穿过堂街回到了棠川某个街角的一处院落。
这里是一处寂静的古朴台阁,房里如同行宫,进门就是温泉花池水汽缭绕,薄雾轻纱弥漫。
贺月绕过池畔,穿过梨木隔屏,进到内厢就看见桌案旁等着一人。
这人是他的侍从,白知扬。
“公子。”他递过来一张字条。
贺月接过字条,望着上面的字笑了出来,他将字条给了知扬,上面只有一句话。
——半月。
“陛下给的时间不多啊。”知扬回答。
“这倒无所谓。”贺月抚了抚下巴,“对了,让你查梅姑娘,如何了?”
“一无所获。”知扬答,“公子,容知扬多嘴一句。能做到隐藏得如此干净的,恐怕只有一人,梅姑娘,您最好不要靠得太近。”
贺月明白,知扬说的,正是百官朝堂,龙椅之上,掌握了天下生杀夺予的那一人。
贺月蹙眉,随后面不改色地将那字条揉成了烂泥,扔进了燃烧的灯烛里。
“行吧,那我要歇了。”贺月说,“快走快走。”
“是。”知扬应允。
临出门时,知扬顿住脚步犹豫再三,还是回头唤了贺月一声。
“公子。”
“嗯?”
“你的脑袋…当真砸得不疼吗?要不要请个郎中看看?”
“……”贺月看着他,扯起笑容摇摇头,“不疼,你可以走了。”
“哦,那,属下告退。”
知扬走后,贺月望着窗外,淋着月光,他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那是一枚被损坏的暗钉,边缘呈锯齿,钉身半寸长,有三棱。
这种暗钉,是江湖客中少见的一种武器,极其恶毒,被刺入者会疼痛异常,伤口处会像堤岸的涌水口一样,血水如注,只能以剜肉的方式整体取出。
贺月那日在玉石桩子里取飞刀时,这枚暗钉的棱边已经被飞刀打断,卡在了刀刃上。
这枚暗钉的目标,是梅漪。
“看来这趟确实不简单啊。”他挑了挑眉,将暗钉收于一个小信筒内,随后学了几声鸟叫。
一只夜色下目色赤红的渡鸦俯冲而来,稳稳地停在了窗台上。
他将小信筒绑于渡鸦爪上,抚摸了几下它的背羽,随后拍了拍窗台,那只乌鸦展翅奔向月亮,逐渐拉长模糊,最后消失了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