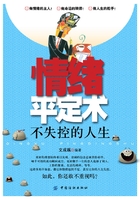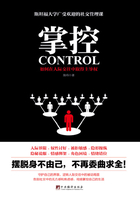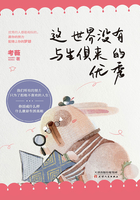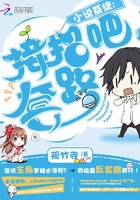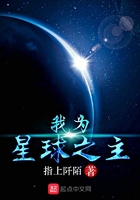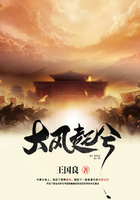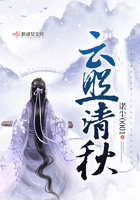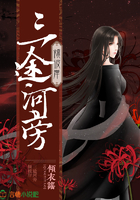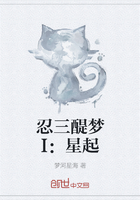拥有一颗平常心,就是最好的处世之道。
解开心结
一般来说,母亲带给我们的是温暖和感动,母爱是最经得起时间冲刷的感情,长年累月地付出却不求任何回报,而子女往往最容易忽视的也是母亲。
鬓角的青丝悄悄变了颜色,细碎的皱纹也慢慢出现在她的面颊上,腰背渐渐弯了下去,脚步越来越迟缓,记忆力也大不如从前,而我们却很少能留意或感知到这些变化,因为她始终不曾停止爱我们。
童年是一段模糊的回忆,也许是太过无忧无虑,所以没有太深的印象,那是蓝天大口大口地吃着白云的天真,是摸爬滚打玩泥巴的幼稚,也是母亲大手牵小手的安稳。
如若问林徽因从她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什么,最突出的便是她的才情、禀赋、个性,而从母亲那里,不是花容月貌,不是温婉淡雅,而是焦躁的脾气和性格。
父亲林长民和母亲何雪媛从未相爱过,也未能联手为她打造一个幸福的童年,相反,他们令她在小小年纪便陷入冰火两重天的境地。
对父亲和母亲,林徽因的感情是复杂的,恨他们,却更爱他们,然而多出来的爱并不能将恨意消融,只能这样僵持着。
梁从诫提起母亲的童年:"她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她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她不争气;她以长姊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她。"
母亲就在她的身边,她却感觉是如此遥远,仿佛隔了千重山、万重水,遥遥相见,要她自己去面对每个孤寂的日夜。
幼小的林徽因随母亲在冷清的后院居住,常常感到悲伤和困惑。
童年留下的阴影,并没有被时间埋没,反而更加根深蒂固,难以动摇。
林徽因的小说《绣绣》讲述了一对遭丈夫、父亲遗弃的母女的故事,妻子也有性格短处,读者不难从小说中绣绣的形象看到林徽因对她母亲的复杂情感。
当我看到她在店里非常熟识地要她的货物了,从容地付出或找入零碎铜元同吊票时,我总是暗暗地佩服她的能干,羡慕她的经验。最使我惊异的则是她妈妈所给我的印象。黄瘦的,那妈妈是个极懦弱无能的女人,因为带着病,她的脾气似乎非常暴躁。种种的事她都指使着绣绣去做,却又无时无刻不咕噜着,教训着她的孩子。
…………
起初我以为绣绣没有爹,不久我就知道原来绣绣的父亲是个很阔绰的人物。他姓徐,人家叫他徐大爷,同当时许多父亲一样,他另有家眷住在别一处的。绣绣同她妈妈母女两人早就寄住在这张家亲戚楼下两小间屋子里,好像被忘记了的孤寡。
…………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爹爹抱过我呢。"绣绣说,她常同我讲点过去的事情。"那时候,我还顶小,很不懂事,就闹着要下地,我想那次我爹一定很不高兴的!"绣绣追悔地感到自己的不好,惋惜着曾经领略过又失落了的一点点父亲的爱。
…………
有一天,天将黑的时候,绣绣说她肚子痛,匆匆跑回家去。到了吃夜饭时候,张家老妈到了我们厨房里说,绣绣那孩子病得很,她妈不会请大夫,急得只坐在床前哭。我家里人听见了就叫老陈妈过去看绣绣,带着一剂什么急救散。我偷偷跟在老陈妈后面,也到绣绣屋子去看她。我看到我的小朋友脸色苍白地在一张木床上呻吟着,屋子在那黑夜小灯光下闷热的暑天里,显得更凌乱不堪。那黄病的妈妈除却交叉着两只手发抖地在床边敲着,不时呼唤绣绣外,也不会为孩子预备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大个子的蚊子咬着孩子的腿同手臂,大粒子汗由孩子额角沁出流到头发旁边。老陈妈慌张前后的转,拍着绣绣的背,又问徐大妈妈--绣绣的妈--要开水,要药锅煎药。我偷机会轻轻溜到绣绣床边叫她,绣绣听到声音还勉强地睁开眼睛看看我作了一个微笑,吃力地低声说,"蚊香,在屋角,劳驾你给点一根。"她显然习惯于母亲的无用。
绣绣的母亲,她的母亲,绣绣的能干,她的能干,绣绣对父爱的渴望,她对父爱的渴望,甚至连绣绣生病的场景都与她幼时生水痘的那一次如出一辙。
从构思到落笔,再到行文成篇,一幕幕往事浮上心头,该怀着怎样的心情去描述绣绣的人生,或者该怎样诉说自己的心绪?
母亲对父亲和姨太太的怨恨,自然而然地牵连到与她同父异母的弟弟林恒身上。他从福建到北平报考清华大学,寄住姐姐家,林徽因待他亲如同胞,何氏却不肯释怀,常常与林恒因为无谓的小事而起纷争。
林徽因致好友费慰梅的信中抱怨:"最近三天我自己的妈妈把我赶进了人间地狱。我并没有夸大其词。头一天我就发现我的妈妈有些没气力。家里弥漫着不祥的气氛,我不得不跟我的同父异母弟弟讲述过去的事,试图维持现有的亲密接触。晚上就寝的时候已精疲力竭,差不多希望我自己死掉或者根本没有降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那早年的争斗对我的伤害是如此持久,它的任何部分只要重现,我就只能沉溺在过去的不幸之中。"
窄小的屋子里,却聚集着天大的怨气,林徽因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关于这对母女关系,哲学家金岳霖写给费正清的信里分析得非常精辟,他这么看何氏:"她属于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却又生活在一个比较现代的家庭中,她在这个家庭中主意很多,也有些能量,可是完全没有正经事可做,她做的只是偶尔落到她手中的事。她自己因为非常非常寂寞,迫切需要与人交谈,她唯一能够与之交流的人就是徽因,但徽因由于全然不了解她的一般观念和感受,几乎不能和她交流。其结果是她和自己的女儿之间除了争吵以外别无接触。她们彼此相爱,但又相互不喜欢。我曾经多次建议她们分开,但从未被接受,现在要分开不大可能。"
当别人家的孩子只知道玩耍的时候,林徽因已经开始学着独立,学着讨长辈的欢心,也学着小心翼翼地避开母亲的痛处。
父亲带她走进的新世界,充满着积极昂扬、明朗欢快,那里有广阔的海洋,乘风破浪的邮轮,有高耸矗立的建筑,有别致可口的下午茶,有精彩绝伦的诗篇,还有侃侃而谈的文人雅士。
母亲带她走进的世界里,则是完全相反的基调,忧郁无奈、灰暗冷寂,那里只有以泪洗面的心酸,永不停止的牢骚和抱怨,除此之外,只剩下小小的一方庭院。
对比太过鲜明,以至于她的爱恨也是这样彻底。
林徽因急躁又心直口快的脾气多半来自她的母亲,而她的成熟稳重也应该"归功"于她不顺心的家庭情况。
林长民49岁因为战乱英年早逝,留下尚未自立的女儿和失宠已久的妻子。
林徽因扛起了母亲的全部,她所有的不满、所有的愤恨,都一股脑儿地融入了林徽因的人生。
明明共处一室,却永远像生活在地球两端。吵起架来也分人,跟梁思成用英语吵,跟保姆用普通话说,跟母亲何雪媛,则一律用福州话。只有母女两人听得懂。
与母亲有关的回忆,总是那么不堪。
1937年,抗战爆发,林徽因的生活开始出现重大转折。为了躲避战乱,一家人四处辗转,最后定居四川李庄。
贫苦、疾病如洪水猛兽,容不得挣扎,只能默默忍受,至于精神上无边无际的孤单寂寞,更是难熬,若不是太阳一直东升西落,她还以为时间停摆了,要不然怎会度日如年,时间在压榨着她的生命,好在她聪慧,可以自娱自乐,勉强从苦中品到一丝甜意。
苦上加苦的是,母亲何雪媛与她的矛盾,二人鲜有平安无事的一天,彼此的冲突总是不断。
林徽因说:"我自己的母亲碰巧是个极其无能又爱管闲事的女人,而且她还是天下最没有耐性的人。刚才这又是为了女佣人。真正的问题在于我妈妈在不该和女佣人生气的时候生气,在不该惯着她的时候惯着她。还有就是过于没有耐性,让女佣人像钟表一样地做好日常工作但又必须告诫她改变我的吩咐,如此等等直到任何人都不能做任何事情。我经常和妈妈争吵,但这完全是傻冒和自找苦吃。"
林徽因与母亲何雪媛,正如新旧两个对立的时代,互不相容,互不理解,或者,就从未想过要去了解什么。
林徽因是新式的女性,她独立、自强、有主见,受过中式西式的双重教育,作为建筑学家著书立说,研究学术,作为文人纵论古今,写诗作文章。
与之交往的人,皆是高级知识分子,大多经历相仿,志同道合,举止得体,谈吐风雅。高朋满座,欢呼雀跃,与朋友们在一起,她有着无限精力。
唯独她的母亲,与周遭的一切是如此格格不入,固执、守旧,永远用悲观厌世的眼光看待一切,打量一切,怀疑一切。林徽因打心底厌恶这样的母亲,更准确来说,是厌恶这样的卑微软弱。
可她最大的失误就在于,她忘了回过身,仔细看一看母亲走过的路,是何等的艰辛曲折。
何雪媛是旧时代的女人,家境富裕却没有接受教育的意识,决定了她的思想都是陈旧落伍的,她的父母也没能将她管教成讨人欢心的媳妇。嫁入林家,在生儿育女上又没能争气,她所受的白眼和冷落,在林徽因还未出生或还未记事起,就已是家常便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