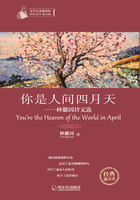一九九一年七月底,妈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衰老了,身体也分崩离析地说垮就垮了。好像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不行了,连个渐进的过程也没有。
而妈可能早有预感。
妈去世后,唐棣学生时代的好友石晓梅对我说,六月份她来看妈的时候,就觉得妈明显地衰老了。妈去拿笔记本,想要记下晓梅的电话。可是刚拿出笔记本就茫然问道:“我拿笔记本干吗?”
晓梅说:“您不是要记我的电话吗?”
就是这次,妈伤感地对晓梅说:“我再也看不见唐棣了。”
晓梅说,以前妈也常说这样的话,但她从未介意,因为上了年纪的人常有如是之说。可是这次,妈再这样说的时候,晓梅觉得她是真的再也看不见唐棣了。
一九八七年妈得黄疸性肝炎以后,我每半年带她做一次B超,检查她的肝、脾、肠、子宫等等,医生每次都说她什么病也没有,一定能活到一百岁。
我虽然不敢奢望妈活到一百岁,我想她活到九十岁、九十五岁,是不成问题的。
我这样盲目地乐观,还可能是因为妈太自强、太不需要我的关照,什么事都自己做。就在一九八七年秋天因为黄疸性肝炎住进医院的前几天,她还自己步行到魏公村口腔医院看牙呢;
就在妈去世前的五六个月,还给我熬中药呢;
就连胡容都看出,一九八四年唐棣走后,妈老了一大截。一九八七年得了黄疸性肝炎后,又明显地老了一截。而我却总是看不到妈的衰老,我对她的关心,是不是连外人都不如?
医生的良好祝愿正中下怀地鼓舞了我、欢愉了我,从而也麻痹了我。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从而忽略了妈毕竟是八十岁的老人,以致我大意失荆州。这可能也是造成妈过早地去世的原因之一。
而且我那时不知为什么愚蠢地认为,那个半年一次的B超检查,就是妈整个健康状况的鉴定,既然做B超的医生说她什么病也没有,她就真是什么问题也没有了。我现在悔之晚矣地悟到,其实B超了解的只是腹腔方面的情况,其于心、肺、脑方面的情况还是一无所知。以我的智力,这本是略动脑筋就能想到的事,然而我却没有想到。
我算是大不孝了。
妈年事渐高以后,我并没有经常守在她的身旁,而是把她丢给小阿姨,或游走异国他乡、或应酬交际、或忙于写作、或去陪伴我的先生……以为有小阿姨在她身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尽管现在我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把妈的一点骨灰带上,可这还有什么用呢?在她老迈力衰,最需要我在她左右的时候,我却把她远远地丢下了。
一九九一年七月初我到黑龙江大庆采油七厂采访,她比我哪一次外出都更想念我。听小阿姨说,她不断地说:“张洁快回来了,张洁快回来了。”好像在为无人照应的自己鼓劲。
可是我在大庆给妈打长途电话,问她各方面情况如何的时候,她老是说:“没事,挺好的。”
有一次妈便结得特别厉害,急迫地念叨着:“张洁要是在就好了,张洁要是在就好了。”而我却远在大庆。
多少年来都以为妈的便结是老年人的通病,后来才知道,那是由于她的脑垂体瘤已经影响到了她的内分泌系统,从而影响了身体各系统的功能的缘故。
妈从不要求我的关照,从不抱怨我在她八十岁的高龄,还总是大撒手地把她丢给小阿姨。
妈终于禁不住对小阿姨这样念叨我,一定是因为身体异常不适,有一种到了紧要关头的直觉。
我在黑龙江呆了不过十几天。一到家就发现,短短十几天里妈就颤颤巍巍地塌了腰。走起路来磕磕绊绊,举步维艰,两只脚掌嚓嚓嚓地磨蹭着地面。裤带也常常忘了系,吊吊地拖垂在衬衣下摆的外面。
妈再不是那个不管什么时候都利利索索的妈了。
可我还是想不到,或不愿意那么想:妈是不行了。我还以为,或我宁愿以为她不过是在懈怠自己。
我说:“妈,您怎么这样走路?好好走。”
或者我在内心深处已模模糊糊地感到,妈也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尽管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妈能活到九十五,但是为什么一见妈那样走路我就心里发紧?我心里越是发紧,却越是轻描淡写地对妈说:“妈,好好走。”
妈就抵赖、隐瞒、解释着,说她脚底疼,或是鞋不合适,或是刚睡起来、刚坐起来,腿脚还没活动开……
也许妈心里早就明白,否则为什么老是找出各种理由来蒙混我,也蒙混她自己——那可怕的结局不可避免地快要到来。
那个时候妈大概就知道她已经不行了。可是她不肯对我说实话,她怕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直是互相搀扶才挣扎过来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组成的这个队列,即将剩下我一个人了。
所以妈的抵赖、隐瞒、解释里,总含着隐隐的歉疚。好像她不但不能再扶我一把,反倒把我一个人丢下,让我独自在这实在没有多少乐趣,甚至苦不堪言的人生里继续跋涉、挣扎,是她对我的一种背弃。
妈的两只眼睛,总是老泪凄凄的。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听信眼科医生的话,妈的视力不好,是因为长了白内障的缘故。而白内障一定要在它的翳子蒙上整个眼睛后才能手术。我们不懂,不懂也没问个明白,为什么十几年过去,妈的视力差不多等于零了,翳子还没有蒙上她的眼睛?
有两次胡容来看妈,恰好我不在家。她应声开门之后竟看不清是胡容,问道:“你找谁呀?”
胡容说:“姥姥,您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妈说:“哎呀,听声音才听出来是你。”
到一九九一年更是出现了重影。妈常说,有时能看见两个我,有时半夜醒来,老看见屋子里有人,或有几个小孩子在乱跑。“刚开始我还挺害怕,后来就习惯了。”妈说。
现在,不用念医学院我也懂了,一个人的眼睛如果查不出别的毛病,视力却越来越差的话,就应该考虑是否是瘤子压迫视神经的缘故。可是却没有一个念医学院的眼科医生想到这一点。说他们是庸医恐怕不够公正,只能说他们没有想到。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位能够研究一下,一个视力已经近乎零的白内障患者,她的翳子还蒙不上整个眼睛,是否和脑子里发生占位性的病变,压迫视神经有关?如果那样,妈早在她还可以承受手术的年龄就做手术的话,我现在还有妈。
妈的左肩更加歪斜了。
妈左肩的歪斜,可能是从一九八九年开始的。那一年五月十三号我去意大利的时候还没有发现,后来我从意大利转往美国,并在一九九〇年二月把她接到美国的时候,突然发现她的左肩歪斜了。不过那时远没有一九九一年夏天歪斜得这么厉害。我说:“妈,您的肩膀怎么歪了?”
妈辩解说:“这是因为右手老拄拐杖的缘故,右肩老撑着,左肩就歪塌下去了。”妈几乎不拄拐杖,拐杖拿在她手里只是心理上的一种依赖,哪里是什么“右肩老是撑着,左肩就歪塌下去”。她只是不肯承认那是衰老的象征。在她辩解的深处,恐怕隐藏着对衰老无力、无奈的忌讳,更主要的是她知道我不愿意她老。
我老是一厢情愿地觉得,妈还是拉扯着我在饥寒交迫、世态炎凉的日子里挣扎、苦斗的母亲。有她在,我永远不会感到无处可去,无所依托。即便是现在,我看上去已经是足够的强大、自立、独立的样子了。只有妈深知,这不过是看上去而已。
妈也一厢情愿地想着她不能老,更不能走。她要是老了、走了,谁还能像她那样呵护我、疼我、安慰我、倾听我……随时准备着把她的一腔热血都倒给我呢?
随时,我的眼前都能现出妈住进医院的前一天,坚持锻炼的样子:手杖依旧横空地握在右手,她常说:“我不拄,我就是拿着它壮壮胆。”不管命运如何安排,她要以八十岁的老身奋力延缓着依赖他物、他人那个时刻的到来;
发卡胡乱地卡在头发上。稀疏的白发,东一绺、西一绺地四下支棱着。妈是极要体面的人,不管条件、情况怎样,她总是把我和她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可是,早晚有一天人人都会有的,那个力不从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双臂勉力地、尽快地摆动着,好像还在协调地配合着快速、利索,其实举迈已经相当艰难的双腿;
妈晃动着双臂往前挣扎着,满脸都是对生命力,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的不明不白、不甘不屈,以及在这毫无胜利指望的斗争中、心力耗尽后的空虚。
妈明显地食欲减退,吃什么都不香了。
而以前妈的胃口总是很好,饭量比我还大。更让人不安的是,我要是不给她夹菜,她就光吃饭。给她夹了菜,她就光吃放在饭上面的菜。我要喂她,她又不肯,就只好把她碗里的饭菜拌匀了让她吃。
吃饭的时候,眼睛茫然地瞪着前方,不知其味地、机械地往嘴里填着。端碗、拿筷子的手也颤抖得厉害,已经不能准确地把饭菜送到嘴里去。连端碗的样子都变了,不是端,而是用左手的食指抠着碗边,把碗夹在食指、拇指和中指的中间。我纠正她几次,可是没用,下次她还是那么拿碗。
妈的脑子里,好像什么都装不进去了。
妈终日倚在沙发上昏睡,任门户大开。
到现在,妈那昏睡的样子还时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特别是那一天,我走进她的房间,见她睡得简直昏天黑地。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干这干那,她也不曾感到丝毫的干扰。她那毛发日渐稀疏的头(妈的头发本来就少,但是不秃),枕在沙发的扶手上。那张沙发是我们经济上刚刚翻身的时候买的,式样老了一点。扶手比较高,所以她的脖子窝着,下巴自然杵在了颈窝上。嘴巴被杵在颈窝上的下巴挤得瘪瘪地歪吊着,气也透不畅快地呼呼有声。全身差不多摊放在沙发上,好像那不是一个有生命的躯体,而是没有生命的血肉。
妈不再关心锁没锁门,会不会丢东西;不再像过去那样,不
管谁,哪怕是我进门,也要如临大敌地问一声:“谁?!”
就是跟我到了美国,住在我任教那个大学区最安全的教职员公寓里,对公寓里其他人出入不锁门的现象,妈也总是放心不下,多次让我提醒他们注意锁门。我只是随口应承着,并没有认真去做。妈见没有成效,就“提醒”不止。弄急了我就会说:“锁门干什么,谁能来偷咱们或是抢咱们呢?咱们有钱吗?没有。公寓里的家具人家也不会要;咱们的衣服即便偷去也没法穿,尺寸不对。再说,咱们俩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不对那些歹徒的胃口,您就放心吧。”
妈一生处在无所依靠,不但无人保护,还要保护我的情况下,对门窗的严紧自然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情结。不过她在世的时候我并没有求其甚解,甚至觉得这种过度的谨慎纯属多余。直到妈过世以后,当我细细回顾她的一生的时候,才有些许的感悟。
就连妈平时赖以解闷的电视也不再吸引她了,虽然电视如她醒时那样总在开着。也不再暗暗地为我关心天气预报,因为我和小阿姨每日要在先生和母亲两处交替地来回穿梭。
既然我已身为他人之妇,就得谋为妇之政。晚上过先生那边去给他做晚饭,以及恪尽我其他的为妇之道;一早再从先生那边过到母亲这边来,所谓的陪伴母亲、服侍母亲,给母亲做一顿中饭,外带在电脑上打字挣钱养家。所以妈老是希望天气晴好,免得我这样窜来窜去地被风吹着、被雨淋着、被太阳晒着……提醒我及时地加减衣服。妈去世后,再也没人为我听天气预报,让我注意加减衣服,或是出门带伞了。
所谓的陪伴母亲也是徒有其名。满头大汗地进得门来,问一声安,和她同吃一顿早餐之后,就得一头扎进电脑。不扎进电脑怎么办?写作既是我之所爱,也是养家糊口的手段。
不知道为什么家庭负担那么重,常常觉得钱紧。家里难得吃一次山珍海味,又少着绫罗绸缎,更没有红木家具、纯毛地毯。一应家什尽量寻找“出口转内销”,力求别致而又花钱少。妈更没有给我什么负担,不但没有给过我什么负担,直到妈去世的那一天,还在倾其全力地贴补我。她的每一分养老退休金都花在了我们的身上。最后,她每月的养老退休金已有一百五六十元之多。
十多年前,当妈还没有这么多退休金,而我的月收入也只有五十六块钱的时候,以她七十岁的高龄,夏天推个小车在酷热的太阳底下卖冰棍,冬天到小卖部卖杂货,赚点小钱以贴补我无力维持的家用。那时候卖冰棍不像现在这样赚钱,一个月干下来,赚多赚少只能拿二十多块钱,叫做补齐差额。即卖冰棍或卖货的收入,加上退休工资不得超过退休时的工资额。但对我们来说,这二十多块钱,就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了。
只是在我有了稿费收入以后,妈才不上街卖冰棍、卖杂货了。记得我将第一笔稿费一百七十八块钱放在她手里,对她说“妈,咱们有钱了,您再别出去卖冰棍了”的时候,她瘪着嘴无声地哭了……
到现在,我的眼前还时常浮现出那些又大、又浓、又重、又急的泪滴。当时,妈坐在我们二里沟旧居朝北那间小屋的床上,那张床靠墙南北向地放着,她面朝西地靠坐在顶着南墙的床头旁……
但是好景不长,后来我们经济上稳定了,可是妈更操心了。
早餐也很简单,一杯牛奶、一个鸡蛋而已。一杯牛奶能喝多长时间?这就是妈盼了一夜的相聚。给母亲做饭也赶不上给先生做饭的规模,一般是对付着填饱肚子即可。比起母亲,先生毕竟是外人,我该着意行事。这也是母亲的家教,自己家里怎么苦,也不能难为外人。这和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负我的理论正好相反。而母亲到底是自己的亲娘,不论怎样,她都不会怪罪我、挑我的理。不但不会怪罪、挑理,甚至千方百计地替我节省每一个铜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