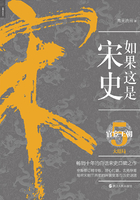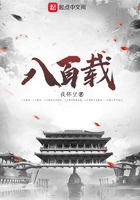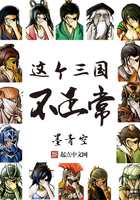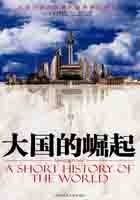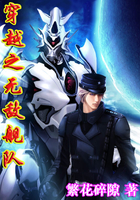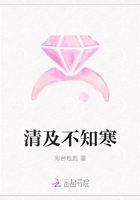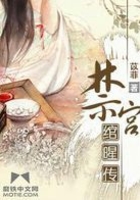一个青年匆匆闯入日本驻清公使馆。他额头宽阔,鼻梁挺直,面色焦急,要找代理公使林权助。这一天是1898年9月21日午后,阴,炎热异常,北京秋日的清爽尚未到来。[3]
日本公使馆是“一栋单层砖木结构的平房……正立面七开间,中砌砖作拱券式的大门”,带有明显的欧洲古典主义风格,门顶檐上的女儿墙上又砌了三角花。它的设计者片山东熊曾入读东京帝国大学,是日本最早接受西方训练的建筑师之一。[4]
公使馆的建筑风格也是日本身份的另一种隐喻:渴望西方却仍深植于东方。它所处的东交民巷正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缩影。它的历史足以追溯到元代,南方稻米经由大运河运到此处交易,因此得名江米巷。到了明代,一些重要衙署、王府与寺庙开始在这里兴建。专门学习外国语言的四夷馆也设立于此,“特设蒙古、女直(女真)、西番(西藏)、西天(印度)、回回、百夷(傣族)、高昌(维吾尔)、缅甸八馆……又增设暹罗(泰国)”[5],这是中华帝国眼中的异域世界,外来者总是朝贡者,臣服于帝国的繁盛与文明。由于“江米”与“交民”读音相近,巷子逐渐被称作“交民巷”,又变成了“东交民巷”,它不再仅指一个巷子,而是一片区域。清代的东交民巷更为喧闹,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都在巷子西口,而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翰林院则在另一端。
巷子的意涵在19世纪后半叶再度发生改变。圆明园被一把大火烧毁之后,清帝国终于同意英国与法国在北京设立使馆,这意味着中国人与外部的关系已彻底转变。这些“野蛮人”与昔日“四夷”不同,他们更强大,还有自己独特的文明。
英国与法国之后,俄国、美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奥匈帝国先后到来,建立使馆。这条曾经用作稻米交易的狭长巷子,如今变成了一个西方建筑、生活方式的展览场,空气里经常飘荡着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先生著名的铜管乐队演奏的曲子。与上海、福州、宁波、广州的租界不同,这里没有治外法权,仍被包容于北京的生活中,使节与夫人们也常抱怨北京道路的泥泞与腐臭。
日本公使馆是东交民巷的后来者。尽管早在1871年中日就已建交,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使馆要么在寺庙要么在租借的民房中暂时栖身——这也折射出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尚未将其看作一个平等的国家。直到1886年,日本终于在东交民巷有了一席之地。接下来的十二年中,公使馆目睹了中日关系的戏剧性转变。日本不仅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还成了清朝革新者们模仿的对象。日本公使曾为觐见皇帝焦灼不已,皇帝如今则充满期待地等待着下野的伊藤博文的到来。
这位匆匆进入使馆的青年,也是一位革新者。“他脸色苍白,悲壮非常。我判断事体极为不寻常”,多年之后,时任使馆参赞的林权助回忆。林权助认识这个年轻人,他是夏日北京活跃的维新者中的一员,名叫梁启超,他的老师康有为更是有名,曾专门给皇帝上呈关于明治维新的著作。
林权助把梁启超请入房间,开始笔谈,汉语是彼时“东亚的拉丁语”,是通用的书面语。“仆三日内须赴市曹救死,愿有两事奉托,君若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林权助觉得这样交流太缓慢,按铃叫翻译官进来。梁启超随即写道“笔谈为好,不必翻译”,接着写下“寡君以变法之故,思守旧老耄之臣,不足以共事,思愿易之,触皇太后之怒……”
此刻,翻译官走了进来,对话加速起来。梁启超乞求,日本出面救助光绪帝与康有为,他自己准备迎接死亡,“我如被逮捕,三天之内会被杀”。
这个场景必定令林权助深感震撼,以至于将近四十年后仍能栩栩如生地回忆起来。其细节或有出入,情绪却异常饱满。这也与林权助的个人经历相关,这位面颊修长的外交官刚刚三十八岁,明治维新时他正是少年。他的祖父与父亲都死于倒幕之战,且站在失败的幕府一边。他运气甚佳,被战胜一方收养,并有幸进入创建不久的东京帝国大学就读,毕业后进入外务省,被派往中国烟台、朝鲜与英国伦敦,是同代人中最有经验的外交官之一。比起回国度假的公使矢野文雄,他的视野与决断更胜一筹。他体验过北京维新的热浪,还为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提过诸多建议。在这些中国维新者身上,他不难看到日本志士的身影。
林权助允诺梁启超,努力去办他交代的两件事,并劝他:“你不必死。你好好思考,必要时随时到我这里来。我会救你。”
梁启超离去后,林权助向正住在公使馆的伊藤博文汇报,这位明治维新的重要缔造人刚卸任首相,中国游历计划正在进行,此刻恰在使馆。“我完全明白了。梁这个年轻人了不起。真是令人佩服。”伊藤感慨道。
夜晚,使馆门口一阵嘈杂,接着梁启超闯了进来。伊藤要林权助救助梁启超,“让他逃往日本。到了日本以后我来帮助他”,“梁启超这个年轻人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奢侈的灵魂”。[6]
留在公使馆的梁启超,当夜必定难眠。这是充满慌乱与恐惧的一日。早晨,太后宣布训政,收回皇帝手中原本就很有限的权力。她颁布的首道政令就是捉拿康有为兄弟:“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康有为的支持者御史宋伯鲁也“即行革职”。[7]
康有为因稍早离开北京,躲过了一劫,康广仁则在南海会馆被捕。一时间流言四起,据说康有为的另一位支持者、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的家也被抄了。在京城的茶馆中,人们纷传皇帝设谋加害太后,且引外人相助,太后因此才再度垂帘。[8]
已预感到大祸将至的梁启超,当日早晨正在浏阳会馆与谭嗣同“对坐榻上,有所擘划”,这时“抄捕南海馆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9]他们连忙拜访李提摩太,想做最后的努力。多年来,这个操着山东口音的英国传教士以促进中国变革为己任。三人随即商定寻求国际力量,容闳去拜访美国公使,李提摩太去找英国公使,梁启超则前往日本使馆。但美国公使进了山,英国公使正在北戴河度假,只有梁启超找到了林权助。
除去给他提供个人庇护,日方拿不出更具体的方案。梁启超或许也被某种羞愧左右,他无法解救陷入危险的皇帝与老师,还躲避起来。翌日,这种羞愧更为加剧。
谭嗣同八月七日进入公使馆,随身携带了著作与诗文、家书的稿本数册,请求梁启超保存。他劝梁东渡日本,自己则选择留下,并以程婴与杵臼、月照与西乡这两个例子来慰藉梁与自己,分别通过一死一生来践行理念。在另一则更为生动的回忆里,谭嗣同还说,海外有很多广东华侨,梁启超可以鼓动他们,建立新的变革基础,而自己作为一个言语不通的湖南人,发挥不了作用。说完这些,他们“遂相与一抱而别”。[10]
对于林权助而言,这也是个充满考验的时刻。收容梁启超的决定,并未得到日本外务省的许可,林尚不知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的态度。八月七日,他发电给外交部,谈及政变的发生、被通缉的康有为、张荫桓府邸的被围。他意识到持续了整个夏天的变法终结了,“皇帝陛下最近数月间已成改革运动之中心,经如此之变故,其权势应有所削减”。他没提梁启超正在使馆内躲避。[11]
时间意味着新的危险,对梁启超的通缉尚未到来,却随时可能发生。当天,林权助请郑永昌(日本驻天津领事,据说还是郑成功后人)护送梁启超离开北京,计划先乘火车抵达天津,再搭商船玄海丸前往日本。离开公使馆前,梁启超做出人生另一个重大决定,他剪掉脑后的辫子,并换上了西装。或许维新者私下谈论了很多次断发易服之必要,但真的发生时,内心恐怕也不无挣扎,它毕竟意味着公开成为反叛者。
梁启超随郑永昌走出使馆时,看上去就像个日本人,中国仆人紧随其后。当天下午三点,火车开赴天津。在紫竹林车站,等候在此的日本领事馆翻译井原真澄发现,同行者中还有“一个穿西装、用手帕遮着鼻子的男士和中国的仆人”。他问郑永昌此人是谁,却没得到答案,只是被命令要警戒前后。回到领事馆后,他才知道,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12]
他们将梁启超藏在领事馆二楼,一切需求由仆人代办。井原真澄随即发现,不断来访的天津变革者说,梁启超已经下落不明,还请他设法相助。李鸿章建立的洋务事业在天津催生出一个维新群体,其中很多人来自广东,“都很热衷于思想和政治的革新”,对伊藤的到访抱有很大的期待。[13]政变消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他们庆幸康有为躲过一劫,但一定想不到梁启超正在楼上。
在八月八日的电报中,林权助向东京汇报整个事件:“主张改革的梁启超因怕可能随时被捕而来到本馆,需求保护。他住了一晚上。由于害怕清国会产生怀疑,我劝他在逮捕他的命令下达前离开北京……他尚未受到任何指控,而我允许他在本馆住一晚上也不至于给清国政府留下任何罪名。如果他在路上还没有被捕的话,几天后,他将乘玄海丸从天津赴日本”。他强调伊藤正住在使馆,“当前的这种政治局势迫使我要求这么做”。他期望得到2000元电汇电信费,还有1000元的津贴费,作为机动费用。
他同时致电郑永昌与驻上海领事诸井六郎,要求“高雄舰、大岛舰的舰长由此奉命与你们一起观察近日的事态发展”,高雄舰正在上海,大岛舰则在天津大沽港。[14]
大隈重信支持了林权助的决定,还在同一天发电报给圣彼得堡与伦敦的日本使馆,通报了北京的政治新动向,令他们探听这些国家的态度。
梁启超躲藏在天津领事馆时,气氛已经变得越发紧张。八月九日,新的上谕到来:“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弟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15]
对梁启超的通缉令也随即到来,在北京捉拿未遂后,朝廷又电旨两江总督刘坤一在上海缉拿。八月十日,上海道台蔡钧搜捕了已改为官书局的大同译书局。所幸,住在其中的梁宝瑛、梁启勋及李蕙仙听闻北京消息后,已于八月七日(9月23日)返回广东。
天津领事馆意识到,让梁启超等到四天后再登玄海丸就太危险了。八月九日晚九点,郑永昌与另两个日本人陪梁启超由紫竹林搭船前往大沽,他们化妆成打猎的样子,计划遇到清兵盘问就说自己要去打鸟。在河上航行一段后,他们被一艘蒸汽快船追踪,上面乘坐着持枪的清兵。十号凌晨两点左右,他们终于在新河附近被追上。快马号士兵声称自己在追拿要犯康有为,怀疑康就在这艘船上。郑永昌随即抗议,说船上并无此人,拒绝搜查。士兵毫不理会,他们将绳索缠上这艘小船,准备将其强行拖回天津。逆行了两百多米后,郑永昌斥责这些士兵非法,又一轮争辩后,快马号同意回天津向总督府汇报,同时派一队士兵登上小船,以护送之名前往塘沽。大约七点,小船抵达塘沽港,恰好与日本大岛号军舰相遇。郑随即挥帽,军舰也放下快艇迎接他们。清兵感到不妙,乘坐路过的一艘清国船离去,不愿再谈。郑永昌登上军舰后,留下梁启超,自己前往塘沽火车站。[16]
经过这惊魂未定的一夜,梁启超甚至来不及喘口气,新危险就再度涌来。第二天八点,又一队清兵登上大岛号,声称要追捕康有为。派遣者正是袁世凯,因荣禄奉旨入京,他暂时署理直隶总督。“该华人年约在三十以内,似非康犯,或为康党”,袁世凯在八月十一日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写道。一天后,他又在电报中更详细地描述情形,称派往查看的洋员魏贝尔在查询时,大岛舰主“坚不肯认,佯不知康犯”,而经过一番访查后,魏贝尔发现船上“实有华人一名,年纪甚轻,已剃发改装。究系何人,无由确查”。[17]
很快,9月26日,大岛舰上又来了一位逃亡者。王照是梁启超的朋友,也是一名活跃的维新者,但与康有为、梁启超不无分歧。他两日前被以“莠言乱政,奸党窃权”的名义弹劾,同样被日本人所救。这是涕泪交集的相遇,在这天崩地裂式的悲剧面前,之前的分歧变得毫不重要。他们对外界所知甚少,不知同志们是生是死,同样不知光绪皇帝会面临怎样的命运,革新的中国又会如何。
他们决定给伊藤博文与林权助写“泣血百拜”的书信,目之所及,似乎唯有这两位外来者才可能提供某种帮助。“启超等忧患余生,所志不成,承君侯与诸公不弃,挈而出之于虎狼之口,其为感激,岂有涯耶”,他们先是表达了感激之心,接着开始担忧光绪的境况,相信外界谣传的光绪患重病的消息只是有意的构陷,皇帝可能被谋害了,因为他在几个月的变法中一直表现得生气勃勃。他们请求日本联合英美诸国,或者致信慈禧太后和总理衙门,要“揭破其欲弑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如”。他们甚至说,诸国干涉或许会导致亡国,但比起俄国庇护下的满洲政权导致的“亡国”,宁可要日、英、美维持下的亡国。他们还恳求伊藤,代为救助身陷狱中的谭嗣同、徐致靖、康广仁等人,因为中国“风气初开,人才甚少”,他们这些“血性男子”之中,或许就有西乡隆盛式的豪杰,若被“一网打尽,敝邦元气无付之士”。落款处是“启超,照,又拜”。[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