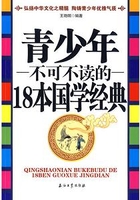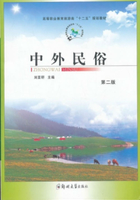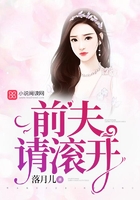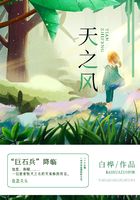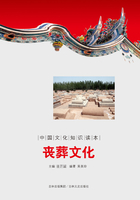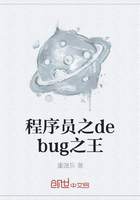追寻汉唐风范
诗歌与散文有着十分长远的历史渊源。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开韵文诗体之一代先河,而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都是用散文的体裁写成的。到有明一代,诗歌与散文的文风几经变换,明代初期的文坛上气势恢宏,宋濂、方孝儒、雄文天、刘基、杨维桢诗性风流,一时胜代遗逸,人才辈出,风神飘举,统领风骚。
这时候的诗文有一种拟古的气象。说起拟古之风,总会让人想起唐宋时候的古文运动,当时文坛上的一些著名人物纷纷打起“复古”大旗,希望借助汉朝以来优秀的文学传统一反六朝骈体文的纤巧华丽和空洞无物,但是唐宋时期古文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借助古文革新开创一条文学发展的新路,正像韩愈所说“师其意、不师其辞”。但是明代初期文坛上兴起的一股追寻汉唐风范的潮流,不但在理论上文必师秦汉、诗必师盛唐,在创作实践上,也是以古人为标本,处处效仿,所以称为“拟古”。
一般认为,明初拟古的风气,是“开国文臣之首”宋濂首倡。宋濂认为“文学之事……当以圣人之文为宗”,对于后世的诗文,他动不动就谴责它们为“风花烟鸟之章”。继宋濂之后,举起拟古大旗的是宋濂的弟子方孝儒。方孝儒的拟古言论表现在他对后世诗文抨击的言语之中:“后世之作者,较奇丽之词于毫末,自谓超乎形器之表矣,而浅陋浮薄,非果能为奇也。”“近世之诗,大异于古。”仿佛因为“大异于古”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与宋、方同时,也有其他一些文学家发出拟古的言论,著名的诗人杨维桢说“非先秦两汉弗之学”,认为只要不是先秦两汉的文章风格与作文技法,就是不应该学习仿效的。著名诗人高启的诗,被人赞扬说是“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时人以为达到极至了,但是就是没有自己的独创风格。
之后兴起的闽中诗派和茶陵派,接过宋、方、杨、高等人开创的拟古旗帜,继续传承。林鸿是闽中诗派的代表人物,他尊奉盛唐诗歌之风,认为“唯唐作者可谓答成……学者当以是为楷式”。他自己作诗也是专学唐人,一味模仿。在他的带动下,闽中一带诗人竞相效法盛唐诗风,形成一个闽中诗派。而明代的诗歌,首先是在闽中一带昌盛的,所以他们推崇盛唐的思想,对后来的诗坛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有人认为,后人作诗师法唐朝,认为唐诗是正宗,其“胚胎实兆于此”。
茶陵派的代表人物是成化、弘治年间的李东阳,由于他的籍贯是湖南茶陵,所以他和他的弟子门生组成的诗派就叫作茶陵派。在李东阳看来,唐以外各个时代的诗歌都是不值得推崇和仿效的。他评价六朝和宋元时代的诗歌时说,虽然这中间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但是不能够代表这个时代的特点,而且也不能够深得诗歌的真谛,“只是禅家所谓小乘,道家所谓尸解仙耳”。这一评论,过于尖刻,不能不说是他的主观臆断。他还认为,宋人写的诗歌,由于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思想比较深邃,哲理性比较强,但是与唐诗相比,相差太远了;元代诗歌相对来说有复归质朴的特点,于是内涵相对浅显,注重形象表达,倒是离唐诗近了一些,但是也不能够尊为典范,因为“所谓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耳”,既然有那么多的唐诗可供模仿,何必再把元代的诗歌拿来效法呢?
讲到明代文坛的拟古倾向,不得不谈“前七子”和“后七子”,他们对明代前期拟古思潮的继承和发扬,使拟古运动在明代文坛中真正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明弘治年间(1488~1505),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徐祯卿、王九思、康海、王廷相七人结成一个文学团体,“文称左迁(左丘明、司马迁),赋尚屈宋(屈原、宋玉),古诗体尚汉魏,近律则法李杜(李白、杜甫)”,至于历史上其他的文学家一概嗤之以鼻,“非是者弗道”。由于这七人在文坛上的影响,明代文学拟古思潮一时风行,后人称他们七人为“前七子”。既然有“前七子”,那么就肯定会有“后七子”,嘉靖年间(1522~1566),李攀龙、王世贞、宗臣、谢榛、徐中行、吴国伦、梁有誉七人,支持“前七子”的主张,结社宣传,发扬天下。这七人才高门望,例如李攀龙有“文苑之南面王”之称,而王世贞更是“声华意气笼盖海内”。这些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认为这之后的书是不应该去读的。“后七子”拟古思潮的影响,直到万历年间(1573~1619)还能够感觉得到,所以自弘治至万历这一百多年的时间,是明代文坛拟古风潮的鼎盛时期。其中“前七子”“后七子”等人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拟古潮流因何而起
想了解明代诗文拟古风潮兴起的原因,就要深入分析这些拟古主义者们所批判和抨击的对象。无论是宋濂、方孝儒,还是后来的“前七子”“后七子”,他们共同抨击的目标是宋代的“理气诗”和“以文为诗”。所以,如果从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来看,这个时代的拟古风潮,无疑体现了一种对宋元一代诗文流弊的反动。
所谓“理气诗”,指的是宋代诗人受到当时流行的理学思想的影响,在诗歌创作中不自觉地融入了许多哲理,虽然使诗歌增加了许多深度,但是忽略了诗歌的形象艺术以及通俗表达,结果诗歌中充满了说教气息,失去了唐代以来的质朴纯真的美感。著名的理学家朱熹有一首诗歌是这么写的: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首诗虽被后人广为传诵,但都是作为一首哲理诗来理解的,它说明了人的思想就像水一样,必须有源头的活水作为补充,流水不腐,否则就会僵化,没有了创新和清晰的思辨能力。所谓“要让你的思想流动起来”,正是这个道理。至于宋朝的散文,更是“长于议论而欠弘丽”“尚理而病于意兴”,甚至“言理而不言情”,使诗歌的文学性大大减弱。还有一些理学家“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把诗歌变成了压韵的语录讲义,“以论理为本,以修辞为末”,这就是所谓的“以文为诗”。“以文为诗”更加忽视了文学的自身特点和规律,使得诗歌难以卒读,味同嚼蜡。
明代拟古文学家极力反对这种创作方式,他们强调诗文之间各方面的不同,认为诗歌首先应该“吟咏性情”,而文章也应该首先是文学性和可读性。李东阳认为,早在“六经”中诗文已经分家,各有各的写法,写诗应该像《风》《雅》《颂》,写文章应该像《诗》《书》《礼》《乐》《易》《春秋》。他指出诗之区别于文的最大之处是诗歌独特的表现手法:“以其有声律讽咏,能使人反复讽咏,以畅达情思,感发志气。”那么,怎样才能够改变宋代诗文的弊端呢?在他看来,学习先秦两汉的古文、效法盛唐时期的诗歌,这才是正途。
明代拟古运动还有一个重要的批判对象,那就是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这一宫廷文学形式。所谓“台阁体”,指的是明初由杨士奇、杨荣、杨溥(人称“三杨”)开创的一种应景、颂圣、题赠、应酬之类的诗文,内容千篇一律,多为歌舞升平粉饰太平的诗文。“三杨”在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都是官居高位,成为所谓的“台阁重臣”,他们所作的诗文就叫作“台阁体”。这一类的诗文,如杨士奇的《西夷贡麒麟早朝应制诗》《圣德诗十首》等,雍容典雅、词气安闲,但是内容空洞、陈陈相因、白草黄茅、纷芜靡蔓,至于“成、弘间,诗道旁落,杂而多端”,更可悲的是“众人糜然和之,相习成风”,终至“庸肤之极,不得不变而求新”了。针对这种“流于庸肤”“气体渐弱”的危机局势,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派”试图以“宗唐法杜”为旗帜,希望能够扫除文坛上的冗长拖沓,于是“永乐以后诗,茶陵起而振之,如老鹤一鸣,喧啾俱废”,给“台阁体”诗风以沉重的打击。之后,“前七子”“后七子”继续以拟古法则批判“台阁体”,极有明一代诗坛大盛。他们对“台阁体”的批判不但有改革文体、文风的要求,而且还有一定的思想解放的意义,因为对宫廷歌舞升平文学的反对,本身就是一种革命性的挑战权威、冲破束缚的行动。
正是因为拟古文人对宋人“以文为诗”和对明初“台阁体”的批判,“情”和“意境”在后来的诗歌创作中才得到了重视。宋人写诗,大多不怎么重视“情”,或者说他们对“情”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如对“理”的重视程度高。宋人“言理不言情”的思潮大大违背了诗歌本身的艺术特征,“感心而动目者,一发于诗”,这一点正是明代拟古主义者所追求和倡导的。在《梅月先生诗序》中,李梦阳说:“情者,动乎遇者也,幽岩寂滨,深野旷林,百卉既痱,乃有缟焉。山英之媚枯,缀疏横斜,奇绮清浅之区,则何遇之不动矣?……故天下无不根之萌,君子无不根之情,忧乐潜之中,而后感触应之处,故遇者因乎情,情者形乎遇。”徐祯卿说:“夫情能动物,故诗足以感人。”所以诗是什么呢?诗其实就是“心之精神发而声者也”。
如果说“情”是诗歌创作的灵魂,那么意境就是诗歌美感体现之所在。如果一首诗没有意境,无论它的文辞多么华美,内容多么丰富,都难以体现出这首诗的美感。明代诗人把诗的意境称为“情景”,认为“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二者是缺一不可的。诗歌创作的真谛,就是“发情景之蕴”,所谓“遇境即际,兴穷即止”“情景妙合,风格自上”,都是这个道理。正是因为受到追求“情景”的启发,明代诗人开始对民间诗文有所重视,比如李梦阳高度评价了市井流传的民间歌谣,认为它们中间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何景明也认为民间诗歌质朴真实,这是那些士大夫们写不出来的。王廷相则亲自研究、学习民间诗歌的创作,他写的十首《巴人竹枝词》就是对民歌的一种模仿。这种对民间诗歌的重视和研究,与当时在市井百姓当中兴起的通俗文学相互对应,共同表达了明代文学思潮的新动向,其中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无论“前七子”和“后七子”的主张产生了怎样的积极意义,在他们后来的著作中却难免出现了一种唯古是尊的错误倾向。古人的诗歌和散文,无论是内容、格调、风尚、音节以及一切内在的意境和外在的形式,都成为这些拟古主义者逐篇模拟的对象。一味地拜古贱今,在精华的取舍方面不免带有盲目的主观意识。何景明认为“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文非秦汉不以入于目,诗非汉魏不以出诸口”“诗自天宝以下,文自西京以降,誓不纡其毫素”“大历以后书勿读”。这种“文不程古则,不登于上品”的思想与主张,在清算宋人“理气诗”以及明初“台阁体”的同时,也阻塞了后来诗文创新之路。
其实拟古主义文学家内部发展到“前七子”“后七子”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危机的征兆。“前七子”中的何景明,已经对盲目的仿古隐含的弊端有所认识,他曾经指责李梦阳“刻意古范、铸形塑模”“如小儿依物能行,独趋颠仆”。“后七子”之一的谢榛,一边在鼓吹诗以初唐、盛唐为宗,一边又主张兼收并蓄、采取各家之所长,尤其是重视性灵的抒发,比如他曾经说过:“万物一我也,千古一心也。”他认为诗文的绝妙之处在于自然,而不是单纯的仿古,所谓“妙则自然”。这使得李攀龙、王世贞大为愤慨,“岂其使一眇君子肆于二三兄弟之上!”于是众人自作主张,把谢榛从“后七子”里面除名。
单纯的拟古,在晚明时期已经在文坛上失去感召力量,再次发起明代诗文革命的,就是性灵派文人。
我是谁——性灵诗歌的文化心态
所谓“性灵”,大致是“反诸内心”,并且把内心的东西真切地表达出来的意思。“夫性灵皎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只要是真情所在、发诸笔端,那么无论是写帝王将相也好,写才子佳人也好,写生活琐事也好,写花鸟虫鱼也好,甚至写蝼蚁蜂蝶、诙词谐语、亲子之情、男女之事,都是真诗妙文。
早在万历年间,当时的大思想家李贽就对八股考试进行了批评,认为八股考试在四书五经上寻章摘句,“咸以孔子是非为是非”,这是对人心灵和个性的一种束缚和摧残,只能够使人丧失本真自我,本来纯净的本心被后天习得的道理见闻所蒙蔽。他提出自己的“童心说”,认为“童心者,真心也”“天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焉”。在“童心说”的基础之上,他又提出应该重视“性情”,认为“声色之来,发于性情,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自然发于性情,则自然至乎礼义,非性情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作诗作文,也必须要以“童心”和“性情”为源泉或者根本。万历十八年(1590),李贽与公安袁氏初次会面,从此他的思想对后来公安性灵派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安袁氏,又称“袁氏三兄弟”,指的是袁宗道、袁中道和袁宏道三兄弟。他们在与李贽初次会面的时候,就已经以诗文著称一方。万历十八年,李贽游历到公安,在一座庙里与袁氏三兄弟会面,几个人谈天说地,意气风发。李贽称赞三人的脱俗性灵,尤其是称赞袁宏道为世间“英灵男子”,说他“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而袁氏三兄弟也对李贽的思想深为敬佩:“先生一见龙湖,始知一句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批露。”尤其是对那些离经叛道的言论,三袁更是真诚折服。此后,袁氏三兄弟文风更加倾向于发掘内心世界,追求一种人心与自然的本真领悟与表达。“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由于这三人的影响,公安一带文人争相尊崇性灵,一时形成“公安”一派。他们或喜悦或悲伤,七情六欲之所致,都拿来写作诗文:
言既无庸默不可,阮家哪得不沉醉?
眼底浓浓一杯春,恸于洛阳年少泪。
如此狂放不羁的表面,掩藏着一颗真实质朴的心灵。当年阮籍驾车出行,信马由缰,走到没有路可以前进的地方,怎么办呢?大哭一场而已。千古之下,有袁氏这样一首诗,几百年的音符,在这里产生了一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共鸣。狂放不羁是与恃才傲物相互表里的,袁宏道也表达了他的直率性情:
一言不相和,大骂龙额侯。
长啸振衣去,漂泊任沧州。
真实的性灵是与自然结合在一起的,而天地之间的山山水水也被诗人的情趣所点燃,生机勃勃而又意趣盎然:
村老无花也自新,山茶红似女儿唇。
数茎白发春前长,一点青峦雨后真。
莺欲下枝先作语,鹊能占梦亦如人。
锦戈金络纷纷去,飞向晴空十里尘。
性灵小品文精巧细致
公安派不但写诗如此,即使是在作文的时候,也是远离经典古文、摒弃说教礼法,随心所欲、散漫风流,真正在文中贯彻“心我天地如一”的理念。灵气盎然的小品文是三袁最擅长的,这种文章无论是从选材定题还是从表达方法上来说,对呆滞死板的八股文都是一种反动。
袁宏道游览极乐寺庙,说那里有“百练千匹,微风水上,若罗纹纸。堤在水中,两波相夹,绿柳四行,树古叶繁,一树之荫,可覆数席,垂线长丈余”,又说看到“对面远树,高下攒簇,间以水田,西山如螺髻,出于林水间”。由于看到这里“南风不用蒲葵扇”的景致,于是便有了“纱帽闲眠对水鸥”的感慨。“何日挂进贤冠,作六桥下客子,了此一段情障乎?”其实古代有许多文人都有一种隐居山水间的心态,或者称之为“弃世情结”,但是有这种情结的人,起先大都在积极地奉行出世信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一旦发现自己的理想受挫,才会想起归隐山林,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结庐于仙境,唱着“敖吏身闲笑五侯,西江取竹起高楼”或者“妻太聪明夫太怪,人何寥落鬼何多”——正像落榜的经历成就了“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样一首千年传诵的绝妙诗句一样。像袁氏三兄弟这样正值壮年,事业上也并没有十分重大的挫折,却也要处处流露出归隐的心态来,即使是一时的“为赋新词强说愁”,也足见他们的生动飘逸与空灵洒脱。
除山水之外,小品文的写作题材多种多样,不一而足。例如袁中道在《寿大姐五十序》中回忆幼时与大姐之间的手足亲情,生活中的琐事细节被袁中道用细腻的笔法娓娓道来,字里行间流露的真情使得读者宛然就在他们的周围。而袁宏道在《虎丘中秋夜》一文中着意描写苏州的市民风俗,张扬声色之欢,写出正常的人间社会之景象:“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僖童走仆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石、千人石、鹤涧、剑池、申文定祠下,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
性灵小品文在晚明非常盛行,除三袁之外,李流芳、张岱、归有光等人也竞相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创作了大量精美细巧的散文片断。归有光所作的《项脊轩志》回忆了自己与祖母、母亲以及妻子三代的真情,也是摘取寻常往事,录在笔端,却能够在平凡的回忆里面抒发出“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的感情来。尤其是描写自己与妻子之间的深情,单单是那一句“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就足以把填塞胸膛的思念表白于日月之间,使人叹为观止。
许多文学家还表达了对当时社会生活长卷的关注,比如张岱就写过诸如《世美华堂》《金山竞渡》《越俗扫墓》等描写民间风情、工艺杂技的小品文,还编辑了一部《夜航船》,收集奇闻逸事,以供读书人在读圣贤之余消遣。
亦诗亦画,风流儒雅
晚明时期,一些画家创作的放荡不羁、不合礼法的诗文也是晚明性灵文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亦诗亦文亦画的人物有家喻户晓的唐寅,有他的朋友祝允明、文征明以及狂生徐渭等等。他们无论写诗还是作画,都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从人的自然欲望出发,表达孤傲不羁的个性,这逐渐成为他们的艺术宗旨。无论是“堕水堕驴都不恨,古来一死博河豚”的徐渭、“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业钱”的唐寅,还是“有花有酒有吟诵,便是书生富贵时”的祝允明,都天真率直。唐寅写过几首题为《漫性》的诗,其中有四句说:“此生甘分老吴阊,万卷图书一草堂。龙虎榜中题姓氏,笙歌队里卖文章。”这几句诗,把一个曾经追求过八股功名而不得,然后沉湎于青楼歌舞之中的“江南第一才子”写活了。社会法统既然已经荒诞化,那么何不在制度之外寻找自己心灵的归宿呢?于是他一边为自己死去的妻子写着“镜里形骸春共老,灯前夫妇月同圆”,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深切悼念,一边为害了相思病的妓女写着“门外青苔与恨添,和书难寄鲤鱼衔”,表达自己对妓者痴情的理解。
当然,性灵文学家的率性有时候也会走向极端。比如徐渭性情狂傲,晚年愤激整个社会,更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有时候达官显贵到他的寓所拜访,他也是拒绝接待。他常常自己一个人带些酒,叫一些乡下人或仆人来,陪他到酒馆一块儿喝酒。这其实还是可以理解的,让人不能够理解的是有时候他甚至“自持利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者“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许”。这种自残的做法只能说是已经有精神分裂的症状了。追求性灵到了这种地步,已经不再是追求本真的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