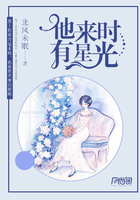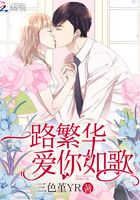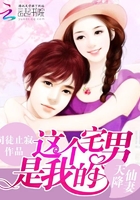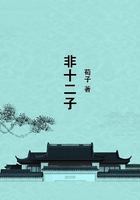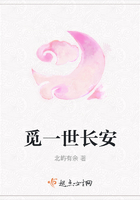来从虚空来,还从虚空去。往生再世,皆当欢喜。——前记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南方小镇,那里桃红李白,草长莺飞。
南方小镇中,和尚小明子和小英子发生了一场懵懂的爱恋。
荸荠庵,庵不像庵,寺不像寺,既无清规,也无戒律,和尚也是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们皆不缺少,可以杀生吃肉,亦可以娶妻找情人。
“幸得识卿桃花面,从此阡陌多暖春。”汪老笔下的明海聪明善良,小英子美丽多情,两个天真纯朴的少年并没有受到世俗的污染,他们的童心明媚而澄澈,充满诗意,充满梦幻,成了作家“桃花源”式的理想生活的象征。就像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他们相遇了,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爱上了,也就爱上了,无关风月,无关功利。
“你叫什么?”
“明海。”
“在家的时候?”
“叫明子。”
“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给你!”
小英子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小明子就剥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起来。
大伯一桨一桨地划着,只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哗——许!哗——许!”
这就是情不知所起,而一往情深了吧。许久许久以后,船桨拨水的声音撩拨着一个小和尚的心弦,正如那串脚丫子印把小和尚的心给搅乱了。
这是一种“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追求“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是民间艺术中弥漫着的自然神韵啊,也正是传统文人苦苦追求的美学理想。
受戒,短短的十天,却意味着小明子将从一个无拘无束的少年,甚至可以说是孩子,变为一个规矩繁多的和尚,而头上那几个漆黑的戒疤,也如同一副铁链,约束着他未来的点点滴滴,成为他灵魂的一部分。在这个顾虑约束繁多的世界,流星中打下的结,少年人单纯的祈愿,又怎能成真。
受戒,便是人性中接受规则与规矩的那一刻,存在于每个人的生命中。
那十数个戒疤便象征着规则的约束,约束着人心底的欲望,更意味着其与欲望的不断抗争,在每个人心底的角落。
《受戒》其实就是作家对普通人的生活与命运的理解,是对自己渴望的生活的描述,是对自由而淳朴的人性的歌颂。汪曾祺所理解的真正的生活是,它是命定的,正如小明子命定要出家当和尚,庄稼人命定要为收成与一日三餐一年忙到头,但人可以不完全受制于命定,可以把种种对生活的戒律抛开,因为人是有创造力的,有情感的,正是创造力与情感,使人创造了风俗,而这种风俗就是对命定的抵抗。
其实受戒这个题目是带有反讽性的,“受戒”本来是和尚表明接受佛门戒律的仪式,而就在明海受戒的同时,两个小主人公的爱情也走向成熟,在结尾就以秋水般的文字,纤尘不然的意境揭示了性的成熟。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乡村的姑娘比较纯,在性的观念上比较解放。这是思无邪,是《诗经》里的境界,汪老就说: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
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这正是汪老的境界啊,大道不动干戈的境界。汪老的文章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不管是文学还是做人,最高标准,终极追求,可不就是一个真字。面对是非时要真,面对感情时要真,面对选择时要真,面对自己时更要真。
这正好与如今将简单的道理表达得百折千回的风气相反,他则把最复杂的事物写得明白如话。
他是洞察秋毫便装了糊涂,风云激荡过后回复了平静,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
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
“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无怪乎汪老被评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那是一株冬眠的老树,在经历了无数的严寒冰冻之后,终于盛开了满树夺目的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