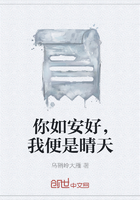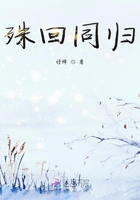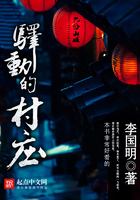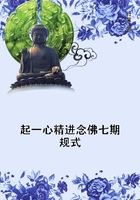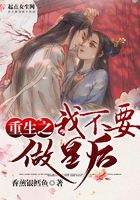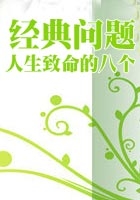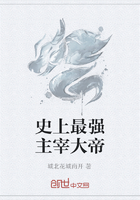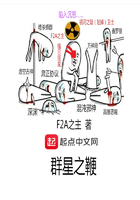千般荒凉,以此为梦;万里蹀躞,以此为归。——题记
夜色寂寥,几点星辰。
母亲说今日带我去看越剧,我很欣喜,长这么大,还从未正经看过一出戏。
说来惭愧,我对戏曲的认识仅限于书本上一板一眼的方块字,什么四大剧种、中国国粹云云,以及电视屏幕上的流光溢彩、顾盼生姿。也许儿时在剧院里是看过戏的吧,但那时不过六七岁年纪,又怎生坐得住?那时不是被那动人的起承转合的腔韵吸引,而是只全神贯注于那五彩斑斓的戏服。这恐怕是每个人孩提时代最初的幻想吧,无限地纯真。
前去的路上,遥遥地就望见了那座阁,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八角玲珑,四方通透,古朴却不拙重,轻灵却不出挑。橘黄的灯光掩映,像是披上了一层华衣,有种令人惊艳的大气与典雅。
行至正面,只见匾额上书三个隶字:
“琢玉阁”。
不免被震撼。青石阶、雕梁柱、钿花窗,似乎回到了那些个梅雨色的朝代,在那江南亭阁深院里,那些个知书达礼的世家小姐,是否期待着她的那个翩翩公子打马归来?抚今追昔,那些金玉良缘、才子佳人的故事岂又少得了?
一直到踏上石阶,我还幻想着水袖轻扬、佩玉鸣鸾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窈窕淑女。然而世事总是那么地出人意料。
没有戏台,没有道袍,没有浓妆粉饰,只有几个普通的老头老太正在理座清腔,准备开唱,只有一束纯白的日光灯笼罩着他们,几台风扇不知疲倦地微微吹着。凉风有信,花香清逸。
实在难掩失落,这不过是阁的一隅罢了。我草草寻了张塑料椅落座,周围已有零零星星十几人,看样子是常客了,从容宁静。他们大都倚在石栏上,和母亲一样。我闭上了眼,有些乏困。
“梁兄——”
一道亮丽清亢的女声乍起,随后,是二胡,是琵琶,是胡琴,是洞箫,水月镜花之中,还有微微的钟磬之音。
倏地,我睁开了眼,不可置信地注视着眼前这一群低眉信手续续弹的老人,莫不是谪下凡尘的仙人?恍惚间,我似乎觉得他们身上形式不一的家常便服化为了雪白的素衣,光明的翅羽,在无极中飞舞,衣炔飘飘,仙风道骨。
他们气定神闲,在经历了沧海桑田的那个年纪,看什么都看若闲花。有的两鬓斑白,有的戴上了老花镜,但他们从来不看曲谱,成竹在胸,信手拈来。
此时此刻,莫名地想到一个词——艺术家,而且是老艺术家,肃然起敬。
这儿没有《桃花扇》、《西厢记》这样的经典曲目,没有青衣绰约的名旦花角,没有像样的舞台,没有华美的灯光,却聚集了一众爱好者,岁月如流,笑颜如花。正所谓“高山仰止,流水知音。”越风雅韵,破古而来,今天的他们,一声一喉觅知音。
买花载酒,不似少年游。愿少年阅尽繁华,归来不忘初心。人们常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却很少有人知道下一句,“初心易得,始终难守。”日月如百代过客,去而复返,返而复去。艄公穷生涯于船头;马夫引缰辔迎来老年,日日羁旅,随处栖身。日复一日的生活,磨去了少年的锋芒,生活的激情,还有那诗意的文化也与我们渐趋渐远。纪伯伦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而现在,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似乎早已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混沌初开,洪荒初始,天清地玄,是人猿相揖别的年代。最初的人类,赤诚袒露,以叶覆体,采露为食。山顶洞穴,篝火冉冉,映照了原始的狂欢,映照了文明与野蛮的撞击。麦黄的皮肤下,鲜红的热血,熊熊燃烧,欲火翻腾。
饥饿,与虎狼争食;雨雪,向苍天祷告。
偶然的机会,金属与星火就那么出现。
霜冷长河,那时就已经有了龙的图腾,也是我们的族徽。
“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浩浩汤汤的五千年,若以花喻朝代,秦朝是毒辣的狼毒花,短暂而狠厉;汉朝是一丈红的蜀葵,明艳艳地张扬;魏晋是水边绽出的幽幽白莲,清秀永恒;隋唐则是端庄大气的华贵牡丹,艳压群芳;至于宋朝,是娇弱的空谷兰花,忧郁且精致。
而中华汉字,经烽火狼烟,狂吟怒吼,浅斟低唱,时至今日,仍与日月争辉,更是以它的傲骨,撑起中国文人的脊梁,撑起中华文脉。戏剧也从中衍生而出,一路繁花,一路云霓。
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倘若有些吟风弄月的风雅,不难在此等简陋艰苦的处境中拾得些许过往的流年记忆,譬如戏剧,譬如初心,譬如文化。越是温贫暖老的东西,越入心。就像梁祝化蝶,“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谶语总是让人心头一暖。
浅浅一笑,我莫不是入了戏吧。
忽然忆起,程蝶衣就那样入了戏。究竟是蝶衣还是虞姬?一句“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让他深陷命运,困了一生。拔剑自刎的那一刻,他有灵魂演绎了死亡的美丽。他的名字是张国荣……
一曲终了,余音仍绕梁。我们四下俱静,无人回神,唯见江心秋月白。不知是谁拍手叫好,拉回了我们,瞬间掌声轰鸣。
突然发现一件奇事,弹奏乐器的都是男子,甚至琵琶也是。
原来,琵琶不仅对旗袍美人。
原来,男子也有这般书生儒气。
原来,普通人也可沾尽风流。
于我看来,他们虽垂垂老矣。但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因于那份岁月的沉淀与对文化的感怀,在静笃的云烟里,他们与自己相知相悦、相承欢。流年,便在温贫暖老中开出了清欢的模样。
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一路坎坷,一路负重前行。一路云霓,一路繁花相送。
诗三百思无邪;诸子百家著作千万;秦一统六合一统文字;汉有司马迁记史;晋有拓跋帝习汉;南朝有孔雀南飞,北朝有木兰从军;唐诗之韵、宋词之魂,镶在明月上;一支元曲花枪有弹,起承转合;明清小说传奇陆离;民国大师南渡北归;现代文学欣欣向荣。只问初心,无问西东。
中华文脉代代相传,从亘古走来,于彼岸亲善地呼唤着所有以文载道的渡者。让他们得以在心中种一片桃源,修篱种菊,与生命的慷慨与繁华相爱,即使岁月以刻薄与荒芜相欺。那彼岸,不是生命的尽头,因为生命永无尽头。
荒原上,这是文字冥迷的召唤。
——这是中华汉字的无尽藏。
但愿千万年后,世间仍是青山绿水,不忘初心,美美与共。我们不会用世间所有的路倒退,只为遇见初心,遇见文化的本来面目,那也是最真诚的面目,最原始的面目,最美好的面目。不会再与美好之间隔着一场梦。不会游山归来,世道人心已变了原般模样,而时光已将我们洗劫一空,我们没有了初心,没有了文明,而只能用残雪粉饰太平。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一书中写道:“时间和文字在一个个老庭院里厮磨,这是文化存在的极温暖方式。千般荒凉,以此为梦;万里蹀躞,以此为归。”那些美好,出生在我的前世,被季节封存在四月天,窗外的柳絮做了宾客,梁间的燕子做了邻伴,梦中的白莲做了知己。以不施粉黛的素净姿态踱步在轻烟长巷,在那个四月天,我们就那么静静地相遇,沿着一首诗的韵脚,随着流淌的笔墨,邂逅纯净的美好。
这不能说是文化的传承,但至少是美好的传承,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青莲皓月,斗酒十千。这群人,也许他们还有一个名字:
“一生诗意似少年。”
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
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
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