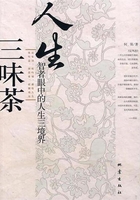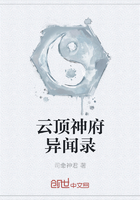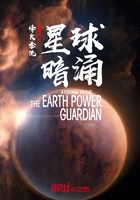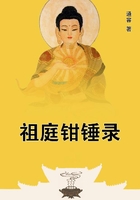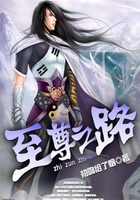《一只丑陋的狗》
久雨乍晴,春天的山径上鸟腾花喧,无一声不是悦耳之声,无一色不是悦目之色。
忽然,跑来一只狗,很难看的狗,杂毛不黑不黄脱落殆半,眼光游移戒惧,一看就知道是野狗。经过谨慎的分析,它断定我是个无害的生物,便忽然在花前软趴趴地躺下,然后扭来扭去地打起滚来。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厌恶,因为这么好的阳光,这么华灿的春花,偏偏加上这么一只难看的狗,又做着那么难看的动作!
但为了那花,我一时不忍离去。奇怪的是,事情进行到第二步,我忽然觉得不对了,那丑狗的丑动作忽然令我瞠目结舌,因为我清楚地感知,它正在享受生命,它在享受春天,我除了致敬,竟不能置一词。它的身体先天上不及老虎花豹俊硕华丽,后天的动作又不像受过舞蹈训练的人可以有其章法,它只是猥猥琐琐地在打滚——可是,那关我什么事,它是一只老野狗,它在大化前享受这一刻的春光,在这个五百万人的城市里,此刻是否有一个人用打滚的动作对上帝说话:
“你看!我在这里,我不是块什么料,我活得很艰辛,但我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要在这阳光里打滚,撒欢,我要说,我爱、我感谢。我不优美,但我的欢喜是真的。”
没有,城市族类是惯于忘恩负义的,从不说一句感谢,即使在春天。
那一天,群花在我眼前渐渐淡出,只剩那只老丑狗,在翻滚唱歌,我第一次看懂了那么丑陋的美丽。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中时”·人间版》副刊
《盘》
颁奖典礼结束了,我看到他迎面走来,今天他既不是领奖人,也不是颁奖人,他是个安静的帮场人。
他的职业是电视台的美工。不过,照我想,电视台大概不十分需要大刀阔斧的美工。每次跟戏,他不忍让自己的两手闲着,所以就拿些竹子来雕,雕久了,也就自然变成了一个竹雕艺术家。
看到他走过来,心里万分高兴,手心里立刻充满上次把玩那些竹器的温凉清润的感觉。这时,一位夏夫人刚好走过,我忍不住立刻拉住她,很“鸡婆”地说:
“你知道吗?他是个竹雕艺术家,小小物事,你不知雕得有多可爱呢!”
年轻的“竹雕人”身上刚好带着照片,便掏出来给夏夫人看,雍容的夏夫人一面看一面颔首微笑说好,但我却火焦起来,一面结结巴巴气急败坏地分辩道:
“不是的!不是的!真的全不是这回事,这些照片不对!完全不对!……那些竹雕一进了照片就完了,那竹雕真的放在你手上的时候才不是这样的呢!完全不是的,跟照片完全不一样……”
“我知道,”夏夫人娴雅凝定,“竹雕,大概像玉一样,要‘盘’。”
我松了一口气,我情急之间找不到的那个字,她轻轻易易就吐出来了。
“盘”是玩玉的人专用的动词,它不是摸不是搓不是揉甚至不是爱抚,它是手指的试探,是以肌肤的贞静柔温去体念器物的贞静柔温。“盘”是物我之间眼神的往返顾盼,呼吸脉搏中的依依相属。
啊!我也要好好地盘一下,盘一下我所拥有的岁月和记忆。
——一九九二年四月一日《“中时”·人间版》副刊
《致L》
亲爱的L:
接到你的信令我错愕惊讶——不是因为你信里的内容,而是因为世间竟有女子如你,如你这样侠骨柔情。
你写信,是急于告诉我T多么歆羡我的文字。你真的有些急了,你大概觉得我如果不知道此事,该是极大的遗憾。
然而,可爱的侠女啊,其实我是知道的,早在二十年前,有一次,在一次冗长的什么大会之后,T曾给我一张小小的名片,片子后面写满了他对我的期许。那是个什么名目的大会我早忘了,但那张小小的卡片,于我却是一生一世的感念。
说起来,这件事,连T自己也未必记得吧!
反而,我是记得的,我记得别人对我的肯定,我真的既愧又喜,绝不敢怠慢亵渎。
但是,亲爱的L,如果你要说的是,T是普天下最拥戴我的人,我也许也有另一项数据要告诉你:我——我自己——是普天下最挑剔我的作品的人。行年愈长,肯指正你的人便愈少,如果不强令自己做自己的对头,又怎能有分毫的进步呢?我知道T是诚恳的,他誉我为登高好手,我感激——但我却明明了解,还有更高的海拔是我没能到达的。
因此,选择孤独对写作者而言几乎是必要的。但逃开令人生畏的冷眼容易,逃开令人开心的掌声难,真正的写作者必须两者都放下而游开去,像鱼,共一个江湖,却悠然相忘。
那些喜爱我文章的人,是为何而喜爱呢?岂不是因为我有一点用功,有一点认真,因而有一丝半毫心得吗?我多么希望自己无负于那些温暖的期望,如果我怠惰了,那才是我此生最大的罪恶。至于疏于礼数,恐怕只好靠朋友曲谅了。
文学令我情深,也逼我情薄;知我罪我,我皆无悔啊!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中时”·人间版》副刊
《傻傻的妈妈》
一位老邻居叫住我,要跟我说新邻居的事:
“你知道吗?我家楼下换了人啦!新搬来的这家也真好笑哩。”她说着,真的咯咯笑了起来,“这家妈妈自己跟我说的,她说她儿子去年联考没考好,今年重考,说不定就会考上台大哩!如果考上了,这间房子刚好近台大,所以虽然贵,她也买啦!买了好让儿子上台大方便嘛!”
“唉!”她忽然脸色一沉,“你知道吗?日本有一个字,叫——”
“什么?”我一点也听不懂她咕噜的一声日文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要是翻出来,就是‘傻傻的妈妈’,世上就是偏偏有这批傻傻的妈妈——”
我忽然想起另一个朋友,他念哲学,他哥哥念物理,他的母亲有天一个人在家里发起愁来。
“她愁什么呢?”我还以为是愁两个儿子都念了冷门的科系。
“愁——哈!你猜!原来她愁如果有一天,我和大哥一同中科,一同拿下了诺贝尔奖,记者要来访问她,那时她该说些什么才得体呢?”
据说后来她不愁了,因为那篇谈话她已经想好该怎么说了,有备无患,她开始安心等待那一天来到。
傻傻的妈妈,痴心的妈妈——但,这是上帝的意旨啊!如果所有的母亲都能清楚评估自己的孩子的资质,我们还要母亲做什么用?她不过等于一个智商鉴定中心的职员罢了。
每一个孩子都是在“误以为是天才”的痴心奉献中才成长的啊!
——一九九二年五月七日《“中时”·人间版》副刊
《半盘豆腐》
和马悦然先生同席,主人叫了些菜,第一盘上来的是“虾子豆腐”。
后面几道菜陆续端来的时候,女侍轻声提醒我们要不要把前菜撤下。
席间几个人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大家都客气,等着别人下决定。时间过程也许是一秒钟吧?女侍仿佛认为那是默许,便打算动手撤盘子了。
“哦——这——”马教授警觉到再不说话,那半盘豆腐大概就要从此消失了,但他又是温文的,不坚持的,所以他欲言又止起来。
女侍毕竟训练有素,看到主客的反应,立刻把盘子放回。
“啊——我——”马教授大约经历了一番天人交战,此刻不禁笑了,“我还老是记得自己是个穷学生的时候。”
穷学生?他现在已是退休的资深教授,是欧洲汉学的泰斗。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中唯一通达中文的委员。所谓穷学生,那分明已是四十多年前的旧事了。
是啊,四十多年前,因为想着要看比翻译本的《老子》更多一点的东西,他从瑞典远赴四川。穿一领蓝布大褂,让路人指指点点。那一年,那红颊的中国少女多么善睐其明眸啊!他终于娶了少女,把自己彻底给了中国。
但这一霎,我却深爱他介乎顽皮和无辜之间的眼神。终其一生,我想他都是那个简单的穷学生,吃简单的饭,喝简单的酒,用直来直往的简单方法为人处世,并且珍惜每一口美味,爱惜每一分物力。
多么好的人生滋味啊,都一一藏在那不忍拿走的半盘豆腐里。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中时”·人间版》副刊
《某个不曾遭岁月蚀掉的画面》
她是我的朋友,我们很谈得来,那是三十年前,我读中学时候的旧事了。
我们彼此交换看作文簿,那大概等于成年人准许别人看自己的企划案吧!我隐隐了解她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不是同一个阶层的人,但谁管那些呢?我们交往很久,彼此却没有去过对方的家。那时代女孩子放学和回家的时间都经父母算准了,去同学家玩是不成理由的。
有一天,大概是由于考试,提早放了学——我终于去她家玩了。她家离学校很远,是一个军眷村。其实我家也是军眷村,但低军阶的眷村不一样,看来像船舱,一大横排,切成许多豆腐块似的小间,而每间小豆腐都低矮仅能容身,倒也别有它的温暖。她的父母极老,她是晚生的小幺女,大的嫁了,她等于是独女,很得宠,我也因此变成小小的上宾。
她家可能算眷村的“有钱人”,因为开了一间小杂货店,不时有小孩跑来买一颗泡泡糖或一瓶醋之类的。似乎还不到吃饭的时间,但不知为什么,二老忽然下决心非让我们吃一碗面不可。他们是旗人,说起客气话来特别好听,特别理直气壮。
面下好了,是麻酱面,只两碗,二老自己不吃。她的父亲负责把麻酱调稀拌匀——并且端上桌,然后他转身走开。他的脚不好,走起路来半步半步地磨蹭着往前挪。
就在他转身的那一霎,我忽然看见,他背过身去把筷子头上残余的芝麻酱慢慢舔食了。虽然看不见脸上的表情,但却直觉地知道他正十分珍惜地享受着筷尖那一点点麻酱的芳香。就由于那种敬慎珍重,使人不觉其寒酸,只觉得在窥伺一场虔诚恭逊近乎宗教的礼仪。
不知为什么,这样一个画面,在我心中竟保存了三分之一世纪而不能忘记。
——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日《“中时”·人间版》副刊
《我自我的田渠归来》
近午的时候,暴雨倾盆,而且打雷。闪电劈过城市上空,整条巷子里有四五辆汽车给触动了防盗系统,纷纷大叫起来。一时之间,令人重温了古代山林里百兽咻咻狂啸的场面。
我放下手边的工作,直奔顶层阳台。果不出所料,排水孔给落花坠叶堵住了,积水盈尺,我赤着一双脚去清花叶,大水忽然找到出路,纷纷把自己旋成涡流,奔泻而下。
我全身湿透——既然湿透,也就没什么可忧可怕的了。干脆又探视了一下石斛兰、荷花、非洲凤仙和软枝黄蝉,倒有点像省主席微服出巡似的。
然后下楼,脱掉衣服,用大毛巾把自己擦干,又盛了一碗红心番薯汤来喝。汤里放了两片姜,暖辛暖辛的。这种煮法是某次在大屯山上跟山民学的。此刻热汤放在景德镇制的“米粒瓷碗”里饮来,竟觉这汤简直从口从舌从咽喉一路流到心窝里去了。真的,有些食物对我而言,是只入心室不入胃囊的。
我犹嫌它不够甜,于是又去冰箱里找来一罐从维琴妮亚农场买来的枫糖浆,加了一勺进去。于是,恍惚之间仿佛西半球的山川精华来和这中国大地里的红心番薯彼此融会贯通,连成一气,并且安静安详地盛在我的碗盏里,像澄澄湖水里卧着一丸艳艳的夕阳。
这一天,觉得自己极幸福;这一天,我是辛苦的老农,刚整理完田渠回家,浑身为雨水湿透,于是喝一碗红心番薯汤;这一天,我活得多么理直气壮啊!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中时”·人间版》副刊
《公平》
他年轻——也许不是太年轻,可能是三十五,或三十六七。青春的光彩未失,却又可以偷偷地炫耀一份“安全的沧桑感”。(真正年华老去的沧桑感,美则美矣,却是回光返照的天鹅之歌。)
如果要为他加个头衔,大概是“旅美学人”吧!他写一点诗,诗里有一点甜质,有一点浪漫——很适合发表的那一种。
诗尾也许注着“寄自××”,那异国城市的名字是如此引人遐思,隔着重洋,那些奇特的拼音念起来清朗如花坞碎浪、梦里梵音。
有位文笔老辣的杂文作家,有次出国旅游,人到国外,赶紧写一稿寄回,文末巴巴地注上“寄自×城”,她开玩笑地说,好歹也要风光它一回哩!
然而那学人却篇篇都附上一个美丽的地名,令那些屡遭退稿的年轻孩子又妒又羡。
是痖弦的名句:“短短的篇幅,淡淡的忧郁,浅浅的哲思,帅帅的作者。”
这样的话,简直是为此人说的。
然而,那人的诗却写得十分枯索黯败,如一卷因受潮而失真的录音带,属于人的原声和节奏全不见了,听来只知道有字有句,也听得懂那字那句,却全然不能碰触到一寸皮肤,更不要说触心了。
我忽然觉得这大约就是公平了!那人虽拥有这个世界所艳羡的少壮和学位,上帝却并没有把才气给他。他生命的筹码已够多,足以让他去纵横捭阖了——至于才气,上帝一向十分悭吝,毕竟,拥有才华便也是“小型的创世者”了,上帝岂肯将他自己的看家本领随便分给人呢!
——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中时”·人间版》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