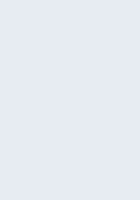《不知道他回去了没有?》
车子是一辆野鸡车,拉够客人就走的那种。路程是从中坜到台北——一小时的因缘聚散。
大家互不相识,看来也没有谁打算应酬谁,车一上路,大家就闭目养起神来。
“慢点,慢点,”后座有一个老妇人叫起来,“不要超车——”
“免惊啦!”司机是志得意满的少年家,“才开一百就叫快,我开一百四都不怕的。”
大家又继续养神,阳光很好,好得让人想离开车子出去走走。
“要说出事情,也出过一次的啦!”没有人问他,他自顾自地说起来,“坏运,碰到一个老芋仔(指老兵),我原来想,这人没有老婆儿子,不会来吵。后来才知道,他的朋友不知有多少哇!全来了,我想完了,这下不知要开多少钱。最后他们老连长出来说话了,他说:‘人死了,不用赔。火葬费我们大家凑,也不要你出。但有一天可以回大陆的时候,你就要给他披麻戴孝,把他送回安徽去下葬。’”
“安徽?阿娘喂,我哪里知道安徽在哪里啊?”
“可是那时候也没办法,他又不要钱,我只好答应了。现在那老连长还一年半载就打电话来,我想想就怕,安徽是不是比美国还远啊?”
——这是十五年前的旧事了,开放回大陆探亲以后,我常想起司机口中那遭人撞死的老芋仔。他,和他的骨灰,不知有没有回去?不知有没有人为他披麻戴孝地送他回到安徽?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二日《“中时”·人间版》副刊
《盒子》
过年,女儿去买了一小盒她心爱的进口雪藏蛋糕。因为是她的“私房点心”,她很珍惜,每天只切一小片来享受,但熬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也终于吃完了。
黄昏灯下,她看着空去的盒子,恋恋地说:
“这盒子,怎么办呢?”
我走过去,跟她一起发愁,盒子依然漂亮,是闪烁生辉的金属薄片做成的。但这种东西目前不回收,而,蛋糕又已吃完了……
“丢了吧!”我狠下心说。
“丢东西”这件事,在我们家不常发生,因为总忍不住惜物之情。
“曾经装过那么好吃的蛋糕的盒子呢!”女儿用眼睛,继续舔着余芳犹在的盒子,像小猫用舌头一般。
“装过更好的东西的盒子也都丢了呢!”我说着说着就悲伤愤怒起来,“装过莎士比亚全部天才的那具身体不是丢了吗?装过王尔德,装过塞缪尔、贝克特,装过李贺,装过苏东坡,装过台静农的那些身体又能怎么样?还不是说丢就丢!丢个盒子算什么?只要时候一到,所有的盒子都得丢掉!”
那个晚上,整个城市华灯高照,是节庆的日子哩!我却偏说些不吉利的话——可是,生命本来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吗?
曾经是一段惊人的芬芳甜美,曾经装在华丽炫目的盒子里,曾经那么招人爱,曾经令人钦慕垂涎,曾经傲视同侪,曾经光华自足……而终于人生一世,善舞的,舞低了杨柳楼心的皓月;善战的,踏遍了沙场的暮草荒烟;善诗的,惊动了山川鬼神;善于众敛的,有黄金珠玉盈握……而至于他们自己的一介肉身,却注定是抛向黄土的一具盒子。
“今晚垃圾车来的时候,记得要把它丢了,”我柔声对女儿说,“曾经装过那么好吃的蛋糕,也就够了。”
——一九九二年三月八日《联合报》联合副刊
《可爱》
酒席上闲聊,有人说:
“哎哟,你不知道,她这人,七十岁了,雪白的头发,那天我碰到她,居然还涂了口红,血红血红的口红呢!”
“是啊,那么老了,还看不开……”
趁着半秒钟的“话缝”,我赶紧插进去说:
“可是,你们不觉得她也蛮可爱的吗?等我七十岁,搞不好我也要跟她学,我也去抹血红血红的口红!”望着惊愕地瞪着我的议论者,我重申“女人到七十岁还死爱漂亮,是该致敬的”。
记得有一年,在马来西亚拜访一位沈慕羽老先生。古老的华人宅第中,坐镇着他九十多岁的老母亲,我们想为她拍一张照,她忽然忸怩起来,说:
“等一等,我今天头发没梳好。”她说着便走进屋去。
在我看来,她总共就那几根白发,梳与不梳,也不见得有差别。可是,她还是正正经经地去梳了头才肯拍照。
老而爱美的女子别有其妩媚动人处。
又有一次,听到有人批评一位爱批评人的人。
“可是,听你们说了半天,我倒觉得他蛮可爱,”我说,“至少他骂人都是明来明去,他不玩阴的!人到中年,还能直话直说,我觉得,也算可爱了!”
有人骂某教授,理由是:
“朋友敬酒,他偏说医生不准他喝。不料后来餐厅女经理来敬酒,他居然一仰脖子就干了,真是见色忘友!”
“哎呀!”我笑道,“此人太可爱了。酒这种东西,本来就该为美人喝的,‘见色忘友’,很正常啊!”
我想,我动不动就释然一笑,觉得人家很可爱,大概是由于我自己也有几分可爱吧。
——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中时”·人间版》副刊
《“黄梅占”和稼轩词》
我在一樽小小的玻璃罐子前站住了。只因罐子上有三个字:
黄梅占
这里是香港的超级市场,架上货色齐全,而顾客行色匆匆,各人推着购物车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唯有我,为一个名字而吃惊驻足,只因为它太细致太美丽。黄梅和占卜放在一起会是什么意思呢?记得辛稼轩的词里有一句:
试把花卜归期
才簪又重数
写的是女子在凄惶的期待岁月里变得神经质起来。于是拔起鬓边的春花,十分迷信十分宿命地数起花瓣来,想在一朵花的数学里面去找出那人几时回家的玄奥——然而,她对答案并不放心,她决定从头再数一遍……
而这小小玻璃瓶中的黄梅,又如何用以占卜呢?黄梅是指蜡梅花吗?梅花是五瓣的,而用来占卜的花应该是重瓣的才对。唉!“花卜”真是一种美丽的迷信。自从有了长途电话,数着花瓣计算归期的企盼和惊疑都没有了,“重逢”竟成了时间表上确确实实的一道填充题。
我是从稼轩的词里认知了那一代女子的清真明亮和婉约多姿的。
而眼前的这“黄梅占”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仔细拿起瓶子一看,不禁失笑,原来只是一瓶果酱!香港人用音译的方法把果酱译成“占”。黄梅则指的是一种经由桃杏嫁接而长出的水果。虽然觉得被标签摆了一道,我还是买了一罐“黄梅占”——像一个虚荣的女子,既被甜言蜜语所骗,便也不打算拆穿。回到家,慢慢地品尝,因为有大块果肉,嚼起来十分甘美。这,或者也算古诗词的某种滋味吧?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五日《“中时”·人间版》副刊
《老教授所悬的赏》
她大三,在公认最好的T大读书。
这几天是寒流过境的日子,也是停课考试的季节,整个校园有点狩猎的意味,人人摩拳擦掌,等待逐鹿天下。
她走来逛去想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读书位置。
忽然,远远在布告栏里,她看到一个大大的“赏”字。
她近视,需要走近才看得清楚,但为什么要走过去看呢?她问自己,是单纯的好奇,还是对一切赏格都有一份贪婪?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事赏些什么呢?
按照惯例,一切的布告栏都该标出张贴人的名号,以示负责。她看了一下,原来是植物系的李教授张贴的。她在通识课上选过这位教授的课,是一位很具真性情的老教授。
全张布告是这样写的:
赏枫
要趁早
钱穆先生纪念馆9:00~17:00
枫要正红(周内即逝)
美景共赏
地址:外双溪东吴大学内素书楼
所署的日期是一九九二年一月九日,布告的左上角还画了一枚五角的枫叶,中间涂上红色的网格。
布告是影印的,想来老教授在全校各处悬了不少张这种“赏”吧!
不知有几人会在考试季节去赏枫,但至少,她感到一树枫叶的绛红在眼前炫其光彩——透过老教授所悬的赏。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中时”·人间版》副刊
《这些石头,不要钱》
朋友住在郊区,我许久没去他家了。有一天,天气极好,我在山径上开车,竟与他的车不期而遇。他正拿着相机打算去拍满山的“五节芒”,可惜没碰上如意的景,倒是把我这个成天“无事忙”的朋友给带回家去吃饭了。
几年没来,没料到他家“焕然一旧”。空荡荡的大院子里如今有好多棵移来的百年老茄冬,树下又横卧着水牛似的石头,可供饱饭之人大睡一觉的那种大石头。
我嫉妒得眼珠都要发红了,想想自己每天被油烟呛得要死,他们却在此与百年老树共呼吸,与万载巨石同座席。
“这些石头,这些树,要花多少钱?”
“这些吗?怎么说呢?”朋友的妻笑起来,“这些等于不要钱。石头是人家挖土,挖出来的,放在一边,我们花了几包烟几瓶酒就换来了。树呢,也是,都是人家不要的。我们今天不收,它明天就要被人家拿去当柴烧。我们看了不忍心,只好买下来救它一命。”
看来他们夫妇在办老树收容所了。
“怎么搬来的?”
“哈,那就不得了啦!搬树搬石头可花了大钱,大概要二十万呢!”
真不公平,石头不要钱,搬石头的却大把收钱。
我忽然明白了,凡是上帝造的,都不要钱,白云不以斗量求售,浪花不用计码应市。但只要碰到人力,你就得给钱。水本身不要钱,但从水龙头出来的水却需要按度收费。玉兰花不要钱,把花采好提在花篮里卖就要钱了。
如果上帝也要收费呢?如果他要收设计费和开模费呢?果真如此,只要一天活下来,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变得赤贫,还不到黄昏,我们已经买不起下一口空气了。
我躺在这不属于我的院子里,在一块不经由我买来的石头上,于一个不由我设计的浮生半日,享受这不须付费的秋日阳光。
——一九九二年二月五日《“中时”·人间版》副刊
《传说中的宝石》
那年初秋,我们在韩国庆州吐含山佛国寺观日出。
清晨绝冷,大家一路往更高更冷的地方爬上去,爬到一座佛寺,有人出面为那座并不起眼的佛像做一番解释:
“哎哟!你们来的时候不对!如果你们是十二月二十二号那天来,就不得了啦!那菩萨的额头中间嵌着一块宝石呢!到了十二月二十二号那天早晨,太阳的角度刚好照在那块宝石上,就会射出千千万万道光芒,连海上远远的渔船都看得见呢!”
我们没有看到那出名的“石窟庵菩萨”的奇景,只好把对方词不达意的翻译放在心上,一面将信将疑地继续爬山路。那天早晨我们及时到达山顶,兴奋地从云絮深处看那丸蹦跃而出的血红日头。
每想起庆州之行,虽会回想那看得到的日出胜景,却不免更神往那未曾看到的万道华彩。其辉灿绚丽处,果如传说中说的那么神奇吗?后来又听人说,那块宝石早就失窃了。果真失窃,那么,看不到奇景的遗憾,就不仅是我一个人的了。这件事在我心里渐渐变成一件美丽的疑案,我常想,如果宝石尚在,每一年的某月某时某分,太阳就真可以将一块菩萨额头的宝石折射成万道光芒吗?我不知道,然而,我却知道——
如果,清晨时分我面对太阳站立,那么,我脸上那平凡安静的双瞳也会因日出而幻化为光辉流烁的稀世黑晶宝石!不必等什么十二月二十二日,每一天的日出,我的眼睛都可自动对准太阳而射出欢呼和华彩——并且,这一块(不,这两块)永不遭窃。除非,有一天,时间之神自己亲手来将它取回。
我于是憬悟到自身的庄严、灿美,原来尤胜于在深山莲花座上趺坐的石佛。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九日《“中时”·人间版》副刊
《致友人谢赠》
——寄S
谢谢你赠我一袭睡衣。
是何处裁得的湖蓝,是哪里抽来的霞缕,织就这样一身柔和如秋芒的睡衣。
睡衣大约也是某种旅行装吧?穿上它,可以出发,前去赴梦。而梦泽千里,任人驱驰,那么,我想你赠我的,不仅是睡衣,还是梦乡的度牒了。我心感激,因为一切与梦相接的导体都神秘幽玄,令人迷乱欣喜。
唐人诗中每有谢友人赠茶的绝句,茶是山云相亲而结成的一叶幻象。饮茶的人饮的是片状的山脉和固体的朝露。留山风于舌尖,观青岚于茶烟,如此这般的魔术幻境,焉得不雀跃答诗。
我不能诗,只好以文来谢你赠衣之情。
但首先容我说,你不乖,不是天主的好女孩。你病了,我去看你,但我却不是去看“一位病人”,我是去看一个在人世间跋生活之艰、涉创作之险的女子。我去看你不是缘于怜悯,是出于尊敬。你却耿耿于怀,觉得过意不去。你叨叨念念,不能忘,也不肯忘。
亲爱的朋友啊,你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去承受别人的善意呢?如果蓝天可以忘记白云的拂拭,如果老树可以忘记黄鹂的啭歌,你也快快忘了我那天小小的造访吧!否则我也不安啊!你病了,你的膝盖不好,这件事就像古希腊神话里“阿喀琉斯的脚跟”一样无奈。生病,在我看来,是大事,生病的人应该在自己的职业栏里填上“生病”二字才对。和病缠斗,是一份全职(full-time job),是全天候的值勤,生病是亟须“敬业精神”的呢!
睡衣极美,但下次如果你想到送我什么,请送我一颗大喇喇的受之无愧的心。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中时”·人间版》副刊
《饮者》
在中国大陆冬季的盛雪中行山路,我到小铺里买了一小瓶100 CC的四川茂公酒厂出的大曲,倒也不是因为想喝,而是觉得放它在皮包里便有份安全感,有份暖意,仿佛偷藏了一部自力发电的内燃机。
走离山道,来到小城,那城叫“大墉”。整个城都仿佛仍是古代的墉国,静静的、悠悠的、尘埃仆仆的。
我走到人声沸扬的市集上,东张西望,望到一个卖酒的女人。那女人像个魔法师,紧紧看守着面前一桶桶神奇的魔术,眼神淡淡的,仿佛穿越时空。我走上前去一一问酒名,她也一一答复:
“这是果子酒,什么果?很多种果子说不清啦!这是米酒,这是苞谷酒……”
“等一等!等一等!这是苞谷酒吗?”
“是,是苞谷酒。”
“我要买一点。”
“你有酒瓶吗?”
原来这里打酒要自备酒瓶的。我当机立断,打算把我的大曲酒找个人送掉,只留瓶子。旁边另外有个女人立刻去找了个杯子盛了我的酒拿走了。
“奇怪哩,大曲贵,苞谷酒便宜,你这人怎么倒掉大曲去买苞谷酒?”
我笑而不答。
终于买了100 CC的苞谷酒,一路走一面抿上一小口,觉得仿佛在吞食液态火焰,怎么向市集上的那些人解释呢?只为读过古华的《芙蓉镇》,那小说里有一坛苞谷酒。此番买酒只为领略故事中郁郁烈烈的风情,只为知道世上有某种强劲力道。
那100 CC的酒,一直回到台湾还剩一口没喝完呢!但我却自许为“饮者”,急于饮下“未知”。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八日《“中时”·人间版》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