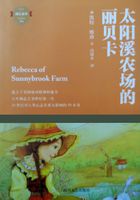没过几日,一些见风使舵的占星方士趁机跳出来,说广陵有天子之气。司马炎最是热衷祥瑞之说,于是封年仅四岁的孙子司马遹为广陵王,邑五万户。
如此一来,关于东宫易主的流言蜚语再也没人敢传。
当一切尘埃落定,那封召司马攸回朝的急诏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切,远在凉州的司马攸是不知道的,他只知道,诏命如此紧急,朝中必有大事发生。他怀疑皇帝身体欠安,召他回去主持大局,毕竟司马炎身体江河日下,旋即,他猛抽自己一巴掌,他不该生出这个想法。
在他出发那日,一场暴雪席卷了晋帝国西部边陲,雪花大如瓦片,纷纷扬扬,从敦煌到武威,再到长安,到处是一片素白世界。那片流血漂橹的惨烈战场被埋在数尺厚雪中,一切都没了踪迹。冰雪之上,万籁俱寂,山川,树木,一如原始般纯粹。
官道被大雪掩盖,了无痕迹。司马攸众人刚出武威不到百里便无法前行,于是找了一个破败的山神庙安下身来。山神庙非常大,墙壁用石块堆砌而成,足以容纳百十人,四周用巨大木柱撑起,屋顶一角已被积雪压塌,露出铅灰色的天空。神像早已不见,仅留下一块三丈见方的底座。庙内有些干草,众人收集到一处,生火取暖。
他有些想念张轨,那个一腔热忱豪气冲天的年轻人。他命人翻遍了战场的每个角落,一无所获。这样也好,好歹留着一丝念想,司马攸这样安慰自己。山庙破败不堪,冷风顺着墙缝灌进来,刺骨的冷。司马攸裹紧身上的羊皮,又往火堆里添了一把柴,火苗登时旋起了舞。
映着火光,司马攸发现墙上似乎有字,于是,他点起一支火把,抵近观察。石壁上刻画着简单粗犷的线条,线条组合成人和牛羊以及山川树木的形状。有些复杂的线条甚至勾勒出人的穿着,从装饰上看,应该是胡人。
壁画脉络清晰,只见第一幅画着两匹马,似在争斗;后面一幅画着两个人,一人直立,一人弯腰作揖;再往后便是浩大的迁徙及行猎画面。司马攸估摸,大约这里水草丰腴,胡人便定居下来,并修建了这座庙宇。
司马攸仿佛能看到数十万人迁徙的宏大场面,这些人背井离乡,去一个完全未知的地方放牧,修建屋舍。沿途其他部落像豺狼般尾随着,稍有不慎便会被撕下一块血淋淋的肉来。而迁徙中的人们只能像牛羊一样舔舐伤口,只要一息尚存,就得一直向西。
当然,如果遇到比较弱小的部落,他们也会化身豺狼。这就是沿袭数千年甚至上万年的自然法则。而汉人,有时是凶残的豺狼,有时又是无助的羊羔。
门外传来几声狼吼,司马攸辗转反侧。
突然,守夜士兵夺门而入,急促喊道,“敌军来袭!”,声音在寂静的旷野中洪亮如终。
紧接着便是大队人马踩踏积雪的窸窸窣窣声。司马攸暗道不好,迅即夺出庙门,只见外面火把点点,呈扇形向山庙逼近。
久临兵阵的兵士们亦被惊醒,他们枕着箭筒席地而眠,若非大雪,七八里外都能听到敌军接近。伴随者一阵杂乱的兵戈撞击声,士兵们列队迎敌。亲兵队则紧紧护着司马攸,寸步不离。
敌军足有千人之众,都是胡人骑兵。他们每人握一把半月胡刀,见人便砍。
司马攸所带的百余兵士虽拼死抵挡,仍被冲的七零八落,眼见全军覆没。亲兵队簇拥着司马攸骑上快马,往东疾驰。然而胡人马快,不消几里便已追上,亲兵们随即拨转马头,冲入敌阵。转瞬间便只剩司马攸孤身一人。
又奔出一里地,此时天已放亮,司马攸回身看到胡人愈来愈近,心里着急万分,只得奋力挥舞马鞭,祈祷马儿跑得快些,再快些。
突然,马儿一声悲鸣,扑跌于地,将司马攸重重甩到雪里,司马攸直感到阵阵晕眩,继而胸口发闷,喷出一口血来。
待他清醒,远远发现另一队胡人骑兵疾驰而来,转瞬已到身前。
司马攸闭眼叹道,“想不到我竟命绝于此!”,索性不再闪躲。
这队骑兵并未睬他,直直向他身后的敌军冲去,一时间杀声大作。与先前敌军相比,这些人气力大得惊人,一刀砍下,人马俱裂;此外,他们武艺甚好,冲杀时互为掩护,与之相比,先前那伙人倒是莽夫流寇般。
敌军源源不断赶来,这队骑兵陷入苦战,左右支绌。正在此时,一声低沉的号角声响起,在寂静的旷野中传出极远。
这是军阵之中冲锋的号声。
敌军闻之迅速逃窜。
等战场平静下来,雪地上已是大片鲜血。
地平线上,隐隐现出一匹白马,上面坐着一个身着白衣的少女。少女浑身洁白,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若非东边的朝霞映衬,谁也不会发现这一人一马。
司马攸遥望少女慢慢走近,更加震惊、疑惑。
“想不到,名满天下的齐王大人,竟会落得这般田地。”少女下马,对司马攸冷笑道。
一旁的胡人见到少女,纷纷拊住胸口,低头行礼。
司马攸见状,心中的惊疑无以复加,这位年纪轻轻的女子,竟是胡人的首领!他费尽力气,颤巍巍地站起身,拂去身上积雪,行礼道,
“想必是阁下救了我,若非阁下搭救,我已是死去之人,阁下救命之恩,在下不胜感激!敢问阁下芳名?日后也好答谢!”
“不必!你司马家的报恩法子,小女子万万经受不起!”少女嗤之以鼻。
“阁下认得我?”司马攸惊道。
“岂止认识,你司马家的每一个人,我都认识!”少女咬牙切齿、一字一顿道。
“姑娘,你既救了我,有些话我便不该说,司马氏乃当今皇室,姑娘当尊重一二”。见少女口无遮拦,司马攸索性不再称呼“阁下”,而是直呼“姑娘”。
“哼!”少女冷冷道,“我姓甚名谁不重要,也不需你答谢,你我今后还会相见,到时你自然知晓。”
少女翻身上马,“你不是有急诏在身吗?速速上路吧!大晋皇帝已对你生疑,只怕洛阳的腥风血雨不见得比凉州少,齐王大人好自为之!”
再不管司马攸如何询问,少女自顾自离去,马儿在三丈之外停住,少女仿佛记起什么,转身道,
“张轨还活着,至少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这话仿佛比司马攸遇刺被救更令他兴奋,张轨还活着!张轨还活着!
“敢问姑娘,张轨在哪?又是被何人所救?!”
回答他的,只有一阵马踩积雪的窸窸窣窣声。
两月后,当司马攸历尽艰辛回到洛阳,早已物是人非,平日里与他亲近的大臣,不是被罢黜便是寻个由头外放,就连三朝老臣张华都被贬幽州。人们都希望他早日前往齐地,不要再生事端。
一切已成定局。
司马攸不贪恋皇位,他只想辅佐皇兄和不成器的太子,只想为大晋社稷熬白青丝,死而后已。但几乎所有人都在误会猜忌,只有王妃能理解他,只有在王府他才不会显得那么多余。王妃劝他进宫面圣,把心中所想和盘托出,哪怕消弭一丝误解也是好的,不料被司马攸拒绝,陛下能信吗?既然陛下已经起疑,再去反倒越抹越黑,不如早些回齐地。
连日来,司马攸以病为由,不再上朝。他确实是病了,自凉州遇刺,跌落马背时起,便受了内伤。他也不见任何生人,只把自己闷在屋中,或奋笔疾书,或鲸吸牛饮,借此遣愁。偶尔来了兴致,他会和王妃谈及当年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谈及那个战乱纷争的年代。
他想起凉州那个出现数次的女子,却怎么也猜不透。从女子的语气来看,似乎对司马氏有着很深的成见,女子气质高雅,绝非出身一般人家…
莫非,莫非是曹家的后人?!司马攸感到后背发凉。他急匆匆喊来王妃贾荃,让她去查曹氏宗谱。
几日后,贾荃告诉他,曹髦子嗣并无记录,高贵乡公府邸在一场大火中被烧得干干净净,她问过太宰张华,张华只道不知。
而其他的曹氏宗族,大半被屠戮,余下的,有名有字的,没甚么公主。
司马攸猜测,肯定有人动过手脚,曹髦的死因,注定他必须湮灭在历史的尘烟里,这两字最好连同主人一齐烂掉。
贾荃觉得司马攸多虑了,从凉州回来,她的夫君有些疑神疑鬼,经常一发呆便是半晌。
昔日门庭若市的齐王府,一时变得门可罗雀,所有人都避之不及,生怕触怒皇帝,吃不了兜着走。然而这日,有许多人备着礼物,登门造访。
来人是刘渊和拓跋悉鹿,司马攸摆摆手,示意不见。王妃劝道,若只是刘渊,可以不见,拓跋悉鹿毕竟乃他国使者,又是鲜卑大首领,拒之门外非待客之道。于是,司马攸强打精神,到前厅迎接。
拓跋悉鹿此行目的是拜会当朝齐王,由刘渊作陪。司马攸甚是厌恶刘渊,极少与他搭话。倒是拓跋悉鹿拘礼甚恭,言语谦逊。司马攸与他谈论代地风物,言谈甚欢,说话间,司马攸知晓这位鲜卑大首领乃沙漠汗之弟。
“贵兄沙漠汗与我乃故交,他为人光明磊落,不拘小节,与我甚合得来。”司马攸望着门外,陷入沉思中。
“那齐王可知兄长往事?”拓跋悉鹿小心翼翼地问道。
司马攸道,“略知一二,不过与我相比,你身边这位左都尉应该知晓的更多。”
“是啊,当年沙漠汗还救过在下一命呢,不知齐王可否记得?”刘渊嘴角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他所指的,是一件往事。当年刘渊入洛阳不久,司马攸便上书皇帝,说此人气度不凡,将来必成祸患,定要严加看管。有一次,好友王弥回乡探亲,刘渊忍不住对他吐露心声。不料刚好被司马攸听到,于是,司马攸立即上奏陛下除之后快。幸得王浑、沙漠汗等一些臣子劝谏才作罢。
“刘渊,我不能奈你何,你若不思悔改,继续狂悖下去,必有自取祸患之日!你且...!”司马攸喘着粗气,额头青筋暴起,一口气没上来,竟憋得满脸通红,只得拊着胸口,踉踉跄跄地瘫坐在胡床上。王妃贾荃正在偏厢缝织新衣,听见屋内似是吵架,急急冲进屋来。
“我刘渊如何尚不得知,眼见你齐王将要日薄西山也。”刘渊冷笑着,语气阴森怪异。
“刘渊!吾家齐王春秋鼎盛,竖子休要妄言!”贾荃柳眉倒竖,愤然道。
拓跋悉鹿并不知两人过节,只得两头陪好。“这是为何!大家都请息怒,就算给拓跋氏三分薄面。”拓跋悉鹿坐立不安,代地常吃烤肉,他感觉自己就是那片滋油的羊炙。
“你乃鲜卑大首领,又是拓跋沙漠汗之弟,于情于理,我当厚待你,刘渊狼子野心,乃喂不熟的草原豺狐,你万不可与他亲近。”司马攸缓缓道,他脸色煞白,皱纹横生,竟显得苍老许多。
会客无法再进行下去了,王妃强压怒火,起身行礼道,“诸位,齐王今日不宜见客,来日必登门致歉,各位请自便。”
这是下逐客令了,拓跋悉鹿和刘渊只得起身告辞。
齐王妃也不送客,连正眼都不瞧一下,任由他们离开。
“你乃堂堂大晋齐王,何必跟一只丧家之犬过不去。”贾荃一边为夫君捋背,一边小声埋怨着。
“刘渊包藏祸心,绝非善类,这十余年来,朝中大臣被他笼络的十有七八,连杨骏兄弟都被他蛊惑,此人若不除,将来亡我大晋者,必是匈奴蛮子!”
“大晋国泰民安,即便要亡,也都是身后十好几辈的事了,你还是先顾好自己吧!你最近心里烦懑,整日关在屋内,这样可不行,人哪能不见阳光呢?”
司马攸被说得心动,二人带着司马冏,出了门。
拓跋悉鹿首次拜会齐王便有此出,非但脸上无光,心中也甚是忐忑,他在心里责备刘渊口不择言,却也不好明说。刘渊则不以为然,遣退仆从,拉着他进入一家酒肆,找一个无人的角落坐定。
二人推杯换盏,不多时便饮完一大坛子。拓跋悉鹿问他,方才齐王府,到底是为何。
“此事说来话长,司马攸不止一次在汉人皇帝面前诋毁我,若非乃兄和征北将军说情,我早已成刀下亡魂,此仇不得不报。”
拓跋悉鹿哑然失色,早知有这一遭,何必要带着他去拜会齐王呢。
刘渊问道,“你可知乃兄因何而死?”
“兄长在中土待得久了,不免沾染汉人习气,逐渐在代地推行教化,引发数位首领不满,一日,他用一张空弓射下飞雁,人们皆言他会巫术,事情闹到父王那里,眼见大乱将起,父亲也保不得他。”
“哈哈哈,什么空弓,是不是那个?”
刘渊指指楼下,大街上有两个小童正拿着“空弓”,射远处的酒坛子。只见小童拉开牛皮绳,一松手,酒坛应声破碎,店家听到响声,抽出棍棒骂骂咧咧地追赶,小童一边跑,一边回头做鬼脸。
“这...”拓跋悉鹿瞪大眼睛,呆坐半晌,突然嚎啕大哭,“王兄,你死得好冤枉!”
“拓跋兄节哀,沙漠汗沾染汉人习气,这我是知道的,他仰慕汉人教化,苦读诗书,神似汉人士大夫,一个深受诗书礼仪余毒的世子,如何当鲜卑人的王?他的死,你也不必太过悲伤了。”刘渊口干舌燥,满饮一大碗酒,继续说下去:
“仰慕中土文化,却也无可厚非,他曾说过,回到代地后,他要设立百官,开设学馆,像先秦那样积数世之功,建立能逐鹿中原的文明之国。”
“他果真如此说过?”拓跋悉鹿诧异万分。
“千真万确,况且此话并非我一人知晓。你可知,你各部首领诛杀沙漠汗是受人挑唆?”刘渊贴近拓跋悉鹿,声音几乎弱不可闻。
“受人挑唆?”拓跋悉鹿更是疑惑,这位匈奴左贤王身上似乎藏着无数秘密。
“没错,挑唆之人位高权重,想必许各首领多金,以此架空先王,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什么目的?”
“这就不大知晓了,总之,中土朝廷想法设法削弱你我各族,要的是无力与他们为敌,我和乃兄及其他世子皆然,表面是客,实则为质。”
拓跋悉鹿急于想知道到底是何人挑唆,但无论如何追问,刘渊始终三缄其口,只道饮酒。
刘渊还告诉他,当年与沙漠汗一同离开的,还有一名汉人女子,女子乔装成沙漠汗仆从,这才无人发觉,女子的身份他并不知。
拓跋悉鹿冷气倒抽,原来歌舞升平的大晋帝国,私底下竟有这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沙漠汗的死乃有人刻意为之,还有,那个汉人女子是谁?沙漠汗回代地时,他并不曾见过。
帘子动了一下,像是风为之,刘渊急忙掀开,帘后并无人。
楼下,司马攸夫妇牵着小司马冏,刚刚走过。
司马冏长到三岁,与父母出游的次数屈指可数。父亲不在的这些日子,小家伙学会了很多新词,卫瓘最近正在教他《博学篇》。他指着路旁一个卖糖人的老伯,“爹爹,糖人!”
刘渊啐道,“呔!真是阴魂不散!”
临近岁首,洛阳城到处张灯结彩,人们洒扫庭院,剪切窗花,巷子里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不绝于耳,年前那场大雪消融殆尽,从大街上到角落里,到处都洋溢着欢乐气氛。
宫里也不例外。
经过上次大病,司马炎稍稍收敛些,整个冬天再未宠幸西域美人儿,只留宿芙蓉殿、承光殿以调养身体。此时,司马炎正在芙蓉殿的暖床上打盹儿,杨芷和丫鬟玉兰在一旁刺绣,那幅鸳鸯戏水图已完工,就在司马炎脑袋下面枕着,她俩这次绣的是“松鹤延年”。
杨芷入宫多年,对夫君的脾气秉性摸得通透,夫君往往在身体抱恙的时候才想到她这个皇后,每次来都是病怏怏的。她的心早就枯成了灰,她的爱宛如灰烬上的一点儿火星,只有在黑暗中才能显现。皇帝来就来,不来也不强求,这一年来,她把讨好皇帝的心思,把指摘众妃的心思都用在了蜀绣上,如此一来,内心的寂寞便少了许多。
安谧的气氛没持续多久,一个丫鬟慌慌张张进了屋,见皇帝小憩,便悄悄对皇后禀报,东宫又出了事。太子妃贾南风杀了良娣,整个东宫闹翻了天。
这还了得!杨芷花容失色,赶紧告诉司马炎。
司马炎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立即吩咐侍卫,摆驾东宫。
东宫,院子里一条长长的血迹,从侧屋一直延续到大门口,良娣的尸体被一张席子卷着,两头不断流出暗红色液体。不远处,始作俑者贾南风披头散发坐在地上大喘粗气,她满脸怒色,手上,身上全是血。手边有一把长戟,血迹斑斑,戟尖儿上还挂着零星皮肉。她面皮本就乌黑,眉毛边有颗痣,快占了半边脸,此时更显得面目狰狞,神似地府勾魂儿的黑无常。
司马衷在一旁瑟瑟发抖,不知所措。
司马炎等不及通报,直接闯进东宫。
眼前一幕让他眼前一黑,差点晕倒;杨芷则以袖掩目,不忍直视。
司马炎怒不可遏,须发皆抖,抢起地上长戟,像一道雷向贾南风横劈过去,好在众侍卫反应快,戟尖儿在离贾南风脑门前不到一尺的地方停住,剧烈摇晃,贾南风早被吓得魂不附体,摊作了一团烂泥。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司马炎怒喝,“你们放开,朕!朕今天要除了这个妖孽!妖孽!”
司马衷急忙跪下,双膝着地,踉踉跄跄过来,护住妻子。
贾南风终于没有殒命当场。
司马炎命众侍卫把席子打开,就在一瞬,众人纷纷作呕,司马炎靠过去,只看到一团人形物体,汩汩鲜血从物体里面涌出。
司马炎让侍卫召集东宫所有人等,问明原因,事实很快水落石出,死去的良娣已有五月身孕,太子妃妒心大起,便杀了她。贾南风平时在东宫为非作歹,下人们苦不堪言,这次有皇帝做主,纷纷一吐为快,原来,这种事已不是第一次,贾南风每见侧室有孕,或下药,或动手,必要堕其胎,因此除了长子遹,东宫已许久不添丁了。
司马炎刚刚缓过神来,听众人如是说,又气血上涌,一阵胸闷。
“侍卫何在?将贾南风禁足金墉城,褫夺太子妃封号,择日处置。”刚说完,司马炎眼前一黑,再也看不到眼前景物。
当司马炎再醒来时,已在太子床上,太医令王熙又是把脉,又是开方,虽是寒冬腊月,额头不免渗出一层细密汗珠。
新年的喜悦荡然无存。
关于太子选妃这事儿,中间还有些许波折。当年司马炎中意的其实是卫瓘之女。贾充要出镇凉州,心里不愿,便与荀勖等人合谋,撬了这门亲事,以便留在洛阳。荀勖向皇帝进言:卫瓘子嗣众多,如果再与皇室结亲,日后免不了外戚干政,因此国破家亡的例子还不够多吗?而贾家只有四个女儿,不会掀起多大风浪。原本定的是贾家小女儿贾午,因年岁太小,改定三女贾南风。所谓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司马衷竟一见钟情,非她不娶,于是,这门亲就成了。
司马炎为当时的决定懊恼不已,木已成舟,已容不得他反悔。
太子妃德行败坏,已不是一次两次,刚过门不久,便将侍女毒打致死,要不是太子和皇后苦苦求情,早已将她废掉,想到此些,司马炎将宗正司马亮召来,想让他依照族规行废立之事。
司马亮乃当今皇叔,掌管宗室事宜。依着他的意思,褫夺太子妃封号,废为庶人即可,何必非要加以刀戈?毕竟是皇家媳妇儿,闹得太大,传出去丢人。就在司马亮说话的空当儿,皇帝陛下已然鼾声大作,司马亮拂袖而去。
时光如水,新年很快到来,年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很快过去,贾南风整日在金墉城哭哭啼啼,司马衷则内宫和金墉城两头跑,哀求各位大臣劝劝陛下。
除此之外,整个晋帝国沉浸在热闹喜庆的氛围中。
边陲各部趁此机会,纷纷派遣使者上表朝贺,可把大鸿胪寺一干官员忙得够呛。辽东鲜卑更是派出一个庞大使团,由世子慕容廆带队。张华上任后,慕容氏败绩连连,年前又新逢大败,无力再与中原为敌,于是上表称臣,愿累世修好,司马炎一高兴,封首领慕容涉归为鲜卑大单于。
慕容乃辽东大族,自称帝高辛后人,秦汉时为匈奴所破,迁徙至大鲜卑山,后来参与檀石槐草原会盟,莫跋护作为中部三位大人之一,统帅中部。与其他各族不同,慕容鲜卑以黄帝苗裔自居,极为仰慕中原教化,衣着举止皆仿照汉人。到了莫跋护这一代,便把姓氏改为“慕容”,取“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之意。
此番入使,慕容廆备了山参、鹿茸、貂皮等物,足足装满百十车。除去进贡,剩下的都拿来交好朝中大臣。
齐王府亦送了不少。自从上次会完刘渊,司马攸身体江河日下,开始尚能走动,后来便咳血不止,走路都极为艰辛。他写信给张华,道自己来日无多。张华知道,齐王心中郁郁,不得排解,以致伤了心肺,他让慕容廆带信,曰:殿下春秋鼎盛,毋要多想,听说辽东的山参,鹿茸都是大补之物,对齐王之疾定大有裨益。
阅毕,司马攸仔细打量起慕容廆,这个年轻人身高八尺,仪表堂堂,与很多涂脂搽粉的汉人男子不同,他身上有一种浩然之气。司马攸不禁心生喜欢,家长里短唠个不停。经过上次一事,王妃怕再有闪失,一直躲在暖阁偷听,夫君的身子可经不住刺激了。
日头渐渐偏西,二人毫无倦意,王妃贾荃吩咐庖屋,今晚有贵客盈门,务必小心准备,觉得还不放心,干脆自己下厨。
临走时,齐王夫妇再三挽留,慕容廆以他日再来为由婉拒。
一连两日,慕容廆都在齐王府做客,二人相谈甚欢,王妃甚至想给他挑一个汉族女子,慕容氏的女人们更像是妻子,而非父子兄弟间赏赐的财物。慕容廆唯唯诺诺,并不置可否。
第三日,慕容廆前来辞行,宇文氏在辽东大动干戈,劫掠慕容氏不少百姓,他必须回去主持大局。司马攸取来竹简,给张华修长书一封,让他带上,并对他说,吾命不久矣,百年之后,若大晋有变,你定要在辽东保境安民,推行教化,好歹让中原汉人有个去处。说罢作了一个长长的揖,半晌不起,慕容廆甚是诧异,急忙还礼,问齐王何出此言。
司马攸并不作答,只将所戴冠巾赠予慕容廆,摆手让他离去。
回到屋内,司马攸一阵胸闷,缓了许久,喷出一大口鲜血,他为人要强,在外人面前始终体体面面,此刻终于坚持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