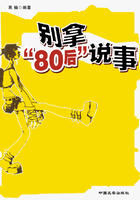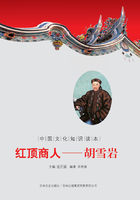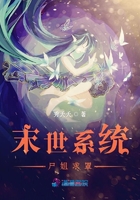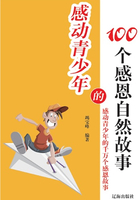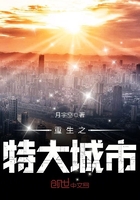献给·P
我不信上帝,但我想念他。有人问我时,我就这样说。我问我哥哥——他先后在牛津大学、日内瓦大学和巴黎大学教过哲学——他对这一表述有何想法,但没告诉他是我说的。他就回了一个词:“自作多情。”
这得从我外婆说起,她叫内莉·路易莎·斯科尔托克,娘家姓梅钦。在嫁给我外公伯特·斯科尔托克之前,她是什罗普郡的一名老师。外公的名字不是伯特伦,也不是艾伯特,而是伯特。他以此名接受洗礼,火化入殓。他是个中学校长,喜欢摆弄机械:一辆兰彻斯特挎斗摩托车;退休之后又有了一辆非常拉风、动感十足的凯旋跑车。跑车前排有三人长凳车座,不过把顶篷放下来,就变成两个单人座椅。等我跟他们混熟了,他俩为了和唯一的孩子住得近些,已经搬来了南方。外婆到妇女协会上班。她腌咸菜,然后装瓶;她把外公养的鸡和鹅去毛、烧烤。她身材娇小,看上去很圆通。和别的老人一样,她指关节粗大,需要用肥皂润滑一下才能把戒指摘下来。他们的衣柜里塞满了手织的开襟羊毛衫,外公的往往织着比较粗犷的缆绳状花样。他们定期约见足疗医生;他们那代人在牙医的建议下把牙齿一口气拔了个精光。这是常规人生必经的历程——从摇摇晃晃的吱吱磨牙,一下子就到了全副烤瓷牙,再到颊侧滑行治疗,到社交窘态和床头柜上泡沫四溅的酒杯。
这种从真牙到假牙的变化既沉重又粗俗,让我和哥哥感到震惊。不过我外婆的一生也蕴含另一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我们在她面前从未提起。内莉·路易莎·梅钦,一名化工厂工人的女儿,生于一个基督教循道宗家庭,而斯科尔托克家族信奉英国国教。在少女时代,我外婆有一天突然不再信仰基督教。根据家族传说的流畅故事,她找到一个新选择——社会主义。我不知道她当时的宗教信仰有多强烈,也不清楚她家的政治主张;我只知道她曾以社会党人身份竞选市政厅议员,以失败告终。等我在1950年代跟她熟了,她已进而成了共产主义者。可以肯定,她是白金汉郡郊区拿养老金的老人中少数几个订《工人日报》的人之一,而且——我和哥哥都坚持认为——把贴补家用的钱捐给了报纸的“斗争基金”。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微妙。对于大多数欧洲信徒而言,这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对接受莫斯科的资金和指令的《工人日报》来说,也是如此。而我那一辈子都没出过国、一直住在雅致小屋里的外婆,决定站在中国一边,与之共命运,个中缘由她从未透露。我坦陈自己支持她的决定是出于私利,因为此时她的《工人日报》已被《中国建设》——一份从遥远的大陆直邮过来的杂志——取代。外婆把那些颜色像饼干一样的信封上的邮票给我一张张攒下来,这些邮票经常是庆祝工业成就——大桥、水电大坝、刚下生产线的卡车——要么就是画着不同品种的白鸽在和平飞翔。
我哥哥并不争这些小恩小惠,因为几年前我们家发生了一场集邮大分裂。他决定专注于收集大英帝国邮票,而我为了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宣称要收集“世界其他地方”的邮票。这个范畴是我命名的,我自己觉得还挺有道理的。其实指的就是我哥不收集的东西。现在,我已经不记得这个举措到底是进攻,是防守,还是单单为了实用。只记得在学校集邮社里和一群刚换上长裤的集邮家交换邮票时,这时常造成困惑:“那么,巴恩西,你到底集什么?”“世界其他地方。”
外公对百利护发乳情有独钟,他的派克诺尔扶手椅——高靠背,带一对能让他靠着打盹儿的侧翼——的罩子可不单单是为了装饰。他的头发比外婆的白得早;他蓄了一副修剪过的威武神气的八字须;拿着铁杆烟斗,烟袋总是把开衫口袋塞得鼓鼓囊囊的。他还戴了个笨重的助听器,这是成人世界——或者,确切地说,是成人时代更遥远的那一边的世界——的另一面,我和哥哥很喜欢嘲笑这个。“你说什么?”我们把手拢在耳朵边,讥讽地彼此大喊。我们俩都期待外婆的肚子咕隆隆地响起,声音大得连耳聋的外公都听见了,他问:“孩子他妈,电话响了吗?”一阵尴尬的嘟哝之后,他们又继续闷头看报纸。助听器偶尔发出啸叫,烟斗被吸得噗噗直响,外公就这样坐在威武的扶手椅里,边摇头边看《每日快报》。在那红色一角,外婆坐在柔软的女式扶手椅上,对着《工人日报》啧啧不已,此报向她描述了一个真理和正义时刻遭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威胁而危在旦夕的世界。
到了这个时候,外公恪守的宗教仪式不过是看看电视节目“赞歌”。他干木工活,在花园里忙碌,自己种烟草,然后放在车库顶上晾干。那上面还储存着他的大丽花块茎,以及用毛绳捆起来的一份份旧《每日快报》。他宠爱哥哥,教他如何磨尖凿子,还把自己的木工箱留给他。我不记得他教过我(或者留给我)任何东西,不过有一次他允许我看他在花园木棚里杀鸡。他把鸡夹在手臂下,轻抚着它,让它平静下来,然后把鸡脖子搁在一个用螺丝固定在门柱上的绿色的金属压榨机里。当他按下刀柄时,手更是紧紧地抓住那只鸡,以防它垂死挣扎。
哥哥不仅可以在一旁观看,而且可以参与。很多次都是由他按下刀柄,外公只是摁着鸡而已。不过我们哥俩在杀鸡的记忆上出现了分歧。我觉得那不过是一台把鸡脖子拧折的机器,而他觉得那是个小型断头台。“我记得很清楚,铡刀下面有个小篮子。我还记得(不过画面有点模糊)鸡头掉在地上,有些血(不是很多),外公把断了头的鸡放在地上,它还挣扎着转了好一会儿……”是我的记忆自动净化了,还是他看多了法国大革命的电影,所以记忆变得更加残暴血腥了?无论是哪种情形,在指引我们认识死亡——及其纷乱——的道路上,外公为哥哥所花的工夫,远甚于为我做的。“你记不记得外公在圣诞节前是怎么杀鹅的?”(我不记得了。)“他在鹅圈里一圈圈地追那只在劫难逃的鹅,用铁锹打它。总算抓住了,他还会把它摁在地上,用铁锹抵住脖子,然后用力拽它的脑袋。”
哥哥记得一个特别的场景(但我从未亲眼见过),他称之为“互读日记”。外公外婆都有记日记的习惯。有时,在某个晚上,他们会朗读几年前某个星期的日记,以此消遣。他们俩记的东西显然都相当琐碎,却常常相互抵牾。外公:“周五。在花园里忙活。种土豆。”外婆:“瞎扯。‘一整天都在下雨。太湿了,花园里干不了活。’”
哥哥还记得,他小时候有一次进了外公的花园,拔光了所有的洋葱。外公把他打得嗷嗷叫。过后,外公的脸变得煞白,向我妈坦白了一切,并发誓今后再也不会对孩子动手。其实,我哥压根就不记得这事儿了,什么洋葱啊,挨揍啊,全忘了。他只是从母亲那里把这个故事听了一遍又一遍。当然,即使他记得这事儿,也许还会大表疑惑。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坚信记忆是会出岔子的。“甚至,按照笛卡尔的烂苹果原理,除非有什么外界的东西支撑记忆,否则谁都不可信。”而我比较轻信人事,或者自欺欺人,好吧,那就继续下去吧,权当我的记忆完全正确。
我母亲洗礼时取名凯瑟琳·梅布尔,但她讨厌梅布尔这个名字。不过她向外公抱怨的时候,外公解释说,自己“曾经认识一个特别好的姑娘,叫梅布尔”。尽管我拥有她的祷告书,但对她在宗教信仰上的进退一无所知。她的祷告书和《古今赞美诗》用柔软的棕色山羊皮装订在一起,每卷上面她都用奇特的绿墨水写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Dec:25.th1932.[1]”。我赞赏她加标点的方式:两个句号和一个冒号,其中一个句号恰好在“th”的正下方。如今可没人这样点标点了。
我小时候,三个不能谈论的话题都是传统话题:宗教、政治和性。后来,我和母亲开始讨论这些问题时——当然只有前两个,第三个是永远不会列入议事日程的——她是政治上的“正宗保守派”,我猜她一辈子都这样。至于宗教,她坚定地告诉我,在她的葬礼上她不要“任何繁文缛节”。所以,当殡仪员问我要不要把火葬场墙上的“宗教标志”拿下来的时候,我告诉他这八成就是母亲的心愿。
顺便一提,条件式过去时是我哥严重怀疑的一种时态。在等待葬礼开始时,我们并没有争论——这是有违一切家庭传统的——而是交流了一下,交流的内容是: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标准,我算是个理性主义者,而如果按照他的标准,就很勉强了。母亲第一次因中风而卧床不起时,她欣然答应孙女C可以开她的车。这辆车是她众多雷诺车里的最后一辆,四十多年来,她一直偏爱雷诺这个法国牌子。和哥哥站在火葬场的停车场里,我寻找着那辆熟悉的法国车身影,侄女却开着男朋友R的车来了。我说:——可以肯定,语气很温和——“我觉得妈倒希望C开着她的那辆车来。”而哥哥——他的语气也很温和——则不以为然。他指出,共有两种愿望,一种是死者的愿望,即死去的人们曾经的念想;另一种是假想的愿望,即猜测人们会有、也许有的愿望。“妈倒希望”是两者的结合:是对死者愿望的猜想,因而需倍加质疑。他解释道:“我们只能做我们想做的事。”去满足母亲可能有的愿望,就像他现在开始回顾自己过去的愿望一样,是很不合情理的。但我回答说,我们应该尽量满足母亲会有的愿望。因为:一、除非我们想让母亲的身子烂在后花园里,否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而其中绝对会面临抉择;二、我们希望自己死后有人也会为我们实现那些我们会有的愿望。
我跟哥哥不常见面,所以我总是惊讶于他的思维方式;不过他说得蛮诚恳的。葬礼后,我开车送他回伦敦,我们两人谈了谈我侄女C和她男朋友,我觉得这场对话更是古怪。两人在一起很久了,然而有一段时间闹别扭,C开始和另外一个男人交往。我哥和他妻子一见面就不喜欢这个第三者,显然我那嫂子只花了十分钟就“把他扫地出门”了。我没问到底是怎么把他扫地出门的。我只是问了句:“那你认可R吗?”
“我认不认可他,”我哥答道,“这无关紧要啊。”
“不,怎么会呢?C也许希望你认可他呢。”
“恰恰相反,也许她不希望我认可他。”
“但不管怎么说,你认不认可他,对她而言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吧。”
他想了一会儿,说:“你说得也对。”
从这一场对话中,也许你可以看出他是哥哥。
我母亲从未对她想在葬礼上放什么音乐发表过意见。我选了莫扎特降E大调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K.282,那种悠长的庄严的展开和再现,活泼段落依然肃穆严正的音乐。全长好像十五分钟左右,而不是唱片套上说的七分钟,以至于我发现自己不时地疑惑,这是不是另一曲莫扎特,或者是火葬场的CD机在跳碟。前一年上过《荒岛唱片》节目,那时我选了莫扎特的《安魂曲》。后来,我妈打电话来,说我把自己描绘成了不可知论者。她说我父亲也曾这样描述他自己——而她自己却是无神论者。在她看来,信奉不可知论仿佛是一种犹疑不定的自由主义姿态,与无神论的真理和市场力量的现实背道而驰。“对了,这些和死有什么关系?”她接着说。我解释说自己并不喜欢这个说法。“你就像你爸,”她说,“也许是因为你还小吧。等你到了我这把年纪,就不会这么介意了。无论如何,生命中最好的时光我都见过了。想想中世纪——那时,人们的寿命可真短哪。现如今,我们活到七十、八十、九十岁……人们信教,只是因为他们怕死。”我母亲表述观点就是这样——清晰、坚持己见、明显听不得反对意见。她主导家庭,对世界有把握,童年时清晰明朗,青年时自我约束,成年时苛责唠叨。
母亲火化后,我从那个“风琴手”那儿取回了我的莫扎特CD。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位风琴手如今定是靠把一张CD放进和拿出CD机来赚取他全部的弹奏费。我父亲是五年前在另一个火葬场火化的,那个风琴手兢兢业业地为他弹奏巴赫。这是“他会想要的”吗?我觉得他是不会反对的。他是一个平和、开朗的人,对音乐并不太感兴趣。他在这一点上,跟在大多数事情上一样,对老婆是言听计从的,尽管在私底下也会挖苦几句。他穿的衣服,他们住的房子,他们开的车子:这一切的决定权都在老婆手上。我年少轻狂时,一度觉得他太窝囊了。后来觉得那叫顺从。再后来,觉得他其实是有主见的,只是不愿争辩罢了。
我第一次随家人去教堂,是为了参加一个表兄的婚礼。那次我惊讶地看着父亲跪在长椅上,一只手捂住额头和眼睛。为什么要这样?我问自己,然后假模假样地摆出虔诚的姿势,底下却透过指缝窥探起来。这就是父母让你惊讶的场景之一。你惊讶,不是因为你在他们身上新发现了什么,而是你发现了一个新的未知领域。我父亲这么做只是因为礼节吗?他是不是觉得如果扑通一声跪下了,他就会被看作一个雪莱式的无神论者?我不知道。
他死得很现代,死在医院里,身边没有家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分钟,只有一个护工陪伴。几个月来,应该说是几年来,医学延长了他的生命,但到这份上已经难以称得上生命了。在他去世前几天,我妈还去看过他,然后就出了疹子。最后一次见面,他脑子已很糊涂。母亲用她特有的腔调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吗?上次我来这儿,你都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父亲也用自己特有的腔调回答说:“我想你是我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