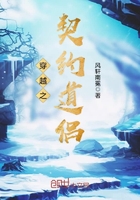段鸿飞鼓着眼睛恨声道:“老夫为你温家尽心尽力,你却谋划着如何除掉老夫,真叫人心寒呐。”
“这?”
温庭钰心头突突乱跳,他努力让自己表现的镇定,道:“从何说起?”
“哼。”
段飞云不屑的望着他冷哼一声,朝后一摆手,“带上来。”
随着话落,几名身穿甲胄的士兵将两名皮开肉绽的少年拖了进来。
在看见两人的一刻,温庭钰只觉脑中嗡的一响,刹那一片空白,明日便是大婚之期,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亲手搬倒这只老狐狸了,却最终棋差一招,一败涂地。
段鸿飞看着深受打击的温庭钰心情十分舒畅,头一扬,嗤笑道:“你以为你离开鄞州地界,在云州操练兵马,老夫便一无所知了?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也敢和我斗,简直太天真了。”
小多抬起带血的脸,凄凄道:“殿...殿下...”
阿四声音里带着哭腔,“师兄,我们的人都被他杀了。”
听见他们的话温庭钰气的踉踉跄跄连退几步,直至后背贴着桌子,才险险站稳。
段鸿飞斜睨着他,“你若乖乖听话,老夫本不打算动你,可惜你太无知了,自寻死路......”
他的话激起了温庭钰的血性,他满脸通红,一直到发根,鼻翼由于内心激动涨得大大的,“段鸿飞,你食君之禄,却不为君分忧,还妄想乱我朝纲,今日本宫便除了你这佞臣。”
随着话声,一把寒光闪闪的软剑自他腰间弹出,人也如流星,卷着剑光射向段鸿飞。
剑如霜雪,周身银辉。
“铿”段鸿飞拔剑,满溢杀气的迎了上去。
于此同时厉喝道:“不知死活。”
月光,映照的厅堂外面如同白昼,两柄长剑已战了四五十个回合,温庭钰招式高绝,怎奈内力不济,渐渐有了落败的趋势。
“去死吧。”
喝声里,只见漫天剑光忽然散开,如十几道金芒呼啸着袭向温庭钰周身。
“噗呲”
温庭钰掌中软剑弹飞,而对方的剑尖已深深插进他的左肩,顷刻间鲜血飞溅,段鸿飞长剑使劲向前推,大有借这一插,刨开他的肩胛之势。
“殿下。”
“师兄。”
温庭钰闷声不吭,想来今日已是在劫难逃,唯一双含恨的眸子狠狠瞪着他,大有用眼神将之凌迟处死。
“父王住手。”
随着一声娇喝,一道黑色人影,快的令人看不清轮廓,人未至,手中金光一闪,一柄细剑带着沉重的风声,极其准确的架在段鸿飞的脖子上,阻住他继续刺下去的速度。
“呼啦啦啦......”大批侍卫涌进来,刀出鞘箭在弦,乌黑的箭尖酷厉的瞄准来人。
“父王,求你不要杀他。”
随后粉色衣衫的女子扒开围着的侍卫,噗通跪在段鸿飞脚下。
段鸿飞瞟了眼脖子上的刀,再看看哭的梨花带雨的女儿,恨的咬牙切齿,“我真是白养你了,竟然用我赐你的暗卫对付我。”
“父王,我已是他的人,如果你要杀他,就连女儿一起杀了吧。”
段鸿飞气的太阳穴青筋突突,“是他要杀你父王,你竟帮着外人,真是我养的好女儿。”
她抬起的睫毛沾满水珠,惶恐而坚定,“父王,求求你,我已经有了他的骨肉,求求你了。”
几日前陆续收到战报,有浣月铁骑不断滋扰边关,似要挑衅寻事,若此刻温庭钰死了,浣月,云夜,还有周边一些小国必定趁机席卷而来。
段鸿飞看看哭成泪人的女儿,再看看在自己剑下苟延残喘的温庭钰,他此生注定了任自己揉捏,又何必急于一时。
于是叹息一声,“罢了,你起来吧,父王答应你便是。”
“谢父王,谢父王”拂云郡主连连磕了几个头,这才破涕为笑的站起来,摆摆手,道:“无痕,还不退下。”
黑衣人听见吩咐,金光一闪,架在段飞云脖子上的刀已收回,同时人也后退数步,立在拂云郡主身后。
“啊......”
听见凄厉的叫声,拂云郡主一抬头,只见温庭钰如一只枯叶蝶般萎靡的倒在地上,她惊慌的扑过去,看着不断冒血的伤口恨声道:“父王,你不是答应我不杀他,为何出尔反尔?”
“我只是断了他的经脉,只有这样他才能乖乖的留在你身边,父王也是为你好。”
话落刀入鞘,朝后一摆手,“把这两个逆贼关入天牢,等殿下大婚后斩首。”
“是”
侍卫走过去提起两人转身离去,身下逶迤出两行长长的血痕。
一队又一队人马,风驰电闪,于星夜里快速奔行,以雷霆不挡之势踏破晨曦的骄阳,行至鄞州,隐蔽至孟轻舟指定的位置。
“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
孟轻舟的咳嗽似乎越来越厉害了,马车行至一处山谷,恒儿心一横,冲车夫喊道:“停车。”
急踏奔行的骏马发出一串长长的嘶鸣,慢慢停了下来。
一阵长长的咳喘后,孟轻舟倚在车壁撩起车帘看了看黄昏的夕阳,“我记得还有二十公里便到一个小镇,我们争取入夜之前赶过去。”
恒儿按住他胳膊,“你在这里等我。”
只见车帘一晃,车内已失了恒儿的影子。
孟轻舟看着如一只猴子般攀壁飞岩的女子,心一漾,她终究是在乎自己的,不是吗?
车帘一晃,笑容满面的女子已出现在车里,怀里抱着一大把紫苏,“我原本以为山上应该有草药的,没想到漠北的山和玲珑山不太一样,我只找到了这些。”
孟轻舟靠在车壁唇角不觉上扬,深海般的眸子里笑意满满,薄唇亲启,“甚好!”
甚好?
几个意思?
恒儿抬头看他,见他因为咳嗽泛粉的脸颊呈现诱人的红晕,不由一怔,这人莫不是这几天咳坏了脑子?
初秋的夜晚,狂风漫卷,寒气逼人,马车到达新阳镇唯一一家客栈,车夫却怎么也敲不开门。
恒儿眼中闪过一丝疑惑,素手撩起车幔,目光停留在紧闭的店门上,回头吩咐孟轻舟,“你坐在马车你,我下去看看。”
“有人吗,我们要住店?”
旁边的车夫只感觉耳边一道惊雷炸响,好一会才恢复听觉,恒儿的声音暗含内劲,除非是聋子,否则任你睡的多死也会被吵醒。
车夫疑惑道:“会不会这家店已经不经营了?”
恒儿手指触了触窗户,见上面的麻纸是新糊的,院中无一丝杂草,肯定的摇摇头,“不会。”
她深吸一口气,敛了敛思绪问道:“附近可还有其他客栈?”
车夫果断摇头,“新阳镇只此一家,下一个镇子离这里五十公里”他转头看了看马车方向,“这天寒地冻公子的身子?”
“砰......”
他的话未落,客栈的门已被恒儿一掌拍碎,木屑四处乱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