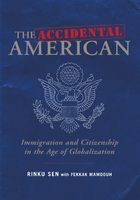潘玲身上冷汗层层而出,她稳了稳神,强自镇定,蹲下身温柔地拍着潘剑的背脊安抚道,“别怕别怕,娘亲在这。”她一边安抚潘剑,一边面带苦涩的对着众人道歉,“我儿这是癔症又犯了,让诸位见笑了。”
说罢,她大声一喝,“来人,将少爷带回房吃药。”
两个小厮急忙跑过来去抱潘剑,潘剑身子一扭从三人中挣脱出来,用孩童独有的尖锐声音大声叫喊,“我没有癔症!!娘,我还没有过继给沈家,我不回房,我要等着过继!沈家那群老东西究竟来了没有?过继何时才开始?”
太可怕了,潘剑说的这些话太可怕了,潘玲抑制不住浑身都颤抖起来,她又急又惊,恨不得直接拿桌上的糕点堵上潘剑的嘴,以免他又口出惊人之语,她对着小厮大声一喝,“捂住他的嘴!”
忽而‘砰’地一声巨响,潘玲寻声看去,只见沈家的族长将茶杯狠狠地摔到了地上,茶杯四分五裂,碎片四溅,四周的人纷纷跳脚躲开,沈家族长重重一拍桌子,“竖子!我沈家的老东西,已在此多时!”花园中皆是石桌,被他重重一拍,声音不大,手却被振得又痛又麻,他越加气怒,喝道,“过继一事就此作罢,沈家有我在一日,你想入我沈家族谱,便是痴心妄想!”
潘玲的心都随着那一声响颤了几颤,她咽了咽口水,扯出笑脸对着沈家族长想要赔礼,却又听潘剑尖声叫道,“你个老东西!老不死!不让我过继,我让我爹杀了你!他能杀得了沈乔就杀得了你!”
潘玲脑子嗡地一声,头晕目眩,只觉眼前发黑,险些站立不稳,她还未来得及反应,就见一个身影冲了出来,对着潘剑心窝子便是狠狠一脚,“畜生,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莫不是魔障了!”
潘剑小小的身子瞬间被踹飞出仗余远,可见那人的这一脚踹得有多狠。
潘玲瞪大了眼,怔怔地看着往日里温柔小意的男人,此刻面目狰狞犹如索命恶鬼般的扭曲面容,她猛地尖叫一声,踉跄着扑过去将被踹得口鼻出血的潘剑紧紧抱在怀中,慌张得不知所措,“剑儿,剑儿,你怎样了?你别吓娘!”
“你,你方才说什么?”一个苍老虚弱的声音响起,沈老爷拖着病体,被小厮扶着缓缓走来,他神情激动,浑浊的双眼中此刻充满震惊与愤怒,他走到潘剑面前,盯着他怒声喝问,“你说谁杀了沈乔?你再说一遍!!!”
来贺寿的宾客未曾想沈家今日会出这番变故,一时间都被潘剑的话惊得目瞪口呆,众人一时也不知是该走该留,尴尬的杵在原地,彼此面面相窥。
沈家的宗亲相互对一个眼神后,在彼此眼中看到了亮光,沈家的过继怕是不成了!原本他们就反对沈家不挑宗族子弟过继,反倒要过继一个外姓人,只是碍于潘昭手腕强硬,几番谈判后只得宗族做出了妥协。
可如今……不管潘剑所说是真是假,能抓住这点向潘昭发难,足以争取更多的利益!于是沈家族人立即便遣了人去府衙报官。
“爹,你莫要听剑儿乱说,他近日得了癔症,你也知道的!”潘昭表情恢复了淡然,他笑着两步上前去搀扶沈老爷。
沈老爷一把甩开他,半分不客气,“是不是癔症,且待我问清楚!”他又转头看向潘剑,声色俱厉的质问,“潘剑,将你方才的话同我说清楚!”
潘剑被潘玲紧紧抱在怀中,小小的身子不住抽动,口鼻溢血,眼神涣散,奄奄一息的模样像是随时要断气,他两只小手紧紧地抓着潘玲的衣襟,口中语无伦次地呢喃,“娘亲,剑儿好疼……疼……我才是,我才是潘家的嫡长子……娘亲,我才是……”
见爱子如此,潘玲心痛如绞,颤抖着手为潘剑擦拭脸上的鲜血,眼泪如断线的珠子不住地低落,哽咽着安抚,“是,我们剑儿才是潘家的嫡长子,是潘家唯一的嫡子,剑儿乖,莫要再闹,娘亲带你去看大夫!”
她哆哆嗦嗦地抱起潘剑想要起身,方一动,便被潘昭伸脚踹去,这一脚恰恰踹在潘剑的腰窝,母子两人皆被踹翻在地,潘剑惨叫一声,整个身子都骤然瘫软。
潘玲心下咯噔一下,脸色煞白,身子也跟着瘫软下去,心直直沉入了谷底。
沈老爷见潘剑痛苦灰白的小脸,想到此刻在那身体里受痛的是他的爱女,又气又恨,脑门上的青筋都齐齐蹦了起来。
“玲儿!”潘昭对着潘玲疾言厉色地一喝,“这个小畜生神志不清胡言乱语,你休要跟着胡闹!”
潘玲闻言抬头,与潘昭狠厉警告的目光对个正着,她心脏猛地一缩,如坠冰窟,杀意!她竟在潘昭眼中看到了浓重的杀意,她下意识畏惧的将潘剑抱紧了几分,正震惊于潘昭居然想杀掉他们母子的巨大失望痛苦中,便听得潘剑微弱的声音传来,语气中带着万分委屈,“娘亲,不是说等我过继给沈家你就和爹成亲吗?他为什么要娶知府的女儿不娶你了?是不是我做错什么惹爹生气了?”
他话音刚落,潘玲就感觉到潘昭阴鸷如毒蛇的目光落到了潘剑身上,那像是恨不得要将潘剑生吃活剥的目光,像极了八年前沈乔撞破他们二人亲热时,他看向沈乔的目光,真是讽刺啊,万没想到,有一天他也会用这样的眼神看向她和他们的儿子。
也是,他已经要娶知府的千金,他再不是落难需要她帮扶的穷小子,他吸干了她家,又吸干了沈家,如今,她也如同沈乔一样,成了他往上爬的绊脚石,挡了路,自然是要踢开清除的,他向来是如此狠厉果断的,她比谁都要了解他。
可她不甘,她不是沈乔那个蠢妇,她与他青梅竹马一同长大,有二十余载的情分,她爹更是倾尽财力抚育他培养他,他想踏着她们一家的血肉平步青云,他做梦!一瞬间,往日深切的爱意化作森森强烈的恨意,她缓缓地勾起嘴角,冷笑出声,“胡言乱语?”
潘玲眼也不错地与潘昭对视,恨意蓬勃,“你口中这个小畜生是你的亲生骨肉,他是小畜生,你又是什么?”
霎时,四下皆静,众人瞠目结舌。
“玲儿!”潘昭面色阴沉得要滴出水来,他在一瞬间的意外后,轻轻的唤了潘玲一声,声音虽是轻柔,对他再了解不过的潘玲却感觉到了十足的警告威胁。
众人在一瞬的寂静后,立即窃窃私语讨论开来,“天啊!原来潘剑是潘昭的儿子?潘玲不是他的亲妹妹吗?”
“想我大魏礼仪之邦,竟有这样的事情!兄妹乱伦,简直丧德败行,畜生不如!”有人义愤填膺的唾骂。
“啧啧啧,真是开了眼见!”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你们知道什么?谁知道人家是不是亲兄妹?说不得,是情妹妹!”有人开始各种猜测。
“沈家可真是惨,招了这么个丧心病狂的人入赘,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你说那沈大小姐,多精明的人儿,居然被他骗过去了!”有人忆起沈乔,万分惋惜。
“方才那娃儿不是说沈大小姐是被潘昭杀死的吗?这可是命案,快去报官!”有人直抓重心。
“呵!”潘玲心知今日与潘昭撕破脸已是鱼死网破,再无活路,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完全没有了往日的仪态,她轻柔地将潘剑抱在怀中,尽量让他能舒适一些,她冷笑道,“潘昭,我爹30年前因承了你潘家恩情,是以在你潘家满门抄斩时冒着杀头的风险将你救出来,远遁登州,我家生计艰难,爹却将所有的钱财心血都花在了你身上,他抚育你培养你,倾尽全家之力也要供你念书识字,哪怕因此害死了他的亲儿子!”
她的亲哥,为了赚钱供养潘昭读书,去了私旷做工,最后旷洞坍塌,哥哥死在旷洞里,连尸体都没能拿回来。
“闭嘴!”潘昭脸色铁青,勃然大怒,随手拿起不远处石桌上的茶壶朝着潘玲狠狠砸去,目呲欲裂,高声怒喊,“来人!来人!他们母子都失心疯了,将他们带下去!”
潘玲偏头一避,紫砂茶壶擦着她的脸颊飞了过去,砰地一声砸后面的树干上,四分五裂,潘玲看着地上的碎片凄笑一声,“登州大旱,我爹临死前将我托付于你,千里迢迢来到淮阳,我在郊外替人做针线养活你,你却转头就弃了我要入赘沈家为婿!”她忽地大笑起来,“哈哈哈!潘昭,你想要攀高枝吃软饭,却非要打着为潘家复仇的幌子,真真是可笑!你潘家贪墨,害死了上千百姓,天下百姓无不唾骂,你有什么脸报仇?又有什么仇要报?一个罪臣之后,却一心想要走官途,真真是可笑之极!”
她爹为了报恩,救下潘昭这个罪臣之后,从此一家人东躲西藏,没过过一天安稳日子,娘在奔波途中劳累病死,哥哥也因生计而死,她爹在死前将她托付给潘昭,可她从小就了解潘昭,他哪里是什么良人,明明是一个眼高手低又阴险虚伪的豺狼!可她已是一介孤女,除了跟着他,别无选择。
她知道总会有一天,潘昭手中的刀会朝她挥来,只是她没想到会这样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