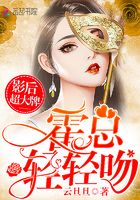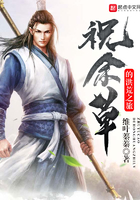11月,系里开始分配论文指导老师。
沐歌不知道分配的原则是什么,成绩、宿舍、学号、年龄都不是。
沐歌所在的小组一共五个人,其中就有董舒言。
万幸的是,他们的指导老师是个非常讲究效率的人,把他们几个人拉到一个群里,一切要求、注意事项和时间安排都在群里说说得明明白白,没有要求见面开会。
另外让董舒言当了小组长,要求其他四个人把选题之类的资料交给董舒言之后,再让董舒言统一提交给他。
都是在线上就可以解决的事。不用碰面,就不用花费力气去寒暄。
她实在是没有精力再去做个风轻云淡的表演者。
虽然只是实习,但沐歌已经忙到飞起。本来沐歌负责报社微信微博公众号的运营,有不同板块的负责人写稿,沐歌的职责是负责校对、编辑、定时上传公众号。而老吴头又给沐歌加了“作业”:以各个板块的负责人选题为基础,由沐歌再独立写一篇稿子,交给老吴头。
当然,上交的稿子不会出刊、不会上号,老吴头甚至连多余的点评都没有。
真的开始做这个作业,沐歌才发现自己在大学通讯社的写稿是多么幼稚。
每次对比交给她校对、发表的稿件和自己写的同一事件的稿件,云泥之差不过如此。
不可能不沮丧。哪怕用“他们都有经验,我只是个菜鸟”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沐歌心里也没有底气。自己差的哪里只是经验,大学的学习对一个人专业素养和敏感度的养成,才是让沐歌最为自卑的。
只是,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沐歌就不愿意轻易放弃,说出后悔。只能暗自鼓励自己要加油,然后认真分析别人的稿子,借鉴学习。
笨鸟先飞。惟勤是岸。
每当自己觉得有一点点进步,沐歌就特别感谢老吴头的存在。
老吴头本名吴志军,算是沐歌的师哥,只不过比沐歌大30届——老吴头上的学校,之后和几个学校合并,成了现在的H大。
大概因为这一点缘分,老吴头接受H大通讯社的邀请,成了通讯社的顾问。
顾问这种名头,可虚可实。有的人纯属挂个名号,有的人是扎扎实实的有问必答。老吴头是个很实在的人,隔三差五地来H大给通讯社的这群小豆丁做个讲座或者给他们的报纸提个意见,很热心。
当然,更实际的帮助是,通过老吴头的“牵线搭桥”,通讯社好几个人拿到不错的门户网站实习机会。
当时沐歌也是其中一个。本来老吴头推荐沐歌去一个以发展势头强劲、出的新闻常常引爆热搜著称的门户网站。但是沐歌找到老吴头,想要交换。
交换到湘水报社实习的机会。
“你可得想清楚了,你来湘水的话,留下的机会比去那小多了,而且没有实习工资。”老吴头一开始就摆好车马,交代的清楚明白。
沐歌没有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