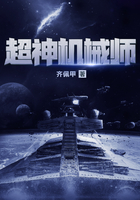想到这里,便从身上拿出三两碎银子去巷子外面包圆了馒头摊与粥铺并着蒸饼之类的,唤着摊主帮他拿着这些食物一起到巷子里。
那蒸饼摊主是个四五十岁的妇人,眉眼斜吊,显出几分刻薄来,赔笑道:“哎哟这位大爷,恐怕我们这些不够那娃娃们吃的,您瞧瞧。”
说话的同时指着边上几家食店,“大爷,这水饭、干脯、包子鸡皮连着扁食什么的也都是垫肚子挡饥的好东西,还有那炸响铃、糖藕的,不如大爷多发善心,一并买了吧。”
沈擎岳打眼往边上铺子一看,又见那些摊主面含苦色,眼里夹杂着三分哀求,又想起那群娃娃,已然软了心肠,挥手道:“都拿过去给他们吃了吧。”
众位摊主纷纷打包自家食物,喜笑颜开的送到巷子里。但他没想到的是,饥饿的娃娃家必有穷苦挨饿的大人。
这一送,巷子里的人可都出来了,一个个是跪倒在地苦苦哀求起来。
那妇人又喊道:“乡亲父老们啊,是这位大爷菩萨心肠买来的这些食物送给大家的。大家快来谢谢他。”
如此三来两往之下,五十两银子被花的干干净净。
老话说得好啊,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天下不稳,做生意的摊贩借机涨价,看着你好说话,有的没的都往上算,别说你五十两银子,就你五百两五千两也经不住这帮人这么榨的。
沈擎岳只觉得一番热闹过后,自己被好多人扯个不停说个不停跪个不停的,等耳边清净下来后,明月已高悬当空。
伸手摸了摸自己洗的变了色的衣袖又遭一劫,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撕烂了,听着肚里传来的咕咕叫声,他缓缓靠在墙根底下,想捋一下刚刚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想了半晌,仍是十分混乱,无奈的叹口气,想念自己的师弟来,若是他在,肯定不会是这样罢。
冷风阵阵,饥困之下的沈擎岳只得盘腿打坐练起功来,唯有如此方能不思今日处境。
醒时天已大亮,伸手抹了抹眼睛打量着周围,见这里临水傍桥,杏柳斜倚,桃李正旺,春色一片大好。
周边处处又荡着叫卖之声,肚子不应时的咕咕叫了几声。
正打量时忽然看见前方有个身着翠绿衣衫的少女正看着自己,忽见那姑娘向自己招招手:“哎,那人,你过来,你过来。”
看看周围,并未见到其他什么人,沈擎岳拿手指了指自己,奇怪道:“姑娘叫我?”
“对,大个子,就是在叫你,你过来。”
那少女笑嘻嘻的瞅着他说,声音娇软清甜,见他似乎还没反应过来,便抬脚走到他边上来,边走边说:“哎,我叫你你不来,那我过来好了。”
那少女快步走到沈擎岳身边,矮身坐他身边来,问他:“大个子,你来这做什么呢?”
沈擎岳打量她刚走路的姿势,知她会些武功,不高罢了。便道:“参加比武,夺盟主的位置。”
那少女听完噗嗤一声笑了起来,笑完了方说:“可我见你昨日被人坑光了银子啊,这离比武可还差几天呢,你怎么活下去?”
沈擎岳瞥了她一眼,并不说话,只是蹲着往边上挪了挪。
那少女不在意的继续往他边上挪过去,说:“不过我倒是可以出银子请你吃饭住宿。”沈擎岳依旧不说话。
“只是我有个要求,就是你这几日得住在我铺子里,白日呢不用你看铺子,但是你得在那守着,晚间你就住那,到你们比武结束后,如何?”那少女说道。
“为什么?你那莫非是黑店?”沈擎岳心中有疑,嘴上却已经说了出来。自觉失言,便去看那姑娘脸色。
那少女噗嗤一笑,片刻后秀眉紧皱说:“我爹娘在锦城街街尾上做些营生,所卖只是些绣线之类,所得也不过是够一家三口果腹罢了。偏对面铺子有人买下了开酒楼,而那酒楼掌柜的非说我家绣线铺子挡了他家风水,逼着我爹关了铺子。”
说到这里,少女随手捡起身边的石子扔在河里,带有几分不快道:“原本我娘想着息事宁人,不与他们争执,卖了铺子再寻个就是行,结果那掌柜的非说铺子挡了他们风水,也不能卖了给他人,他们愿意盘下来,可盘铺子的银子连十两都不到,明摆着欺负我爹娘来。”
说完瞅了几眼沈擎岳,见他依旧不言语,又道:“我是学了两年功夫,可都是些花拳绣腿架秧子罢了,唬人挺好,却是怎么也打不过那些人。”
说完略带几分恳求的看看沈擎岳道:“我们不过一介百姓,哪里斗得过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家,便拉着爹爹关了店去乡下。我却咽不下这口气,嘱了店里的伙计留下,我自己来这里转转,说不定能碰上个高手帮我伸冤呢。”
那姑娘一双大眼似乎已带泪花,转眼间便已落下泪来。
沈擎岳平时最见不得人哭,尤其是老人、稚子与这女子哭,昔年他六娘同他开玩笑说:“若是敌人擒你,不必多高深的武功,只需派上两个幼儿抑或老妇到你面前哭上一番就成了。”
欲伸手劝这少女别哭,拍了几次没敢碰上,又看已有早起的路人指指点点的看着自己,一时结结巴巴起来:“你…哎,姑娘你别哭…别哭、别哭,我跟你去,跟你去还不成吗?”
那姑娘一听他答应了,瞬时脸上便笑开了花,一把抓过沈擎岳手臂开心道:“大个子,你人可真好,我姓江,小名儿菀娘,你怎么称呼?”
沈擎岳看她一手揽着自己,略带几分紧张的说:“我姓沈,名擎岳,字…枕山。”那少女一听,嘻嘻笑道:“那我便叫你枕山大哥了。”
沈擎岳随那女子一路走,走了不多时只见一处高耸的门楼,街上人烟繁华,绝不似前几日那样荒无人烟的山林小道。
穿过门楼又往前行了一炷香的时间,转入一个小道里来,又过一处桥,见桥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好不热闹,伸头往桥下看,只见河里轻舟来来往往,内心大为惊讶,忍不住问道:“姑娘,不是说打仗大家都在逃难吗?”
菀娘看他这一副惊讶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过会儿方道:“大哥莫不是从北边来的?虽说京城不安生,可是只要官老爷坐得住,我们该怎么过日子还是怎么过日子啊。”
沈擎岳暗自悲伤,绝对是师弟那个家伙,见自己把银钱都散尽了才带着自己走些荒无人烟的小道来着。
可是,自己还真以为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催着他去投奔官军去了,这可如何是好?若是被绊住了回不来,别说柳老头,就连家里的几个夫人都不会放过自己。
菀娘看他脸色十分的难看,略带关切的问道:“沈大哥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闻言,沈擎岳只是干笑了一声,说:“无事,无事,离你家还有多远?”
菀娘一听,也不纠缠,只是说:“快了,穿过这条街,过了一家豆腐坊,便就是我家的铺子了。”
如此二人继续往前行去,不多时,菀娘止住脚步说到了,沈擎岳抬眼看原是一个小铺子,门外挂着青布幌子,只是门紧紧关着。
趁着菀娘开铺子门锁时沈擎岳往对面酒楼看去,只见那是一座三层的酒楼,外观明亮辉宏,一排幌子随风摇晃,幌子上写着谢家酒楼四个大字,字势凌厉。
细瞧这谢家酒楼,虽是大清早的,堂客却不少,跑堂的进进出出招呼客人,个个脸上带着三分喜色。
打眼看了一圈,余光瞅到菀娘进了铺子,抬脚也跟了进去。
进入铺子后,沈擎岳仔细打量这小绒线铺子,见只几排空空的架子,柜台上也是空无一物,奇怪道:“怎么搬空了?”
菀娘从柜台后搬出两个木凳子来,擦拭干净了,请沈擎岳坐下说道:“他们来铺子里一通乱砸,我爹娘同伙计把剩余的货物全给收起来了。”
“那你们为何不去报官?”沈擎岳疑道。
那菀娘听到此话,冷笑一声道:“报官?报哪门子的官。整个临安城谁不知道这知府大人姓什么,哼,谁给他钱姓什么。”
抬眼扫了对面酒楼一眼,愤愤道:“这酒楼背后主人,是临安有名的富户周胜周老爷家开的,京城一个姓赵的官老爷是这周胜的干爷爷,平时不拘什么节日,周胜总是备了厚礼送与知府大人,两家前些日子还续了姻亲,谁敢报官?恐怕正主没看到,报官的先被拉去大堂上拶手指去了。”
沈擎岳平日为人最为正义,与他师弟不同,见到不平事便要去管,此刻一听这话,心里哪还按捺的住,但此刻上前去又有寻衅滋事之嫌,一时之间倒想不到什么对策。
看他脸色,菀娘知他内心愤怒,便低声说道:“我刚刚已请傅伙计回去取货来了,今日我同傅伙计先把线团理好,明日重新开门做生意,若是有人来挑事,沈大哥再出手相助不迟。”
话刚说完,忽然听得一阵咕咕叫声,一时之间沈擎岳满脸通红起来,原是他昨夜未尝吃饭,清早又一路走来滴水未进,肚子饿的咕咕叫起来。
菀娘一听,忍不住笑起来说:“是我怠慢了贵客。”说罢起身邀沈擎岳去隔壁卖羹汤的张婆婆家。
张婆婆的儿子名叫安哥儿,安哥儿素日里与街上一家药铺里做伙计,还未出门,见菀娘领着个大个子进他家铺子里来,笑着冲着菀娘道:“菀姐儿几时回了,俺竟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