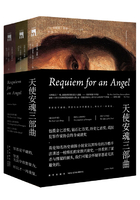闲话少说。却说芙能那日夜见有柱那物件如此萎小,立刻忍不住号啕起来。正号得伤心,窗外头连山喊道:“哭啥哩,让外人听着该咋!”芙能只好强咽,不再敢哭。两厢睡下。有柱抹着泪看窑顶。好大一阵,芙能又觉有柱可怜,随问:“你哪为咋?”有柱说:“我不晓得。”芙能又问:“生下来就是这相?”有柱说:“没有的。听我大说,小时候我家里喂一条大狗,那时候我四五岁,手里拿着馍,狗随着我,我蹲在门前尿尿,黑狗看我鸡鸡动弹,扑上来一口咬了。我大一生气,把狗杀了。”说完又是抹泪。芙能看他实在太可怜,便替他擦了眼泪,安慰他说:“甭哭了,没那东西,咱照样过日子。”芙能又想说啥,但一听声音,再去看那有柱,已尸木贴贴地睡着了。芙能叹了口气,随之吹了灯,仍想自己对有柱是不是太过分了。
也许天下的女人都有这份善良,说来也难能可贵,但与天理人伦,总有些不大得当之处。你且细想,那芙能说起简单,但于男女之间耳鬓厮磨日夜厮守过日子份儿上,哪有那么容易?再说那有柱自己不成,心性却非常张狂。一到黑便穷骚情,在她身上这里摸摸那里捏捏,就是大天白日没人时候,也没个正点,手脚上极是贱作。不过芙能有时也想有些动作,但由有柱一逗之后,便是恶心想吐。一个身性备佳的女人,岂能忍受如此摆弄?何况芙能多少还算有点经历之人。日子一久,脾气变得古怪起来。虽不敢在公公面前发泄,但对有柱却时常恣意显排,打起来像打娃一般,不论是头是脸,上去便几耳光。芙能每回娘家,和妈私下对面,总是长吁短叹面色惨怛。妈问啥事,芙能摇头,只是潸然泪下。妈问:“是有柱对你不好?”芙能说:“不是。”妈又说:“做女人难哩,熬呀熬,熬到老了就没事了。”芙能点头,认妈说得有理,心头却是不允。在娘家一住就是半月,总不说走,妈也不好催她。只等有柱牵着骡子载她回去。
这事情邓连山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作为公公尽管是一世精明,但于此事却是没了主见。上地下田,随在芙能后头,看着她那年轻活泛的腰身,回头再看自己那窝里窝囊死不中用的儿子,心里头直不是滋味。
日月穿梭,时光飞度。紧说就是一年。这年夏天,一日,有柱下河里水磨上磨面。说来也巧,临天黑时噼噼啪啪下起一场大雨。这雨下起来没有一刻停顿,有柱许是回不来了。芙能做好晚饭,看着公公吃了,收拾碗筷便回自己窑里,上炕脱光衣服睡了,心想这一夜得个清静。
有柱不在,独自一人,听窗外的雨声,胡思乱想了半日,待到雨点歇下,这才迷糊睡着。先是梦见娘家,大在地里犁地。她去给送饭。大吃罢饭便转身过去,背对她往田里撒尿,边尿边说话。后来又是她妈指着大的脊背说:“你个老没出息的,没看见婆娘女子都在跟前,也不嫌丢人现眼,掏出来就尿。”后来又梦见下雨,有柱扛着面粉,喊叫着进了院子。只听老汉那边窑吆喝:“芙能,快把你男人接住,操心面湿了!”她赶快跑到雨地,扶住有柱一块儿进窑。又梦见她在炕上躺着,佯装睡着,听那有柱拿汗巾擦脸,后来又上炕。有柱睡下,又像往常一样探身过来,伸手摸她。她一把推开,说道:“人都快睡着了,你又咋,烦的!”紧接着只觉着一个冰凉的身子揭开她的被子进来。
她一惊,苏醒过来。仍以为是有柱,真真实实地推了一把。没推开,那凉飕飕的身子战战兢兢地将她沉沉压住。此时她已完全清醒过来,以那身架觉出不是有柱,刚要喊,一只大手将她的嘴捂住。身底下随即便觉着有一根硬物在腿面上戳捣。她觉摸着是男人那物,一下子慌了神,也不说挣了,只是恍惚了片刻,两腿不由自主地腾开空地,任凭那物瞎摸乱撞,终于在一阵刺疼中感受到那物非常鲁莽地插入她的身体,很深很深。她说不清自己是疼还是咋的,随着那物的来往抽动,小声地哭泣起来。
唉,黄土啊黄土,黄土地人不就是这样?芙能明知不是有柱,却是自己允了,把一个好端端的女儿身子,付与那不明不白之人,就是这个道理。人生在世,大凡难就难在固守心性这一条上。心性动了,即就有万千个明白,万千个决心,也抵不住那心性深处欲念的蹿动。何况是这花红世界,小儿呱呱坠地下来,立刻便分男辨女。再长大些,且不说自身的体会觉悟,用村里庞二臭那一路人的话说:“灯吹了,我不干乃事,再有啥干的!”这也是黄土地人唯一欢悦和动情的地方,只有到这种时候,他才觉得活得值了。因此,少辈子人耳濡目染,自是跟着心性难守,常有那不到年龄,便做出一些张致来的。大千世界统归一理。多少正人君子,贞淑女子,撕下面皮,难说有几位能抵赖掉内心深处的欲念。芙能乃一乡村女子,没得到过什么圣人点化且不说,却又经有柱多方挑逗,心性混乱已是实情。此时此刻,竟怪不得她。回头朝近处说,如今那水花,明明白白被张法师诓骗着奸了,身下却是心满意足,竟将自己一生的私情都与那张法师联系,此便又是证实了这番道理。
水花也苦,儿子山山生下来,长到九岁。这不,去年春上黑烂在石堡川修水库炸石头,不期跌了大祸,两条腿捐了进去,成了直骨桩桩的一件废物,终日戳在炕角,拉屎尿尿都得人去服侍,落得好不可怜。张法师从此来来去去,更是毫无顾忌。此情形村人皆心里明白,但在生活艰难份儿上,并不觉着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却说那天夜里,张法师告别黑女大,回到水花家中,向有灯光的东边窑走去。进门见黑烂一家人在炕上坐着。水花看他回来,忙说:“你也快到炕上暖脚。”法师看了一眼黑烂,水花忙说:“或许你先把你黑烂哥背过去。”法师说:“那也成。”说完,大家一起协帮着把黑烂扶到银柄背上,由法师背到西窑。黑摸着将黑烂放到炕上即要转身,黑烂喊起来:“给我把灯点上。”法师说:“你还需点灯?你没看我这会子忙着呢嘛,得赶快过去忙着拾掇明黑给马驹子戴笼头的事情。”说着走了。
东窑里过来,水花问:“马驹的事说妥了?”法师道:“妥了妥了。”说着从桌桌上取了包袱,脱鞋上炕,趁着油灯打开包袱。水花对娃说:“去,快到那边窑里睡去,明早还得上学。”山山好奇心重,不舍走,但妈的话又不能不听,迟迟委委下了炕,出门走了。
张法师将道袍等一揽行头摆在炕墙上,又从中取出一张黄表纸来,在炕头展开,取了一管毛笔,蘸着包袱内的一瓶无色药水,屁股撅起写下现编的一段:“西天取经神马再世贱民刘武成大敬大仰无奈田畴劳力人手亏乏意欲从耕驾之役恭请土地诸神因假东沟弟子银柄之口传话天庭……”等等文字。写好搁在炕席上晾干。待那头水花铺好被褥。张法师不紧不慢脱了衣服睡下,与水花做在一处,自是常事。做完之后,张法师光着个干瘦的身子蹲在炕上,收黄表于包袱之内。吹熄了灯火,说了一阵子话,此夜不再有啥。
天亮时候,两人几乎是同时睁开了眼睛。窑里阴冷,那水花反趁到张法师的被窝里。张法师一面抚摸一面对她说道:“从今往后,甭再把黑烂弄过来了,人看着心憷的。”水花说:“平日就在那边窑里,吃饭时送一碗就完了。哎,你晓我昨黑做了个啥梦?”张法师问:“啥梦?”水花舌舌喋喋地说:“我梦见我是在河沿上走哩,一只大蛤蟆随着我的脚步,前前后后蹦跳着,弄得我左闪右闪,没下脚的地方。你说,这是啥梦?”张法师沉吟了阵子,问道:“那蛤蟆是啥颜色?”水花说:“我记不清了,好像满身是黑麻点子。”张法师又问:“它没冲你叫唤?”水花说:“好像是叫了。”张法师道:“此乃吉祥之兆,近日内必有外财得手。”水花说:“你若不填我一些,有谁予我啥财?”张法师道:“不是指我,是旁人。”水花心喜,不言声了。心念道,自己如今的作难,亲戚们远远看着,单怕走近了粘穷,一院的清凉黄风,何以有外财入手的机运?此时又听西窑门响,忙退过身,回自己被窝,说:“娃起来了。”话音刚落,山山推门进来,黑摸着在窑后头的馍笼取了个玉米窝窝,掩门去了。水花说:“我先起,你睡你的,等饭好了我叫你。”张法师应声,又睡了过去。
这天白日,张法师一直囚在黑烂家中。水花在午饭之后,抽身出去到槐树底下,女人堆里,神神叨叨地对婆娘们说了一阵。婆娘们看那水花说得有鼻子有眼,听着听着,倒将那水花惊羡一时,且有恨不得是她的那种意思。
天将黑时,张法师借说去茅厕,出了院门,信步在村里头转悠。到了大队部门前,只见那里立着一人,獐头鼠目甚是难看,一双贼眼盯着他,只是死瞅活瞅。隔远处又听见村里几个青年呼朋唤友,像是有事。他忙隐到路边,溜住墙根,快步回走。
一进门,便对在灶火头烧汤的水花慌张说道:“瞎了,今儿个我觉得不对。”水花问:“咋的?”张法师道:“今儿个我觉着不对,村里头不安静,像有民兵活动。”水花说:“甭怕,那帮子人经常这相,一到天黑便张张狂狂地排村窜哩。”张法师问:“这是为何?”水花说:“你没听说,现在全国上下都在闹哩,我村来了个工作组,见天领着社员学文件。”张法师道:“今日我觉着不对,今黑看来不做为妥。”水花说:“甭,没什钱事!再说是生产队里请你,你管它的毬毛不沾灰。”张法师一想:“说是这理,但我预先觉着不对。刚才我去小解,听头上嘎嘎一阵乱叫,抬头一看,一群嘎鹊在门前的树梢上胡飞乱舞,极不是好兆头。”水花说:“你多心了,天一黑那嘎鹊便是如此,天天不误,你怕啥嘛!”张法师道:“你们屋人不晓,我觉着这里头的的确确有些问题。我在大队部门前,碰见一个怪人:长得立眉狰眼,不是相况。”水花问:“你说说是啥模样。”张法师道:“披着军大衣,像是国家干部。”水花明白过来:“嗨,那是季工作组,没事,他才不管这些小事。”张法师道:“不成,今黑的事我不想做了。”水花急了,道:“不做咋行,到手的玉米和布你不想要了;再说你和黑女大已经商妥,半路地撂下,给人咋说?”
张法师蹴在炕棱上,想了又想。脱鞋上炕,刚摸住烟锅,水花端上来一碗糊汤给他。他紧忙趁着油灯,吸了几口。这时山山放学回来。撂下书包,说起学校里的事。黑脸将人家社宝打了,社宝妈掇着娃到学校里嗷开了:“把我娃打成这相,嘴扯得像簸箕,眼打得像铜铃;挨毬的老师偏心,不说管管黑脸他那贼娃,由他打人的是?妈日的,这是啥毬学校嘛,让那贼日下的就这么着张狂哩!”水花和张法师有心事,没理他。此时突然听到院子外头有人喊水花。
水花放下碗,开门一看,是黑女大,忙说:“快进来说话,院子里冷。”老汉手插袖筒,嘶喉嘶喉抽着凉气,跌跌撞撞进窑里,炕棱上坐好,向那要起身的张法师叫喊道:“你随咋甭动弹,我还说叫你到我屋吃饭哩,看这……”水花说:“哪里不都一样,不过到时候算酬头时,甭忘了没在你屋吃即是了。”老汉说:“那是当然。”
张法师沉下张脸,说:“今黑这事,恐怕是弄不成了。”黑女大吃了一惊,问:“咋?”张法师道:“你不晓得,政府如今抓这事,抓得紧得很哩,万一叫觉摸着就瞎了。”黑女大说:“没事没事,咱两个在饲养室悄没声地把事做了不就对了?”张法师说:“好老哥哩,你不晓得这其中的风险!”黑女大道:“不怕不怕,甭说不会出事,就是出了事也有队长海堂顶着,你怕啥嘛!”水花插言道:“我刚才还对他说,海堂办事稳着哩,不会让你受害。”张法师点点头,看来是心放下了。
水花问黑女大:“你黑女十几了?”黑女大说:“十六了,再过个把月就十七了,腊月二十八的生日。”水花说:“十六长了个大个子,那天我见着,迎面就叫婶子,嘴巧得很,人看着惜得不成。”黑女大说:“啥都不会,只是长得高,不抵啥。”水花说:“你说的,女娃到这时,过个日头是个样子,过个日头是个样子,一日比一日变得好看。”
黑女大看张法师放下的一只空碗,笑着说:“咱该走了。”张法师沉吟一下,只得说:“走便走。”携了炕头的包袱,黑女大忙接过去,一手搀着下了炕。山山说:“我看去。”水花说:“甭,一会儿同妈去,甭叫人看见一去一大帮子人,起了疑心。”黑女大对水花说:“我们先走。”水花收拾碗筷,边收拾边答道:“你们走,我一会儿去。”说完,黑女大和张法师出了窑门。到饲养室,包袱刚打开。这时,只听门外一阵乱响,一帮子莽头大汉冲了进来。黑女大抬头一看,是吕连长带着民兵来了。民兵扭住张法师,同时一边抄了现场,转身扬长而去。黑女大慌了手脚,跟屁股追到大队部,一旁不停地辩解。
季工作组指着他的鼻子道:“你不要吵,再吵连你一起抓了。我早对你说过,要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觉悟,你不听,犯下今日的大错。今黑要不是论你还要喂牲口,你也得来受审,你以为咋?避尸(滚开)!明早来大队部报到,批斗大会上,你得首先检查认罪。”黑女大还要说什么,吕连长示意民兵狗蛋。狗蛋上来,也不管他年老不年老,啪啪就是两个耳巴子,抽得老汉靠在门上不敢言喘。只可怜那张法师,被这帮民兵簇拥着从饲养室押到大队部,一路上拳脚相加,肆意折磨,直将一方能人之首,打得是神灵出窍,口鼻生烟。作法行头倾囊没收,搁在公社里多年,一遇破除迷信的运动,便拿出来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