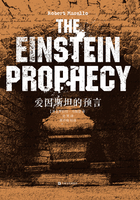据说这个姑娘随后又谈了两次对象,想必都是家境殷实的男生。可不知为什么,也都无果而终。总之,她也失败了,她为此付出的不仅仅是贞节,还有学业,同宿舍的其他女生都考上了研究生,她只能拿着一纸本科文凭回老家任教,接着火速相亲,嫁给当地一个二百多斤的富二代。
几年后,提起这个中文系姑娘,社团的老同学们直言她有这样的结局也算不错,但我还是为那份长相和气质遗憾,作为一个少有的知性范儿的姑娘,她不应该只得到这些。
老同学们提供了更多的八卦,说这个姑娘生了娃娃,做了母亲,各类聚会,从来都是一个人参加,依旧喜欢摆出一副高贵的架子。她喝完酒后喜欢对身边的人抱怨,抱怨过去,抱怨现在,抱怨所有曾令她付出过的东西。她注册了两个QQ号,一个号码扮演贤妻良母,一个号码贴满黑金属摇滚和极端自由主义的绘画,她一遍又一遍地对人诉说着“婚姻就是长久地忍受痛苦”之类的话。
有人说:女人是爱情最大的消费者。可现实中很多女人并不迷信爱情,她们更迷信物质带来的生活。女人看重物质,源于中国绵延几千年的男权制度,生产资料由男人把持,女人就不容易得到尊重,选择更好的男人成为她们唯一可追求的人生目标,也是她们唯一的安全感,薛宝钗这样冰雪聪明的女子,也只能把前途押在男人身上。
所以,我不恨那个中文系姑娘,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的权利。我也不再诋毁大学生的恋爱,这显然低估了大学生的心机,一部分大学生确实付出过真心,比如我这样的,一部分大学生也远比我想象中成熟,比如那个最终得到了金钱的中文系姑娘。
与中文系姑娘分手的当晚,石家庄下了四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我望着窗外灯光中凌乱的雪花,几乎心碎了。这段夭折的感情给我的价值观带来的毁灭性冲击影响了我许多年,我再不敢轻易相信女人,再不敢轻易触碰心灵,一个人穿着盔甲走到了今天。
4.轰隆隆的歌谣
尽管遭遇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情劫,如今回忆起大学,我还是会告诉人家,我的大学是幸福的,因为我有摇滚乐。
为什么总会有人在青春期迷上这种吵闹的音乐?也许真像某位朋友说的:这些孩子的童年太糟了。不幸的身世让我们比同龄人早一步见识到人性中的虚伪,也早一步学会了独立思考。对我们来说,这种奇怪的音乐带来的不只是感官高潮,还有一扇重新认识世界的窗口。没有人再去听那些无病呻吟的港台流行乐,也没有人再去信那些虚伪的主流教条,大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诗歌与哲学,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追求快乐的方式。
红旗大街,是石家庄最知名的高校聚集区,也是省城最知名的夜市,这地方只有一样商品与我有关,就是打口唱片。作为最后一代打口青年,卡带、CD、音像店、地下演出、摇滚杂志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课余时间,花掉了我全部的零花钱。那个时候的裕大,整届中文系也不见得有五个人知道大卫·鲍伊,更不会有人理解为什么要花钱买这些残破的卡带和光盘。
当年石家庄有三处著名的打口店,分别是倚梦、极端音乐和金旋律。我对倚梦的感情很深,不光因为这个店在裕大旁边,还因为他们光明正大地在货架上摆出打口唱片。倚梦的店员是老板娘的弟弟,也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帅哥,他每次看到我,都会递一支烟笑着打招呼。他蹲在地上,拧开功放,陪我一起聆听Tiamat乐队(提亚马特,瑞典的一支乐队)的专辑,听得酣畅淋漓时,指着窗外的雾霾天说:“你看,这种天配上这种音乐,多带劲儿!”
可惜,我们赶上的只是打口时代的小尾巴。自2004年开始,MP3铺天盖地,喜爱音乐的青年有了更多获取国外音乐的渠道。很快,倚梦开始为客户提供下载服务,金旋律也摆上了空白盘和刻录机,卡带、CD彻底被淘汰,我们亲眼目睹了唱片工业的陨落。
因为品味的独特,我在学校的朋友不多,基本都是通过摇滚乐小圈子认识的,分散在不同的学院、不同的班级。那几年,我一直扮演着摇滚乐迷召集者的角色,穿着重金属的T恤、戴着耳钉四处奔走,在校园二手市场摆摊卖打口带,在社团报纸上发表有关摇滚乐的文章,在其他学院宿舍发放摇滚杂志,甚至和朋友一起接受学校电台专访,用公共平台向全校师生播放Metallica(金属乐队)和Pink Floyd(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歌。但这些举动无一不是徒劳,没有人响应我们,甚至连我们参与编辑的报纸也停了刊。
我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传播摇滚乐,是在学院的送老生晚会上。当时我背着一把破吉他走到舞台中央,低着脑袋演唱了一首改编自鲍勃·迪伦的民谣,台下小马扎上坐着数百名大一新生,远处角落里围着数十名大三、大四的老生,他们一个个都盯着我,等着我出洋相。我唱到一半,台下开始嗡嗡作响,显然大家不喜欢这首歌,也不喜欢我,他们多么希望我演唱的是乌龙节目表上的那首《同桌的你》。演出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在机房观看晚会录像,发现自己在台上傻得不能再傻了,灯光把我的脸照得像失去亲人一般惨白,脸上、腿上的肌肉随着和弦上下抖动,活脱一个胖乞丐在唱民谣。我不忍心再看,走到楼道里默默点燃一支烟,心想这是何苦呢,将来我要是成了伟人,这段录像还不得传疯了啊。
人都是这样,只有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审视自己,才能发现自己的丑态。就像我长久以来对裕大各方面的抱怨,换个立场,这些都不过是一个偏执狂的成见,我和其他心胸狭隘的小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我甚至比他们更可恶,因为我有太多泼妇式的一厢情愿。
在外人眼里,摇滚乐又何尝不是丑陋的音乐呢?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将全部的快乐都拿出来与他人分享。
我放弃了摇滚乐迷召集者的角色,伴随着无尽的失落,这份失落远远超过当初那个中文系姑娘对我的遗弃。因为在我看来,别人的否定远没有自我质疑来得可怕,当你最引以为傲的东西不能给你带来理解与尊重,也就是孤独到了最深处的时候。我归还朋友的吉他,扔掉床头的摇滚杂志,重新回到图书馆三楼,整整一年都趴在厚厚的书籍上睡觉,等待着这一切最终落幕。
2005年冬,红旗大街一所高校的学生手持棍棒冲出校门,光天化日之下打砸高教市场里的平民超市,蓝色的碎玻璃和白色的运动鞋散落在街边,无一人敢去打扫。2006年秋,红旗大街夜市上发生群殴,十几个设计学院的男生追打一名校外摊贩,板砖泡着鲜血静静地躺在路人的脚下。2007年春,裕大北宿舍一名女生从六楼飞下,原因是保研未果。同一天,科技大学也有一名女生轻生,原因是相恋四年的男友把她玩腻了。2009年夏,音乐学院晚会的舞台上演真实版“王子复仇记”,女演员谢幕时被上台献花的男生一刀刺死。
现实生活远没有摇滚乐真诚,却远比摇滚乐残酷。
大四,是就业的时期,已没有什么课可上,少数与老师关系好的学生获得保送,大多数学生自己制作简历在招聘会上投递。我得到一家广告公司青睐,搬出学校实习,离校前,我招来所有同窗,打开自己收藏的那一箱子打口唱片,说:“要毕业了,没什么送给大家的,大家认识我也就是从这些东西开始的,随便拿吧。”半小时后,箱子空掉,我的青春正式宣告结束。
我最后一次停在舞蹈系练功房后,透过灯火向内望去,女孩子们穿着统一的黑色紧身衣,扎着统一的马尾辫,旋转着,跳跃着,细长的手指划破飘舞的光线,绽放的睫毛挑动流动的琴声,像一群恸哭不止的精灵。离开练功房,我的清澈演变为凌乱,眼前裕大的孩子们,将来都要脱掉学生的行头,去做白领,去做学者,去做官员,去做“资本家”,我们会在各种流水线上学会各种技术、各种规则,只因为我们向往同一种美好的生活。
5.没有母校的人
昔日的大学同窗,如今从事各行各业,靠祖上关系委身豪门的,回老家做人民教师的,在私企公司做小主管的,开网店搞创业的,时光飞逝,岁月匆匆,男人们开始发福,女人们开始身材走样,有房的结婚,没房的也要结婚,接着为孩子的户口发愁,为事业的出路焦虑,为爱人的不忠愤怒,为亲人的逝世伤神,有些人在股票大盘前手舞足蹈,有些人万念俱灰地站到了天桥边缘。而仅仅在十年前,他们都是那个跟着家人踏进裕大校门的一脸羞涩的孩子。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男人如何才算成功?男人们向往妻妾成群、车库并排、随从遍地,追求的是钱,是地位,是名声,那有了钱、有了地位、有了名声以后呢?人生是不是只剩下了吃喝玩乐,或者说人生本来就是吃喝玩乐?当年在一起玩摇滚的美术学院的小哥们儿,毕业后丢掉画板剪掉长发,在高教区支摊卖起女装,不出两年就开了分店,三年后更是买到了曾经梦寐以求的天价限量版电吉他。可他还会弹吗?还有时间弹吗?他会不会摆出一副恶心的样子直接告诉别人,他买这把琴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买到?中文系的贫困生小高,毕业后选择去遥远的塞北教学,选择塞北,不是因为那里有马奶酒和烤羊肉,而是因为与世隔绝的环境,他期望着坝上的清风能一点点洗去他往日的耻辱与伤痛。五年后,他洗完了,吃胖了,用公积金买到当地一所两室一厅的房子,可他随后跑到北京,告诉我他受够了那个地方,他想去大城市发展,他甘愿为此辞去教师的工作、卖掉新买的房子,只要能走出那片草原。
??2010年,我在通州区遇到两个20世纪80年代末出生的男孩子,其中一人是我同学所在公司的少东家,也是他的直属上司。这些人在我的住处冲我显摆他们的奥迪车,显摆他们的漂亮女友,显摆他们能够熟练地演唱台湾流行歌曲,熟练地偷取QQ农场的蔬菜,但他们不知道姜文是谁,更别提梁实秋、黑泽明、巴菲特、史蒂芬·霍金、米兰·昆德拉这些浮云般的名讳,他们生活得很幸福,他们会这样幸福地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
2011年,我回到裕大,那里已盘给了其他学校,图书馆、文学院的牌子都没了,传播学院看起来也更加陈旧。我们当年入住的宿舍区,被区政府收回后变成了鬼城,门窗生锈,灯柱破裂,杂草丛生,纸屑遍地。长长的树荫下,只有我一个人慢慢地走着,我努力回想着这里曾有过的无数年轻而嘈杂的灵魂,却不过是一段与这里相似的凋零殆尽的往事。回京的火车上,我对朋友说:“北大、清华的学生到六十岁还能拥有母校和青春印象,裕大的一部分孩子不再有了。”事实上,我的小学校园、中学校园也都不存在了,我和这个时代众多城乡结合部的孩子一样,正式成为“没有母校的人”。
2012年,我破例第一次参加裕大老同学的聚会,也最后一次失望,在场所有的人均不再是当年的模样。讽刺的是,他们也指责我变了,说我变得世故、变得冷漠、变得虚伪。我告诉他们,我真实过,只是他们忘了。那天的酒刚喝到一半,我就提前离开了酒店,独自一人去逛后海。前井胡同的尽头,我邂逅一双黄绿相间的袜子,我盯了它很久很久,离开时又情不自禁地哭了,它如此眼熟,我竟想不起谁曾经穿过,是男生还是女生,是我曾经爱过的人吗?他们穿着这双鲜艳的袜子在风中游走,像团燃烧殆尽的火焰。
2013年的平安夜,我终于梦到了那个中文系姑娘。她远远地站在舞蹈系练功房后等我,依旧那么年轻,依旧那么漂亮,我笑着走过去,告诉她我愿意做她的朋友,她也笑起来,问我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要去北京,她问为什么,我说也许那里有特别的东西,我会在那里租房,在那里工作,甚至爱上那里的一个姑娘,我还会忘了她,忘了裕大,忘了自己来自什么地方,因为缘分是有尽头的。
人们在纵横交错的电流与数字生活中重新找到了生存的方向,一切,又回归平实、平庸与平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