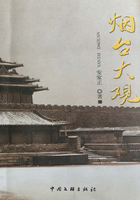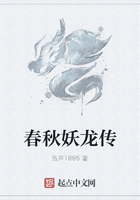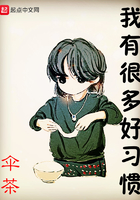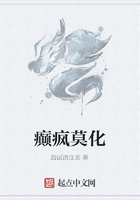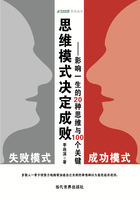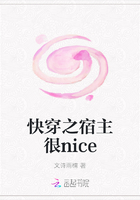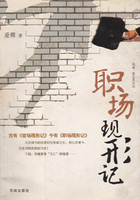俗谓“京油子,卫嘴子,河北保定的狗腿子”,这话在局中人和局外人看来,评价自然大不相同。“老北京”萧乾对北京和北京话情有独钟,认定“到过十来个国家的首都,哪个也比不上咱们这座北京城”,他自然也不会承认“京片子”的“油”或“贫”。但这“油”与“贫”又确实是不在少数的外地人对北京话的感受。“京油子”的“油”也可以从毕树裳辑录的歇后语和比喻中看出来。遇到胡同深处大杂院里的老爷子、老太太,赶上和他们唠嗑,还可以经常听到他们嘴里冒出这么地道、传神而有味道的说法。
但“京味文学”的广为传阅和深受好评,却也说明北京话的影响。说起京派文学,大家容易想到的是居住在北京的和以北京话入文学的现当代作家,这可以拉出一长串名单:老舍、萧乾、沈从文、林徽因、汪曾祺、林斤澜、邓友梅……正像我们一说起海派文学,就想起施蛰存、穆时英、叶灵凤、张爱玲、王安忆一样。其实,要说京派文学,我们不应忘记《红楼梦》、《品花宝鉴》、《儿女英雄传》这样一批以漂亮而有味道的北京话渲染出丰富人物性格,描摹出精彩北京生活的文学经典。以方言创作文学,并产生较大影响的,除了北京话(如语言大师、京派文学祭酒老舍的大量作品),大概只有吴方言了。可惜后者只有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等了了之数,无法与前者深厚的传统相提并论。
说京腔、京韵,除了黄裳谈论的国粹之一——自然也是北京文化的精粹——京剧之外,还有相声、京韵大鼓,以及闻国新津津乐道的“北平的说书”。书场中代卖清茶,也和听京戏一样,“是一边品着旗枪的滋味,一边品着说书的滋味的”,那样的悠闲,真不是我们今天守着电视机看肥皂剧的生活方式可比的。
北京城杂忆①
/萧乾
一、京白
五十年代为了听点儿纯粹的北京话,我常出前门去赶相声大会,还邀过叶圣陶老先生和老友严文井。现在除了说老段子,一般都用普通话了。虽然未免有点儿可惜,可我估摸着他们也是不得已。您想,现今北京城扩大了多少倍!两湖两广陕甘宁,真正的老北京早成“少数民族”啦。要是把话说纯了,多少人能听得懂!印成书还能加个注儿。台上演的,台下要是不懂,没人乐,那不就砸锅啦!
所以我这篇小文也不能用纯京白写下去啦。我得花搭着来——“花搭”这个词儿,作兴就会有人不懂。它跟“清一色”正相反:就是京白和普通话掺着来。
京白最讲究分寸。前些日子从南方来了位愣小伙子来看我。忽然间他问我“你几岁了?”我听了好不是滋味儿。瞅见怀里抱着的,手里拉着的娃娃才那么问哪。稍微大点儿,上中学的,就得问:“十几啦?”问成人“多大年纪”。有时中年人也问“贵庚”,问老年人“高寿”,可那是客套了,我赞成朴素点儿。
北京话里,三十“来”岁跟三十“几”岁可不是一码事。三十“来”岁是指二十七八,快三十了。三十“几”岁就是三十出头了。就是夸起什么来,也有分寸。起码有三档。“挺”好和“顶”好发音近似,其实还差着一档。“挺”相当于文言的“颇”。褒语最低的一档是“不赖”,就是现在常说的“还可以”。代名词“我们”和“咱们”在用法上也有讲究。“咱们”一般包括对方,“我们”有时候不包括。“你们是上海人,我们是北京人,咱们都是中国人。”
京白最大的特点是委婉。常听人抱怨如今的售货员说话生硬——可那总比带理不理强哪。从前,你只要往柜台前头一站,柜台里头的就会跑过来问:“您来点儿什么?”“哪件可您的心意?”看出你不想买,就打消顾虑说:“您随便儿看,买不买没关系。”
委婉还表现在使用导语上。现在讲究直来直去,倒是省力气,有好处。可有时候猛孤丁来一句,会吓人一跳。导语就是在说正话之前,先来上半句话打个招呼。比方说,知道你想见一个人,可他走啦。开头先说,“您猜怎么着——”要是由闲话转入正题,先说声:“喂,说正格的——”就是希望你严肃对待他底下这段话。
委婉还表现在口气和角度上。现在骑车的要行人让路,不是按铃,就是硬闯,最客气的才说声“靠边儿”。我年轻时,最起码也得说声“借光”。会说话的,在“借光”之外,再加上句“溅身泥”。这就替行人着想了,怕脏了您的衣服。这种对行人的体贴往往比光喊一声“借光”来得有效。
京白里有些词儿用得妙。现在夸朋友的女儿貌美,大概都说:“长得多漂亮啊!”京白可比那花哨。先来一声“哟”,表示惊讶,然后才说:“瞧您这闺女模样儿出落得多水灵啊!”相形之下,“长得”死板了点儿,“出落”就带有“发展中”的含义,以后还会更美;而“水灵”这个字除了静的形态(五官端正)之外,还包含着雅、娇、甜、嫩等等素质。
名物词后边加“儿”字是京白最显著的特征,也是说得地道不地道的试金石。已故文学翻译家傅雷是语言大师。五十年代我经手过他的稿子,译文既严谨又流畅,连每个标点符号都经过周详的仔细斟酌,真是无懈可击。然而他有个特点:是上海人可偏偏喜欢用京白译书。有人说他的稿子不许人动一个字。我就在稿中“儿”字的用法上提过些意见,他都十分虚心地照改了。
正像英语里冠词的用法,这“儿”字也有点儿捉摸不定。大体上说,“儿”字有“小”意,因而也往往带有爱昵之意。小孩加“儿”字,大人后头就不能加,除非是挖苦一个佯装成人老气横秋的后生,说:“喝,你成了个小大人儿啦。”反之,一切庞然大物都加不得“儿”字,经如学校、工厂、鼓楼或衙门。马路不加,可“走小道儿”、“转个弯儿”就加了。当然,小时候也听人管太阳叫过“老爷儿”。那是表示亲热,把它人格化了。问老人“您身子骨儿可硬朗啊”,就比“身体好啊”亲切委婉多了。
京白并不都娓娓动听。北京人要骂起街来,也真不含糊。我小时,学校每年办冬赈之前,先派学生去左近一带贫民家里调查,然后,按贫穷程度发给不同级别的领物证。有一回我参加了调查工作,刚一进胡同,就看见显然在那巡风的小孩跑回家报告了。我们走进那家一看,哎呀,大冬天的,连床被子也没有,几口人全蜷缩在炕角上。当然该给甲级喽。临出门,我多了个心眼儿,朝院里的茅厕探了探头。喝,两把椅子上是高高一叠新棉被。于是,我们就要女主人交出那甲级证。她先是甜言蜜语地苦苦哀求。后来看出不灵了,系了红兜肚的女人就插腰横堵在门坎上,足足骂了我们一刻钟,而且一个字儿也不重,从三姑六婆一直骂到了动植物。
《日出》写妓院的第三幕里,有个家伙骂了一句“我教你养孩子没屁股眼儿”,骂得有多狠!
可北京更讲究损人——就是骂人不带脏字儿。挨声骂,当时不好受。可要挨句损,能叫你恶心半年。
有一年冬天,我雪后骑车走过东交民巷,因为路面滑,车一歪,差点儿-把旁边一位骑车的仁兄碰倒。他斜着瞅了我一眼说:“嗨,别在这儿练车呀!”一句话就从根本上把我骑车的资格给否定了。还有一回因为有急事,我在人行道上跑。有人给了我一句:“干吗?奔丧哪!”带出了恶毒的诅咒。买东西嫌价钱高,问少点儿成不成,卖主朝你白白眼说:“你留着花吧。”听了有多窝心!
二、吆喝
一位二十年代在北京作寓公的英国诗人奥斯伯特·斯提维尔写过一篇《北京的声与色》,把当时走街串巷的小贩用以招徕顾客而做出的种种音响形容成街头管弦乐队,并还分别列举了哪是管乐、弦乐和打击乐器。他特别喜欢听串街的理发师(“剃头的”)手里那把钳形铁铉。用铁板从中间一抽,就会呲啦一声发出带点颤巍的金属声响,认为很像西洋乐师们用的定音叉。此外,布贩子手里的拨啷鼓和珠宝玉石收购商打的小鼓,也都给他以快感。当然还有磨剪子磨刀的吹的长号。他惊奇的是,每一乐器,各代表一种行当,而坐在家里的主妇一听,就准知道街上过的什么商贩。最近北京人民电台还广播了阿隆·阿甫夏洛穆夫以北京胡同音响为主题的交响诗,很有味道。
囿于语言的隔阂,洋人只能欣赏器乐。其实,更值得一提的是声乐部分——就是北京街头各种商贩的叫卖。
听过相声《卖布头》或《大改行》的,都不免会佩服当年那些叫卖者的本事。得力气足,嗓子脆,口齿伶俐,咬字清楚,还要会现编词儿,脑子快,能随机应变。
我小时候,一年四季不论刮风下雨,胡同里从早到晚叫卖声没个停。
大清早过卖早点的:大米粥呀,油炸果(鬼)的。然后是卖青菜和卖花儿的,讲究把挑子上的货品一样不漏地都唱出来,用一副好嗓子招徕顾客。白天就更热闹了,就像把百货商店和修理行业都拆开来,一样样地在你门前展销。到了夜晚的叫卖声也十分精彩。
“馄饨喂——开锅!”这是特别给开夜车的或赌家们备下的夜宵,就像南方的汤圆。在北京,都说“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其实,馄饨挑子也一样。一头儿是一串小抽屉,里头放着各种半制成的原料:皮儿、焰儿和佐料儿,另一头是一口汤锅。火门一打,锅里的水就沸腾起来。馄饨不但当面煮,还讲究现吃现包。讲究皮要薄,馅儿要大。
从吆喝来说,我更喜欢卖硬面饽饽的:声音厚实,词儿朴素,就一声“硬面——焊饽”,光宣布卖的是什么,一点也不吹嘘什么。
可夜晚过的,并不都是卖吃食的。还有唱话匣子的。大冷天,背了一具沉甸甸的留声机和半箱唱片。唱的多半是京剧或大鼓。我也听过一张不说不唱的叫“洋人哈哈笑”,一张片子从头笑到尾。我心想,多累人啊!我最讨厌胜利公司那个商标了:一只狗蹲坐在大喇叭前头,支棱着耳朵在听唱片。那简直是骂人。
那时夜里还经常过敲小钹的盲人,大概那也属于打击乐吧。“算灵卦!”我心想:“怎么不先替自己算算!”还有过乞丐。至今我还记得一个乞丐叫得多么凄厉动人。他几乎全部用颤音。先挑高了嗓子喊“行好的——老爷——太(哎)太”,过好一会儿(好像饿得接不上气儿啦),才接下去用低音喊:“有那剩饭——剩菜——赏我点儿吃吧!”
四季叫卖的货色自然都不同。春天一到,卖大小金鱼儿的就该出来了。我对卖蛤蟆骨朵儿(未成形的幼蛙)最有好感,一是我买得起,花上一个制钱,就往碗里捞上十来只;二是玩够了还能吞下去。我一直奇怪它们怎么没在我肚子里变成青蛙!一到夏天,西瓜和碎冰制成的雪花酪就上市了。秋天该卖“树熟的秋海棠”了。卖柿子的吆喝有简繁两种。简的只一声“喝了蜜的大柿子”。其实满够了。可那时小贩都想卖弄一下嗓门儿,所以有的卖柿子的不但词儿编得热闹,还卖弄一通唱腔。最起码也得像歌剧里那种半说半唱的道白。一到冬天,“葫芦儿——刚蘸得”就出场了。那时,北京比现下冷多了。我上学时鼻涕眼泪总冻成冰。只要兜里还有个制钱,一听“烤白薯哇真热乎”,就非买上一块不可。一路上既可以把那烫手的白薯揣在袖筒里取暖,到学校还可以拿出来大嚼一通。
叫卖实际上就是一种口头广告,所以也得变着法儿吸引顾客。比如卖一种用秫秸杆制成的玩具,就吆喝:“小玩艺儿赛活的。”有的吆喝告诉你制作的过程,如城厢里常卖的一种近似烧卖的吃食,就介绍得十分全面:“蒸而又炸呀,油儿又白搭。面的包儿来,西葫芦的馅儿啊,蒸而又炸。”也有简单些的,如“卤煮喂,炸豆腐哟”。有的借甲物形容乙物,如“栗子味儿的白薯”或“萝卜赛过梨”。“葫芦儿——冰塔儿”既简洁又生动,两个字就把葫芦(不管是山楂、荸荠还是山药豆的)形容得晶莹可人。卖山里红(山楂)的靠戏剧性来吸引人。“就剩两挂啦。”其实,他身上挂满了那用绳串起的紫红色果子。
有的小贩吆喝起来声音细而高,有的低而深沉。我怕听那种忽高忽低的。也许由于小时人家告诉我卖荷叶糕的是“拍花子的”——拐卖儿童的,我特别害怕。他先尖声尖气地喊一声“一包糖来”,然后放低至少八度,来一声“荷叶糕”。这么叫法的还有个卖荞麦皮的。有一回他在我身后“哟”了一声,把我吓了个马趴。等我站起身来,他才用深厚的男低音唱出“荞麦皮耶”。
特别出色的是那种合辙押韵的吆喝。我在小说《邓山东》里写的那个卖炸食的确有其人,至于他替学生挨打,那纯是我瞎编的。有个卖萝卜的这么吆喝:“又不糠来又不辣,两捆萝卜一个大。”“大”就是一个铜板。甚至有的乞丐也油嘴滑舌地编起快板:“老太太(那个)真行好,给个饽饽吃不了。东屋里瞧(那么)西屋里看,没有饽饽赏碗饭。”
现在北京城倒还剩一种吆喝,就是“冰棍儿——三分啦”。语气间像是五分的减成三分了。其实就是三分一根儿。可见这种带戏剧性的叫卖艺术并没失传。
注释:①选自《北京城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作者萧乾(1910-1999),现代作家,记者,翻译家。著有《篱下集》、《梦之谷》、《未带地图的旅人》等。
叫好①
/黄裳
“叫好”在南方曰“喝彩”,或者也是所谓“雅言”乎?这是一种捧场必备的条件。如果角色登台,无人叫好的话,则没有苗头,难为其为名伶了。
考叫好,古已有之。《燕兰小谱》注有云:
北人观剧,凡惬意处,高声叫好!
《梨园佳话》上亦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