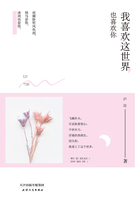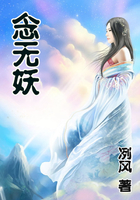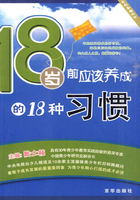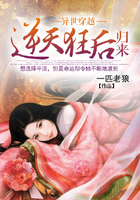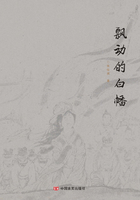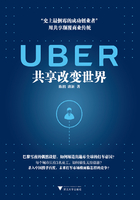莫言自说:
打一个形象化的比喻,如果说我的作品都是高密东北乡版图上的建筑,那《生死疲劳》应该是标志性的建筑。
《生死疲劳》是用了章回体的外部形式,实际上是看作是应该向我们的传统致敬的表现,你把这个章回体换成小标题也完全可以,换成1、2、3、4也完全可以,有了这在形式上向传统小说靠拢。你提到了里面超现实的神话色彩,《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就更不用说了,包括《儒林外史》里面都有神神鬼鬼的地方,这跟中国的长期以来的皇权思想有关。一般讲到皇帝,统治者没有办法证实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就说皇权是天赐,我这个皇帝就是真龙天子,当赵子龙怀揣着阿斗在陷阱的时候,外面的追军过来,这时候一道红光突起,带着真命天子的赵子龙飞出了陷阱。还有,因为涉及到历史,历史往往是传奇,尤其在民间口头流传日久的历史故事,不知不觉被神秘化和传奇化了。
我想我们的读者也绝对不会说莫言在宣传封建迷信,六道轮回——人死了会转成别的动物。民间有很多这样的传说,比如大家说谁家的牛就是他爹托生的,谁家欠了人家很多债,死后变成人家的一头驴天天给人家拉磨……我觉得现代的读者受了这么多科学文明的教育,会正确的理解。
我写这部小说的真实的意图是我认为六道轮回就是时间,轮回来轮回去,在时间的长河里,面对生死,给一个人提供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当每一个人经过生死考验的时候,这个人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当时极左的路线之下,被枪毙的这个人带着很深的怨恨,在生生死死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在时间的长河里面,让他有一次次面对生死,面对生命的机会,最后重新转世为人。我想这是一个隐喻,或者是带有某种象征性的东西。
“大我”与“大声”——《生死疲劳》笔记之一
■李敬泽
一
一个冤屈的厉鬼在大地上游荡——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由此开始。
对这个鬼,我有一系列问题:
他是谁?当然,他名叫西门闹,是一个在历史大变中横死之人,他因他的身份而死,但在自然法的衡平之下,他其实并无死罪,他甚至是个勤劳善良的有德之人。
由此,莫言似乎是承袭了中国文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主题:浩大的历史意志与渺小的个人命运。历史无所不及且不加拣择,个人无所遁逃而孤弱无告。
在这个格局之下,当代文学的一个基本冲动就是在历史的轰鸣中寻求和倾听个人的声音,这是自我倾听和自我倾诉,是要回应和求证一个现代问题:我是谁?
正是在这个地方,西门闹与这个时代的文学想象中他的无数同命运者分道扬镳。他完全不为“我是谁”的问题所困扰,对他来说,他是谁是天经地义、毫无疑义的,他是乡村经济、文化、伦理生活的中心,是承担“天道”之人,他的全部生活具有一种“自然”的正当性,如同四季交替,春种秋收。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推动着他的那种“冤屈”,那是被“天道”所遗弃的冤,是天地不仁的屈;这个人的根本困境是,他有所信,这种所信是如此广大和踏实,它包含生与死,包含绝对的应许——天地大义应许给人的一份公平;但是现在,他发现,他的“天”暗自改变了主意,他不知在他头上运行的“天”已经被“历史”所取代,这是一种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和方向的意志,他当然没有机会领会和顺从这个新的“天”,他甚至不知道这个新的“天”是什么,他只能在他的世界逻辑中顽强地要求公道。
在古老中国的民间想象中,大地的夜晚总是游荡着这样不屈、不散的魂魄,我们曾经相信——并非出于理性,而是出于内心最深处的敬畏——那些冤屈的厉鬼郁结了人世的所有悲苦和不公,他们因此不安息,也因此有权向天、向我们索要。我们对生活和世界的最黑暗的想象在这些严厉、狰狞的影子中惊悸地展开。
这是中国精神中已遭祛魅的一脉传统,它也许还在人心的偏僻角落中活着,但它肯定已经在我们阳光普照的世界图景中消失。但是现在,莫言在《生死疲劳》中让它活了过来,在现代中国的背景下,这个厉鬼森严猛烈地挣扎。
那么,他是谁呢?
西门闹是通行的文学思维无法捕捉的鬼魂,在小说艺术的意义上,他是一个“人物”吗?在哲学意义上,他是一个“个人”吗?他都不是。他是西门闹,但通过转世轮回他又是一头驴、一头牛、一头猪、一条狗、一个猴和一个名叫大头儿的人,每一次新的生命都是新的性格和命运,你无法把他当做“这一个”进行界定,他是“这几个”;你也不能将西门闹和他的几度转世仅仅看做是机巧的结构,“这几个”不仅分担着渐渐稀薄的记忆,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有魂魄、精气贯注。他们中的每一个是“我”,也是“他”,是过去、未来和可能的“我”。
在现代思想背景下理解西门闹是困难的,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中国传统的世界观,那么,西门闹就是自然的;在那古老的世界观中,大道运行,万物各秉精气而生,在身体、表象之下,世界有共同、普遍的根源。
这种世界观无疑已在现代以来的观念竞争中落败,但那是仓促、草率的溃败,落日应该有壮丽的余晖,而我们似乎一直没有来得及回头看看,似乎在一夜间,轰鸣的电声遮盖了天籁,古老的乡土沉沦,全球化的大神降临。
但是在这一往无前的变化中,莫言停下来,回头看到了一个巨大空间,这个空间属于他自己,一个对乡土和传统的悲壮命运有着血肉体认的中国作家,一个有着直觉的、身体的旺盛力量的作家,一个狼吞虎咽、暴饮暴食的作家,一个对生命之酷烈、之浩大和渺小有着东方式的执着和坚忍的作家——最后这种品质常常使饱读西方诗书的神经脆弱的知识分子们感到混杂着厌恶和罪感的不适:人怎么能这样?他们忘了,中国人从来就是这么想、这么经验的,“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这是脆弱,也是坚忍,是天地无情,也是天长地久,中国作家中,懂得这句话的唯莫言而已。
在这个巨大的空间里,莫言的兴趣并非历史,对历史叙事的判断、质疑或拆解从来不是他的目的,他对历史的看法并未超出80年代以来的主流论述,他所关注的焦点一直是乡土的、民间的、恒常默运的中国被强行纳入现代化进程的巨大震荡:酷烈的挣扎和牺牲——《红高粱》、《檀香刑》、《生死疲劳》,都起于或终于“横死”,那是来自外部的力量对世界秩序的决定性干预。
这并非是莫言的真正力量所在——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一直在努力理解和表现这种震荡,莫言与我们的区别在于,他有一个简明而自觉的世界模式:他把高密当作世界的中心,由此他斩截地判断内部和外部,他站在内部,绝对地相信内部,他在内部感受疼痛和困苦,他在内部寻求词汇、观念和形式。
我相信这最初是出于本能,但渐渐地成为了莫言的自觉纲领。由此,他使高密成为了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的一个壮丽景观,它就在我们内部,但它一直沉默,我们对它畏惧、陌生、无以言喻。
在这个背景下,西门闹才能被理解,才是自然的,他不是“这一个”,他也不是“个人”,他是“一本万殊”之本,是灵鹫峰下的那块顽石,是一个“大我”,是四处寻求肉身和血的精神和记忆。
二
《生死疲劳》壮阔、浑浊、激流汹涌。它不完美,如同生活般不完美,我想我能挑出它的一百个缺点,但是我认为,它仍然是、而且可能恰恰因此是一条生气沛然的大河。
《生死疲劳》是关于人与土地的书、关于生与死的书、关于苦难与慈悲的书,也是关于白昼和夜晚的书。白昼中的一切属于人和历史,但在夜晚,世人皆睡而万物醒来,万物不再属于人,它们属于自己,土地在月光下恢复灵性——这是蒲松龄的看法,也是莫言的看法,《生死疲劳》那些最为华美天花乱坠的段落几乎都是流淌于月光之中,那个名叫蓝脸的农民孤独地走进夜晚,在月光照耀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争:成为唯一的单干户,守护着他的土地,对抗历史和白昼,从50年代战斗到70年代。
——蓝脸的脸一半被蓝色的痣覆盖,夜晚印在他的脸上,这是“红字”般的耻辱,也是大地之选民的神秘标记。
《生死疲劳》从1950年写起,总体性地讲述中国乡村五十年的历史、五十年百感交集的复杂经验。
人与土地的关系是乡村历史和生活的内在机枢,莫言的洞见在于,他看出了“我”的土地和“我们”的土地有着根本区别,这不仅是所有制问题,更是人的存在问题,农民大规模地离开土地是一个当代现象,但当土地不再是“我”的土地时,中国精神在人民生活中的内在断裂就已经开始。
土地曾经是古老中国的意义中心,是世界的起点和归宿,莫言知道这个中心已经瓦解,他怀抱颓败的土地,他决意对土地做出重述,把它放回中心,看着它在历史中渐渐荒废,让它在荒废中重新庄严、雄辩、令人敬畏。
宏大复杂的精神历程由此展开——
轮回是陈旧而顽强的东方想象,在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戏剧中,它是一个基本的世界模式,它来自佛教,也来自《易经》,来自灵魂不灭和万物有灵的古老信念,时间与世界如轮回转,循环往复,一切不会消失,一切皆会重来,就如大地生生不息。
这只车轮在现代之初即遭废弃,被笔直的公路所取代,中国人现在对世界的主流想象来自西方,不是圆,而是直线:堕落——救赎或者愚昧——启蒙或者落后——进步。莫言作为艺术家的志向不在于判断车轮正确还是公路正确,他只是意识到,那种向着什么地方前进的公路式的图景无法综合、贴切地表达中国人的经验,面对历史和现实及人心,如果我们宣布我们掌握着路线图那么我们就是骗自己。
这也是贾平凹在《秦腔》中面临的困境,一种总体性的精神贫困,无法给出支撑一切的精神叙事。
莫言应对这种困境的办法是,找回那只轮子,让它在想象中重新运转,轮回在《生死疲劳》中不仅是结构方式,而且成为永恒的生命意志的庞大隐喻。
人之轮回是因为执着,《生死疲劳》是执着的颂歌和悲歌,这里的一切人、一切生灵都是执着的、一根筋的,被汹涌的观念、欲望、激情所支配所驱策,躁动不息折腾不休,他(它)们争吵、流泪、爱、仇恨、贪婪、放荡,他(它)们崇高而卑微,他(它)们推石上山而义无反顾——
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和动物前前后后大概上百,我无从确认谁是主要人物(动物)谁是典型人物(动物),莫言猛烈奔放地展现了浩大的人流,他的老虎吃天般的野心是,包容人间万象,提供人的受苦受难和大喜大悲的苍茫全景。
《生死疲劳》又是一部关于记忆与遗忘的书。
轮回是为了遗忘,忘掉前世之苦、之怨、之冤缠孽结,而西门闹坚决地反抗遗忘,他不喝孟婆汤,喝了也无效,他要活着,可是也要记住。但是,经历一次次轮回,记忆终于被时间或历史渐渐抹去。《生死疲劳》的吊诡之处在于:它清晰地展现了记忆的流逝,但同时,当一切都渐遭遗忘时,遗忘的最终成果——那个转世为人后的大头儿却变成了一个狂热执着的叙述者,似乎遗忘就是为了更深刻地记忆。
为什么记忆又为什么遗忘?因为《生死疲劳》吞吐着巨大的疲劳:中国人庞杂喧哗百感交集的经验,因为疲劳,这部书始终在寻求安宁——它有一种终极志向,把这一切安放在某个地方,让它们尊严、宁息。
于是,莫言看到了土地。他在蓝脸的墓碑上写道:“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这句话承载着《生死疲劳》的全部重量。
这是一句铿锵的空话吗?也许是;是一句无可奈何的咒语吗?也许也是。但是我认为,在《生死疲劳》中所营造的图景中,它在艺术上和精神上都是一个雄辩的结论:在执着与苦难的命运之中运行着浩瀚的慈悲——莫言在《后记》中用的词是“大悲悯”,我认为这不准确,悲悯无论大小,都预设了拯救,上帝的拯救或人的自我拯救,《生死疲劳》的世界并非抵达拯救,它无法告诉人们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但是,它告诉人们土地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土地成为“慈悲”的象征,它就是这人世间,它承受和包容一切,一切爱欲欢乐和一切苦,悲喜交集。
就这样,在一种古老陈旧的想象中,我们的经验、记忆和命运找到了形式也找到了精神,破败的土地在莫言的讲述中——可能也仅仅在莫言的讲述中——恢复生机,重新成为安放一切的中心。
《生死疲劳》是向着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之伟大传统的致敬之书,是小说艺术精神的一次“认祖归宗”。
它的叙事结构异常复杂,三个叙事者,大头儿是巫一般全知的说书者,通天彻地;蓝解放是常人,是日常经验水平上的有限视角;而小说中的“莫言”是个“知识分子”,没他什么事,但是总是瞎起哄,到处提供似是而非的阐释,又像一个插科打诨的丑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