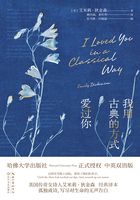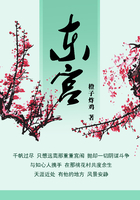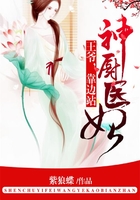吕效平
一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排演《浮士德》,是近年中国剧坛的一件大事。此事之大,不仅由于《浮士德》是德国文学巨匠歌德延续60年创作而成的“巨大的自白”,是与荷马史诗、但丁《神曲》、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并称的欧洲文学“四大名著”之一,尤其由于该剧由当代中国戏剧导演艺术的旗帜人物徐晓钟教授执导。二十多年前,晓钟教授执导的《培尔·金特》打开了中国话剧及其观众的视野,是那个令人振奋的思想解放年代的令人振奋的标志性戏剧艺术成果;他指导改编并执导的《桑树坪纪事》虽然诞生于“新时期”末,但至今仍然处于当代中国话剧的艺术峰巅——作为一部表现当代中国的悲剧艺术作品,同时作为一部成功融合“斯坦尼”和“布莱希特”这两个中国话剧最重要的剧场艺术理论资源的舞台作品,我不认为在“新时期”终结后能有一部话剧作品堪与比肩。
晓钟教授还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最有成就的戏剧艺术教育家,他的弟子蔚然长成当今中国戏剧导演的主力,其中不乏身处前沿的一流导演。可以说,徐晓钟的剧场艺术思想与方法,就是中国当今话剧舞台艺术的主流思想与方法。因此,八十高龄的徐晓钟教授再次出山,在中国话剧舞台上执导西方伟大的文学名著,无论其成功与否,都必然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文化艺术事件。这一重要的戏剧事件还因当年黄佐临先生邀请晓钟教授“来上海排《浮士德》”并欣然允诺担任艺术指导的约定,罩上了温暖的情感色彩——一代大师黄佐临已然仙逝,但他的艺术梦想始终被他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弟子和传人们惦念着,被身居北京的当代导演艺术宗师惦念着。伟大的《浮士德》是中国话剧的一个梦!
稍早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浮士德》的上演,中国当今著名的实验戏剧家孟京辉推出了他的新作《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就《浮士德》所追求的神圣感和《两只狗的生活意见》给人的粗俗印象而言,我相信很多人会认为把这两部戏放在一起谈论是不妥当的。在北京市剧协举办的一个论坛上,我就曾遇见对于《两只狗的生活意见》极度反感的戏剧艺术家,我知道他们并不在少数。但是,无论如何,徐晓钟的《浮士德》和孟京辉的《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剧场效果的反差之大,给我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象。这一印象又由于主流媒体和评论对它们的反应与它们在剧场造成的效果截然相反而大大地加强了,使我忍不住持续地在心中问自己:一边是所有在剧场看过《浮士德》的我的朋友和学生,在我问及他们时,都告诉我说“看不进去,剧场反应冷淡”,但是主流媒体和评论,包括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网页论坛版上的发言,却都对这个戏表达了很高的敬意;一边是《两只狗的生活意见》的每一次演出都热烈地点燃了剧场,许多看过它的青年朋友都向我赞不绝口地推荐这个戏,但是与年轻的戏剧观众不同,主流媒体和戏剧界对这个戏的反应却是冷淡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网页论坛版上的发言几乎一边倒地反感这个戏,有人因为对这个戏在青年观众中所受到的热捧感到失望,把它称为“一件皇帝的新衣”。
在一部其神圣追求赢得了普遍敬重却没有激活剧场的戏剧作品和一部热烈地点燃了剧场却很粗俗的戏剧作品之间,有没有一件所谓“皇帝的新衣”呢?任何一个真诚的艺术追求,不论最终是否名实相符,都不应当被称作“皇帝的新衣”。重要的是:如果说徐晓钟教授执导《浮士德》是2008年中国剧坛的一个重大事件,那么,我感觉,晓钟教授的神圣追求和孟京辉的率性粗俗在当代中国戏剧评价体系与活生生的剧场里截然不同的命运,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重要现象。我希望自己不久能够撰文讨论《两只狗的生活意见》,本文将只讨论晓钟教授的《浮士德》。
彼得·布鲁克在他那本著名的《空的空间》里,把戏剧区分为神圣的(Holy)或粗俗的(Rough)、僵死的(Deadly)或当下的(Immediate)。“神圣”和“粗俗”是戏剧的两个源头,无论从戏剧史上看或是从人的心理机制上看都是这样。神圣的戏剧,源自我们超越形而下感性生活的平庸,追求其背后价值与意义的努力,“是追求无形之物的渴望,追求比最充分的日常生活形式更为深邃的现实的渴望——或则是追求生活中失去的事物的渴望,事实上是庸人反对现实的渴望”。粗俗的戏剧,则源自我们摆脱生活的严肃意义,追求狂欢的欲望。“如果在神圣的戏剧所创造的世界里,祷告比打嗝要真实的话,粗俗的戏剧却与之相反。打嗝成了真实,而祷告则会被看成是滑稽可笑的。”古希腊悲剧主要源自于人类对生活之神圣意义的追求,而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则主要源自于逃逸神圣统治的民间狂欢。神圣和粗俗这两个戏剧的出发点,无论作为心灵的还是作为历史的,它们的价值是平等的,无所谓高下。难得的是能够像莎士比亚那样贯穿粗俗与神圣,既粗俗又神圣。然而,如果粗俗把戏剧降低为纯粹的娱乐,戏剧便在这娱乐中死去了——“真正的娱乐性戏剧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神圣的追求也不能保证戏剧的生命力——“任何地方都不像威廉·莎士比亚的作品那样,能够使僵死的戏剧悄悄地找到安稳、舒适的安身之处。他轻而易举地控制了莎士比亚。我们观看优秀的演员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他们的表演似乎无懈可击,他们生气勃勃,光彩夺目,剧中有音乐伴奏,每个人的穿着打扮都与最佳古典戏剧中所要求的一模一样。
但私下里,我们却感到这种演出无聊得出奇,在心里不是埋怨莎士比亚,就是埋怨这样的戏剧,甚至埋怨我们自己。使事情更糟的是,总有一些头脑僵化的观众,出于某种特殊原因,对缺乏强烈感甚至缺乏娱乐性的戏表示欣赏,就像那日复一日埋头于古典作品研究的学者,他之所以抬起头来微笑,是因为在他自己试验并论证的他钟爱的理论时,没有碰到任何干扰,他可以低声吟诵自己喜爱的词句。他从心里真诚地希望有一种高于生活的戏剧,他把一种理性上的满足和他所渴望的真实体验混淆了。”重要的是在舞台上获得“那个能够将作品和观众连接起来的成分——不可抗拒的现场的生命”,使整个剧场“活”起来。这就是“当下的”、“直觉的”戏剧。这种戏剧是稍纵即逝的,它不存在于演出开始之前,随着演出的结束它也即刻消逝了,它仅仅存在于每一次演出进行的每一个瞬间;这种戏剧使整个剧场成为同一个生命的有机整体,演出者和观众共同创造了这一个生命,演出者的使命就是激活观众成为剧场现场生命的另一半。要做到这一点,戏剧的主题必须能够拨动观众的心弦;这个主题必须被鲜明强烈地表现出来;要不断有令人惊奇的舞台手段强化被表现的生活与心情;最后,强大的生命力总是粗俗与神圣的真正贯通——一切生命都具有粗俗的特征,只有思想才可能是纯粹神圣的。
二
徐晓钟教授的导演方法之一,是为每一部作品寻找和确立一个“形象种子”,他说这“是一个演出形象化的思想立意,它是概括思想立意的象征性形象,是生发整个演出的各种具体形象的种子”。他为《培尔·金特》确立的“形象种子”是“一只没有罗盘的破帆船”——“在汹涌的浪涛中颠簸,几经旋转,最后船底朝天,终于被冲上了沙滩……”他为《桑树坪纪事》确立的“形象种子”是“围猎”——桑树坪愚昧的村民们,每一个人都既是围猎者,又是被围猎者。这两部戏的“形象种子”,尤其是《桑》剧的“围猎”,既准确地揭示了戏剧情节和人物描写的内在主题,又为这个主题确立了鲜明而强烈的艺术形象,在激活表演与观众,创造剧场当下生命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这一次,他为浮士德确立的“形象种子”是“漫漫大海的苦行者”——“给我们的人生奋进一些思索!”“漫漫大海”是漫长曲折的人生之意,“苦行”是苦苦追求、探寻目标之意。徐晓钟这一“形象种子”所揭示的主题,实际上是当代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对歌德《浮士德》的一种流行的、普遍的解读,在这里,晓钟教授所作的,只是赋予这个抽象的、观念性的阐释以一个具体的、视觉性的舞台形象。在这部鸿篇巨制中,浮士德由于对学问的怀疑与厌倦,走出书斋,先后经历了爱情、宫廷政治、追求艺术和改造山河等一系列事件。漫漫人生,不倦探索的主题,或可蕴藏于这一系列的事件之中,需要这一系列的事件方能充分表现。但这次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演出,仅演作品第一部,即浮士德厌倦书斋,堕入爱情,直至与爱人生离死别的部分,所有这些在舞台上展开的情节并不足以呈现戏剧主人公在漫漫人生中苦苦探寻的主题。导演所欲表现的这一主题,在演出中,主要是通过浮士德直接抒发对学问的怀疑和对书斋的厌倦之情以及他在爱人死后跋涉于海边,宣告自己已然“苏醒”,懂得了“行动”的意义,要“永远向最高的追求迈进”,如此表白出来的。相反,戏剧的核心情节与高潮,即恋爱和离别,在与作品第二部所描写的种种经历脱离之后,与“漫漫大海的苦行者”形象十分隔膜。观众关注并深有印象的,主要是浮士德堕入性爱的激情和这一激情导致的骇人恶果,而不是他在激情幻灭后的宣言。与葛蕾卿的爱情悲剧是歌德《浮士德》中最能打动情感和最具戏剧性的部分,如果在海边跋涉与沉思的“形象种子”并不适合于这个激情的悲剧故事,那么,这个未被主题照亮的爱情故事只能是司空见惯的、平庸的,自身尚未被激活,更不可能具有激活剧场生命力的能量。
作者明白地告诉我们:《浮士德》是一部悲剧。什么是悲剧呢?在古希腊人看来,一是看上去有价值的人物“由顺境转入了逆境”,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毁灭,由此揭示了人生或人性价值的有限性。人作为一种物质存在,与宇宙间的任何物质一样,都是有限的。二是严肃地描写高贵人物的故事。前者是精神层面上的悲剧性,后者是形式层面上的文体规范。虽然有些古希腊悲剧,例如《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伊翁》,主要是在形式层面上满足了悲剧的文体规范,但是古希腊悲剧的水准却是由《阿伽门农》、《俄狄浦斯王》和《美狄亚》等充分表现了人生和人性价值有限性的最杰出的作品标志着的。在满足精神层面的悲剧性上,源自中世纪民间狂欢的莎士比亚戏剧也与古希腊悲剧殊途同归——19世纪英国学者布拉德雷曾经成功地论证过,莎士比亚悲剧虽然杂糅着严肃与滑稽,在文体风格上与古希腊悲剧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却在表现高贵人物的毁灭性上,从而也在表现人生和人性价值的有限性上,与古希腊悲剧保持了精神上的一致。
相反,刻意模仿古希腊人的17~18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仅仅在严肃地描写高贵人物这一文体形式上学到了古希腊人,而与古希腊人和莎士比亚所感觉到和表现出的精神层面的悲剧性相当隔膜。他们把文体意义上的严肃性当成了高贵人物的严肃性,把宫廷和贵族的严肃意义当成了绝对的、不容怀疑的东西。这样一来,他们的悲剧便蜕化成了宣传他们“永恒”价值观,教化臣民的正剧。新古典主义戏剧的奠基之作和代表作《熙德》最初就被明示为“悲喜剧”(tragi-comédie)。在这里,“悲喜剧”的意思并不是指像莎士比亚戏剧那样严肃风格和滑稽风格的混合,而是指一方面严格保持悲剧文体的严肃风格而另一方面避免了高贵主人公的毁灭,根据“诗的正义”(poetic justice)的宫廷信仰,仍然给他们以幸福的结局。
路易十四时代法国人精神的委顿使他们误把当代宫廷的趣味风尚看成了绝对的、永恒的、不容置疑的东西,他们无法像精神健旺的古希腊人和莎士比亚那样,看穿“人”作为一种物质存在的有限性。迷信宫廷趣味的不朽,使得路易王朝及其治下的臣民们幻想自己已经找到了人生事业与人性中的终极真理,从而能够幸运地避免人生和人性的悲剧性与喜剧性,他们用被阉割了的悲剧内容,即后来被黑格尔称为“没有多大的根本的重要性”的“戏剧体诗的第三个剧种”——“正剧”,替换下古希腊人所迷恋的悲剧性,一面嘲笑海峡对面的莎士比亚不表现人间和人性的正义却热衷于揭示其无常的“不道德”,一面用悲剧文体的严肃风格把自己的王朝在舞台上装扮成神圣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