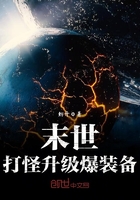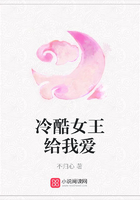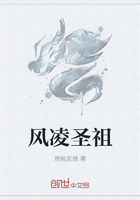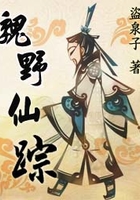尽管存在着这些混乱的情况,阿诺德将军仍然相信首批175架B-29战机将在1944年3月10日前准备投入战斗,并用电报把这条信息发给了在印度的沃尔夫将军。阿诺德按照自己的预期行动,在3月9日抵达萨莱纳目击首次历史性的启程。却被告知没有一架“超级堡垒”准备出发。陆军航空队的指挥官勃然大怒,要求知道谁负责预期的起飞。他大喊道:“我自己来!”
在非正式空军记录中,接下来发生的危机因堪萨斯攻防战而知名。阿诺德转身面向一名高级副官——少校贝内特·E.迈耶斯,告诉他留在萨莱纳现场履行职责,协调处理那里的工作。另外一名将军被派遣到维契托,培训来自于波音公司的另外500名机修工。电话响遍全城,中间商们接到命令把一切其他的工作都推到一边,集中注意力为正在等候的“超级堡垒”机群供应遗失的零部件。一队队的运输机,火车以及卡车开始从四面八方,带着必需的材料到达堪萨斯州。
1944年,在印度克勤格布尔附近的一个为竣工的B-29基地上,劳工们用篮子走泥土。因为当地的承包人是根据发掘的深度付酬劳的,锥形的土堆就留在地里原地不动显示这块土地的原始高度。一旦酬劳确认下来,锥形的土堆就会被移走。
工作忙乱,天气寒冷。堪萨斯平原处在寒冷的严冬中,咆哮的大风雪很快让情况变得更糟。因为没有多少飞机修理库,多数工作不得不在露天的情况下进行,在沿着风力猛烈的航线停靠的飞机上进行。机修工小组,尽管包裹在高等飞行服中,也不得不每20分钟换一次班。
但是,堪萨斯攻防战还是要胜利了。在3月中旬,上校弗兰克·库克驾驶首架做好战斗准备的B-29起飞了,取道迈阿密和纽芬兰岛飞到英国。这次是“超级堡垒”所做的第一次长途迂回的跨洋飞行,行动故意掩盖B-29战机当时打算轰炸日本的事实。库克的假飞取得谨慎的成功;当飞机在英国着陆仅45分钟后,一名德国侦察机飞行员就拍摄了它的照片。但是,日本人是不大可能被迷惑过去的。他们的情报早已报告说印度和中国建有超大规模的机场,显然意味着飞机要比B-17和B-24大些。
大飞机就要来了。在3月26日黎明前的黑夜,堪萨斯机场回响起启动发动机的“呜呜”的声音,很快变成令人震颤的咆哮声。首批阿诺德的“超级堡垒”11架组成的分遣队待命出发。上校杰克·哈曼,该队的指挥官,就坐在领队飞机驾驶室中部左手椅子上。他的行程首先是去纽芬兰岛的甘达尔,然后马不停蹄直奔北非亚特拉斯山脉脚下的马拉喀什,从那里再到开罗。哈曼将横跨近东抵达卡拉奇,最终到加尔各答附近热气腾腾的贾古里——距离冰封的堪萨斯机场11530英里。
重武器解剖
在生产B-29期间甚至还在不断进行修正,使得每一架新的B-29都和上一架有点不同。机尾的标志来自于一架早些时候出产的飞机,外号“威姆匹的闪电伯格”,以该机的驾驶员少校尼尔·威姆匹命名。该机被指派到印度第四十轰炸大队并参加了B-29的首次战斗任务。
“威姆匹的闪电伯格斯”在某些方面不同于B-29同类飞机——比如电线的精确安排——但是,在所有形容B-29飞机的最佳方面就很相似了。翼展长141英尺,空负荷的重量是7.45万磅,B-29是曾被大规模生产的飞机中最大最重的。四台2200高功率发动机,航空学中最强大、世界最大的推进器,每台直径16.5英尺。首架拥有火炮协同的火力控制中心系统,战斗机上的乘员舱第一次压缩。B-29的性能同样巨大。它的最大载弹量达到10吨,比其先辈,“波音B-17”超出四吨;在2.5万英尺海拔高度时最高速度达357英里每小时,要比B-17快55英里每小时,并且其3800英里的航程两倍于其“大姐”。
新兵的基地培训
1944年4月,当首批“超级堡垒”特遣队在印度集合的时候,成员们发现他们的任务被贴切地命名为“马特豪恩峰行动”,出自令人敬畏的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在可以开始执行战斗任务以前,飞行员们有许多障碍要克服。
特遣队指挥官准将肯尼斯·沃尔夫直接领导下的先遣队已经开始工作处理最紧迫的问题了。印度东北方的克勒格布尔附近以前的英国机场被接管过来,成为B-29机群的主要基地,并且先遣队必须为大型机群延长跑道,为队员们建造住宅。同时,B-29机群的前方基地也在美国的监督下即将完成。位于中国中南部的成都附近,那里的飞机起落跑道不得不匆匆地把水稻田填上才建成。
中国给轰炸机提供了可以袭击日本的基地。但是,供给是所有问题中最具威胁性的一个。每架轰炸机,每一个备件,每一加仑的燃料都不得不飞越珠峰送到成都——珠峰是高大的喜马拉雅山脉的一部分,高达2.3万英尺(8848米),分隔印度与中国。无法预测的十分恶劣的天气、可怜的通信条件以及偶尔出现的敌人歼击机,这就使得飞越珠峰是如此危险以至于队员们在运输航路上得到的荣誉相当于参加空战所得。
未经试用过的B-29机群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飞机是新式发动机和许多其他弊病的牺牲品。一架B-29需要在一周之内做出30个大改动。机组成员几乎无法熟悉复杂的新型飞机,不得不抛开神秘的协同防御炮并用雷达引导轰炸。随着时间推移,华盛顿对“马特豪恩峰行动”的抨击也越来越猛烈。“我们只能慢慢地爬,”沃尔夫将军叹道,“而他们要我们做100码的冲刺。”
在一台升举器上,一名印度飞行员在一架B-29的尾翼上喷上了四条带子代表第四十轰炸大队,以标明飞机所属的部队。
克勒格布尔市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不当班的机组成员们无所事事,于是四肢伸开地坐在总部门廊的长椅上。
飞行员们展示着一条七英尺长的巨蟒以及在住宅里杀死的一条巨蜥。
迁入半英亩地狱
美国的轰炸机队员们抵达的时候正是印度最热的季节的开始——这段时间里,灼热的风从西北向印度沙漠吹来,只有到下午下暴雨的时候,令人窒息的沙尘才减轻了一些。一个基地的人们把他们的基地叫做“半英亩地狱”。正午温度达到115℉,严重影响了飞行员和飞机的工作,为此军方不得不限制在拂晓和黄昏时分飞行。
发动机维护在夜晚的灯光下进行,灯光吸引了大批飞虫。更危险的烦恼是眼镜蛇和携带疟疾的蚊子,人们必须睡在帐子里。
然而,到了7月,绝大多数新住宅——麦杆、茅草屋顶的小屋,印度人称作茅顶竹舍已经竣工了。他们已经及时准备做好该地区下个季节——夏天雨季的保护工作。
至关重要的中国跳板
美国在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中国地区建立了四个B-29基地,1944年雨后春笋般地在陈旧的成都大学城周围涌出来实在是令人惊异的成就。
每个基地拥有8500英尺由硬填岩与黏土制成的跑道,所有的这些建设成果是由30万名中国工人在仅仅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用铁铲、手推车以及人力完成的。
在成都基地,生活设施甚至比印度还要少。驻扎在那里或是在供给航路中穿梭的人们被安排住在中国人经营的旅馆里,食用当地食物。任何必须越过珠峰的供给都缺少,成都啤酒配给量是每月两瓶,而在印度时是24瓶。
飞行员们在成都观光,学习当地大步行走的风俗,但有一个悲剧的例外:中国平民会在起落飞机以前快速穿过跑道,在前几个星期里,七名平民死亡。后来的事实证明,许多中国人相信,移动的飞机可以扫去邪恶。后来当跑道上驻扎了守卫兵后,死亡的事情才停止。
成都市场的街上,照片中黄包车和自行车匆匆忙忙地走着,相片是在1944年由一名来访问的美国飞行员拍摄。
试飞磨难
没有几个飞行员在执行战斗任务而不感觉有点紧张的。但是,在印度和中国开展的军事行动在各个方面都让人伤透脑筋。这些远程任务要求有效地训练“超级堡垒”新机组成员,让他们知道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如何操纵飞机和飞机上的设备。组成未经试运行的B-29飞机的五万个零部件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在事先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停止运转,在这期间,飞行还处在试飞阶段。
早期空袭的惟一预期结果就是多数轰炸机都没有成功。第一次的任务——1944年6月初袭击曼谷——98架飞机中的五分之一有严重的机械障碍。飞行员们要么返回,要么在孟加拉湾迫降。还有一些例外的情况,五分之一的失败率在接下来的24项任务中一直让人烦恼。
同样令人烦恼的还有每次空袭后目标的监视相片,只显示出极小的损坏。绝大多数的失败归咎于缺乏经验:在美国空中和地勤人员自信已经掌握了强有力但是难于起动的新型战斗机以前,还需要有六个月的艰苦训练。
总部的巨大损失
起初,B-29是自己最糟糕的敌人,并且最容易在总部或临近总部的地方发生不幸。和其他轰炸机一样,由于装载着爆炸性货物,飞机一直处在危险当中。在印度发生的一次事故中,在数秒钟内,一架胡乱操作的轰炸机在装弹药的时候毁灭了四架B-29。
当每架飞机都要携带8500加仑燃料和2.5吨炸弹的时候,起飞的时候最容易出现问题。为了节约燃料并且避免发动机过热,轰炸机群必须精确计算起飞时间,一架接着一架,没有犹豫或是发生灾祸的余地。时常的飞机间碰撞——和飞行中的故障和着陆时的事故加在一起——造成的死亡要比日本空防造成的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