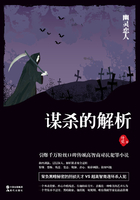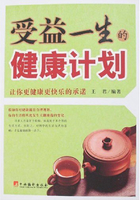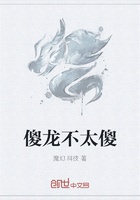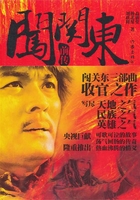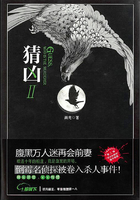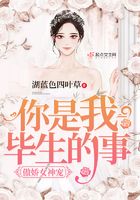父亲困惑地点了点头。
“这么失魂落魄的,我还以为你把它给丢了……”说完,徐护士挽起母亲,头也不回地走了。
父亲面红耳赤地站在那里,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一个星期之后的一天,父亲突然独自造访图云关。
“那天刚吃完晚饭,有人就跑来对我说:‘李玉玺,有一位先生正在院子里找你呢。’我一猜就是你爸,心里一时慌得要命,因为我真的还没想好,应该怎么应付这件事情。可推开宿舍门一看,你爸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站在院子里。那天他穿了一件崭新的白府绸衬衫,一条烫得笔挺的雪白的长裤,戴了一顶亚麻编织的淡黄色的平顶礼帽。他见我出来后,竟然像老熟人一样迎了过来。‘看报了吗?’他扬了扬手里拿着的一张报纸:‘德国飞机越海轰炸伦敦了。’说着,他把报纸递给我:‘晚上还有课吗?’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徐护士长知道你来吗?’我问他。
‘不知道。’他摇了摇头:‘我是专程过来看你的,现配的眼镜,现刮的胡子。’
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确实戴了一副新眼镜,那种当时最流行的金丝镜。你爸摘下眼镜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要不是等这副眼镜,我前几天就来了。’
说话间,他语气突然变得很温暖:‘德亮劝我,不要错过这次和你交往的机会……’
我生怕有人听见我们的谈话,赶紧答应和他出去走走。”
那天黄昏后,父亲和母亲沿着那条绿阴覆盖的山路,一直走到熄灯号响。一路上,二十多座苍劲浑古的石牌坊,在月光的辉映下,见证了他们的第一次约会。
一个半月之后,当父亲重新回到重庆时,刚从上海返渝的徐维廉发现,在父亲身上,已少了些少年的意气与张狂,多了些成年人的镇定与责任。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失陷之后,国民政府的核心机关曾一度撤到武汉。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中央政府不得不再迁“陪都”重庆,而湖北省直机关也从武汉迁至鄂西恩施。
恩施位于长江巫峡之南的崇山峻岭之间,为鄂西通往川湘两省的要冲。一九四〇年六月宜昌失守之后,为确保峡江防线及重庆的安全,蒋介石重新组建第六战区,遂派心腹陈诚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其指挥中心即在恩施。
陈诚是国民政府中一位力求务实的军政官员,在其任内,他不仅有效地节制了第三、四、九战区,以确保重庆安全,同时,积极促进恩施及鄂西地区的地方建设。尤其重点利用武汉撤往恩施的学生资源,于西南各地网罗师资大兴教育。这不仅解决了大批流亡学生的升学就业问题,更为恩施乃至湖北培养和储备了大量人才。而为陈诚具体操办这件事的便是张伯谨先生。
张伯谨,名吉堂,河北行唐人。早年就学于燕京大学教育学系,之后在美国加州大学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央政治委员会教育专门委员,国防最高委员会教育专门委员,湖北省教育厅厅长。
张伯谨到任后,先后在恩施创办了包括湖北省教育学院、湖北农学院、湖北省立医学院及湖北省立工学院在内的多所高等学府。同时,有计划地将从武汉撤下的三十多所省立中等教育学校,分别安排在施鹤八县。一时间,以恩施为中心的鄂西群山之中,大中小学星罗棋布,学者名流云集,其盛况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堪称奇迹。
一九四〇年九月,在从贵阳返回重庆的当天晚上,徐维廉就安排父亲与张伯谨见面了。为加强湖北省教育厅的组织领导力量,张伯谨一直住在重庆,多方奔走,发现和物色各方人才。此次与父亲会面,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谈到兴奋之处,连一向苟于言谈的徐维廉都为之动容:“伯谨兄所做的努力,于湖北乃至全国都是一件功不可没的好事情。子清当应随之前往,以助张厅长一臂之力。”
张伯谨是一个说话很随和的人:“子清的情况,徐校长已和我谈过,很好。当然脾气也要改一改,不要因一些琐事耽误前程。好在你我徐校长都是河北老乡,所以今后更要互相担待,共赴宦海。”
听到“宦海”一词,父亲又有些沉不住气了:“厅长,我去湖北只想教书育人,千万不要安排学生做教书之外的事情。一年多来,我深知自己的优劣长短,仕宦之途于我来说实在寸步难行。望张厅长见谅。”
张伯谨听罢大笑:“维廉兄,看来子清的确让官场上的三老四少给吓坏了。只‘宦海’二字,就让他联想到了惊涛骇浪。哈哈哈……”
谈话期间,父亲向两位前辈谈到了此去贵阳与母亲相恋之事,张伯谨甚是高兴,当即答应母亲去恩施后的工作由他负责安排。父亲听罢,深表谢意。分手时,徐维廉握住张伯谨的手感慨万分:“子清一向忠诚笃实,办事执著认真。无奈随我多年却难有建树,如此下去,我实在担心误其前程。今晚见伯谨兄亲和豁达,湖北之事又轰轰烈烈,子清从此就跟你去了,望伯谨兄相机鞭策,鼎力提携。”
张伯谨爽然大笑:“放心,放心……”
在回家的路上,徐维廉怅然地对父亲说:“鄂西一带,冬天时有冻雪,还需多带些衣被,以备御寒。”父亲默然。
几天之后,父亲与新近招聘的封子虞、高其冰、李维新等人,与张伯谨一道登上了东去的江轮……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初到恩施的父亲与高其冰一起,被任命为湖北省教育厅督学。不久,教育厅通知父亲去省政府参加一个公教人员训导会议,会期三天。
在公教人员训导会议期间,省主席陈诚作了主旨发言。他谈到了地方干部的培养和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建设问题。其间,他再三强调:“政府公教人员说到底就是民众的公仆,民众养活了你,你就要率先垂范,事事想在民众的前面,做在民众的前面,走在民众的前面。”谈到这里,陈诚突然提高语调,郑重地向参加训导会的全体公教人员宣布:“从今天起,在座的省直机关公教人员,皆为我党党员,我就是诸位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入党介绍人。”大家全体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
抗战期间,国民党为扩大组织笼络人心,常用这种所谓集体入党的形式,突击发展党员。其间既不考虑被发展对象的实际政治信仰,也不考量对方的德才水平,致使党员成分鱼龙混杂,完全失去了作为一个执政党所必须遵守的最高原则。
但从此父亲的档案里就有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其“政治面貌”一栏不再是空白。一个更加严重的现实,让后来许多查阅过父亲档案的人面对“陈诚”二字,瞠目结舌。也让父亲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即便浑身是嘴,也很难说清个中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
一九四一年四月,母亲在徐美丽的陪同下,搭乘救护总队重庆运输站运送药械的卡车,从贵阳抵达重庆。不久,父母便结婚了。从当时留下的照片上看,父亲那天穿了一套黑色的中山装,而母亲穿的那一件洒满白色芍药花的玫红色的短袖旗袍,一直保存到一九六六年深秋。当然,那件旗袍也好,那张婚礼照片也好,后来都注定被红卫兵毁掉了。这一切只能深藏在记忆中:照片上父母沉静的目光,旗袍上那淡淡的樟脑气息……
徐美丽抗战胜利后,一直在昌黎汇文中学工作。一九七六年在唐山大地震中不幸罹难,终年七十七岁。
一九四一年四月末的一天,雨雾迷蒙。在重庆朝天门码头,徐维廉夫妇、徐美丽、祁子晋、孙德亮等几位挚友打着雨伞,送新婚不久的父母登上东去的江船。同船前往湖北的,除了亲自来渝为父母证婚的张伯谨之外,还有刚从成都金陵大学招聘过来的留美农学博士管泽良及夫人歌唱家喻宜萱,以及喻宜萱的好友作曲家江定仙先生。
“在船上,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母亲后来回忆说:“因为你爸一向关注乡村建设问题,而管先生又是一位很有思想的农业专家,我和喻宜萱、江定仙更有说不完的音乐话题,所以大家一见如故,无话不谈。”
江船驶过神女峰时,已是第二天的黄昏。母亲站在船尾,望着渐渐远去的一川烟雨,四年来颠沛流离的疲惫,像雾一样慢慢地消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