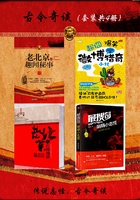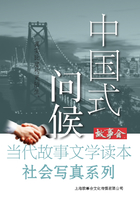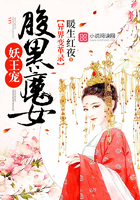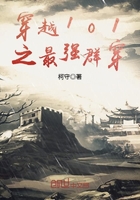退休前两年即二〇〇三年十一月,我曾去成都参加了第七届四川国际电视节。会期结束后,便独自一人,乘长途汽车沿成渝高速公路一路南下了。
这是我期待已久的一次旅程。时值中秋,车窗外高大的桉树,碧绿的芭蕉,果实累累的橘林和刚刚收获的红苕,似一幅展不尽的长轴画卷,将我引向我的出生地——重庆。
在人声喧嚣的重庆长途客运站的站前广场,当出租司机问我去哪里时,我试探着问:“有一个叫牛角沱的地方吗?”
“有的,离上清寺不远嘛。”说话间,他已将汽车开进这座迷宫般的山城里。
我真没想到重庆如此恢宏。虽然其间还依稀能找到母亲曾经讲述过的黑瓦灰墙的老街,但从山谷间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早已填平了山城的条条沟壑。纵横交错的高架桥、快轨电车与无数跨越两江的索道桥梁,将这座西南著名的通衢大邑,紧密编织在长江与嘉陵江之间这片富饶的大地上,雄浑而厚重。
入夜,雷鸣电闪伴着滂沱大雨,将山城沉浸在一团诡异的昏暗里。宾馆的走廊上,传来服务员之间不安的对话:“这天气是怎么搞的嘛,都立冬了,还有这样大的雷雨。”
我一个人默默地站在窗前,望着雨幕中嘉陵江对岸依稀的灯火,不禁潸然。因为我心里知道,是父母在天之灵知我寻到这里,知我依旧如此刻骨铭心地思念着他们。
一九四三年三月底的一个黄昏,当父亲带着全家人从恩施回到重庆时,正赶上徐维廉当晚要为从桂林远道而来的杨扶青接风洗尘,所以舟车劳顿数日的一家人,稍稍喘了口气,便随徐校长去了位于沙坪坝的一家饭店。
“狼狈极了。”母亲后来回忆说:“一家四口儿蓬头垢面的,和逃难的流民差不多。徐校长刚把你姐抱过去,你姐就尿了校长一裤子,弄得老爷子哭笑不得。”
这是嘉陵江边一家较大的饭店。在饭店门口,父亲见到了分别四年的老友张师贤和他的夫人、美丽却面容憔悴的邓辰一。
燕大毕业后,张师贤即赴浙江省财政厅就职,并在那里与湖南湘乡女子邓辰一结为伉俪。随着战事迫近,不久,张师贤便携夫人退到桂林,在市政府农本局工作。其间,与正在桂林创办中华营造厂的杨扶青频繁接触。此次即随扶老一起调重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作。
抗战爆发后,杨扶青即投身大后方,为抗日救亡在西南一带奔波操劳。一九三八年,扶老与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及埃德加·斯诺夫妇结识,开始致力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工作。工业合作社运动,是一个指导和组织失业工人及难民生产自救而兴起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曾为抗日救亡作出过重大贡献。日前,杨扶青应召从桂林来到重庆,出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副总干事,同时负责该协会下属培黎学校的校务工作。
席间,杨扶青对即将就任的培黎学校寄予很大的希望。
“职业教育!”杨扶青精神矍铄地望着徐维廉:“和当初咱们在昌黎汇文所设想的教学方向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那就是通过职业教育,让无业者有业,让有业者乐业。也就是说,职业教育不光教人以职业技能,还要教人以职业精神。”
杨扶青即将就任的培黎学校,是一所颇具规模的职业教育学校,学校附设机器厂、毛纺厂、造纸厂、瓷器厂、皮革厂等教学工厂。新中国成立后,培黎学校培养的专业技术工人,大多成为西南及东北地区一些重要企业的工程技术骨干。
徐维廉始终坐在那里倾听。父亲知道,校长此刻的心情很复杂。
南下以来,徐维廉一直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但实因性格刚直孤傲,且不懂政治,几年下来,难成大业。而杨扶青却不同,扶老为人谦和刚柔相济,又能融会贯通广交朋友。抗战期间,他不仅善于与国民政府的大小官员上下周旋,又不畏与包括周恩来、董必武在内的中共高层广泛接触。在他的身边,不仅团结了像黄炎培、李公朴、闻一多等一大批致力抗战的民主人士,还与许多国际友人保持密切的交往。除此之外,在资金上,杨扶青有自己较雄厚的资本储备。这比起两袖清风动辄需求外援的徐维廉来说,要踏实得多,也自主得多。
祁子晋拿着一本新出版的《残不废》杂志匆匆赶来。他见过父亲母亲之后,便低声请徐校长到走廊里议事去了。
稍后,徐校长回到房间向大家解释:“云山去社会局了,杂志出了点问题,让人家揪辫子了。”
杨扶青撇了撇嘴:“那些混账东西,成天无事生非制造摩擦,照此下去,早晚有一天得让人家掫下台。”
父亲第一次听扶老谈及政治,父亲很清楚,这里的“人家”指的就是共产党。
草草吃了几口饭之后,母亲一直抱着姐姐,与子洵叔叔坐在房间的角落里。姐姐动辄哭闹,让母亲感到很尴尬。
“来,仰山伯伯抱抱。”张师贤回过身去大声地说。
“不行,这孩子谁也不跟。”母亲赶忙笑着谢绝了。
张师贤站起身来迎了过去:“丫头不哭,让仰山伯伯抱抱。”说着便从母亲怀里接过姐姐,姐姐竟然不哭了。她睁着一双大眼睛,惊奇地望着眼前这张通红的大脸,小手轻轻扬起,抓住了仰山伯伯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大家都笑了。
张师贤抱着姐姐在屋子里踱了几步:“不好意思。流离四年,烽烟万里。今与素心兄重逢陪都,即席口占一首七律,大家见笑了。”
夜幕四合的嘉陵江上,传来悠长的汽笛声。张师贤沉思片刻,便朗声脱口成诗一首:
襥被分程出故京,相期不负寸心盟。
四年我已成皮骨,一笑君还旧性情。
乍睹娇娃惊玉雪,却从阿母识聪明。
山城今夜闻春鸟,无复嘤鸣求友声。
“好!”众人一片赞许。姐姐在仰山伯伯的怀里竟然睡着了。
当晚离席的时候,张师贤、邓辰一便邀父母到他家寄住:“挤一挤热闹嘛。”张师贤拍着叔叔的肩膀:“这叫共赴国难,懂吗?”
叔叔点了点头。
七年之后,叔叔娶了张师贤的胞妹张淑云,但唐张两家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
一九四三年,随着国民政府及华东地区工业企业的西迁,重庆的城市人口已暴增了四倍。随着清晨的到来,两江夹峙的这座山城,每天都沉浸在一片雷鸣般的喧嚣中。其中最为壮观的一道风景,便是成千上万由挑夫组成的苦力队伍。
重庆挑夫由来已久。由于地处群山之中,街道跌宕错落,靠一根竹棒两条麻绳帮人挑抬重物的营生日渐红火。这些被当地人称作“棒棒”的苦力,大多来自四川乡下。他们头缠一条白布,身着一件蓝衫,三五成群流散在码头、车站、市场及高高的台阶下,如乞丐一样追逐行人讨要生意。每每目睹其状,父母无不为之悲悯。
六十年过去了。今天,当我走出宾馆时,仍惊讶地看到,为数众多的“棒棒军”依旧活跃在山城的市井坊间。宾馆服务生告诉我,“棒棒”不仅吃苦耐劳,更诚实可靠,无论客人托付什么东西,只要交给他们,价钱再低也绝对放心,极少发生物品损坏和丢失的事情。
从宾馆门前,我搭了一辆出租车去董家溪。
出租司机问我:“去董家溪哪里?”
我张了张嘴:“先走吧,到那里再说。”
出租司机困惑地望了我一眼:“是第一回来重庆吧?”
我点了点头。
出租车风驰电掣地驶过嘉陵江大桥后不久,司机便说:“这一片就是董家溪了,你还要往哪里走?”
我迟疑了。眼前的董家溪已失去了我想象中的所有痕迹:一人多高的拔茅草,一片盘根错节的苦竹林,狭窄的台阶,几间破旧的茅草房。一切早已不复存在了。
但既然那片荒芜的土地归了保育院,如今,便仍有继续归属教育单位使用的可能。
“董家溪有学校吗?”我问。
“有,渝州大学嘛。”司机脱口而出。
“去渝州大学。”我从来相信自己的判断。
那是一个星期天。学校的大门口停着几辆大巴士,一些教职员工正在蹬车,看样子是准备去郊游。
“劳驾,打听一下,渝州大学的前身是不是与一个战时保育院有关系?”尽管我找了一位当中最年长的教师,但我心里很清楚,他也不可能知道那些遥远的往事。
我开始失望了,我真希望父亲此刻能从校园的一个角落里探出身来:“傻小子,我在这儿呢。”
走出校门后,我慢慢沿着高高的院墙向北走去。深秋的阳光洒在肩上,让人感到一阵温暖。忽然,在道路的右侧,我看到了母亲曾经说过的那条狭窄的磨得发亮的青石台阶,我看到了台阶两侧护拥着黑瓦灰墙的陈旧建筑,我看到了一群坐在树阴下摆龙门阵的老人们。
“保育院?就在渝州大学里嘛。”一位干瘦的老人将手一挥:“你可晓得,那保育院可是中央直属第十一分院哩。”
我问那老人高寿了,老人将食指一弯:“九十了。哈哈哈!”
一九四三年春末,经徐维廉推荐,应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之聘,从恩施返回重庆的父亲,在嘉陵江北岸的一片拔茅草丛里,开始营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总会直属第十一保育院。那一年,父亲三十三岁。
抗战爆发以来,中国人民遭受了几千年来最为惨烈的种族屠戮。仅据一九三八年六月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公布的一项统计表明,开战一年以来,日军对中国十六个省二百五十七座城市,实施了两千四百七十二次狂轰滥炸。而随之发生的南京屠城、黄河决堤、长沙大火等震惊中外的战争悲剧,更让中华民族付出了空前惨痛的代价。一九三八年九月,《大公报》惊呼:“中国七千万儿童在十个月内被日寇直接杀害的在十万人以上,被掳掠的达十五万人以上,流离失所的在四十万人以上。”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对此曾做过估计,他说在全国,需要保育的儿童竟达两千万人以上!拯救难童成了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急需解决的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经过三个多月的酝酿筹备,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在武汉正式诞生了。在庆祝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典礼上,宋美龄发表了“谨为难童请命”的演说。不久,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女士更明确地指出:“我们已发现了一座桥梁,可以沟通环境、种族、宗教和政党之间的分歧,这座桥梁就是儿童——我们的儿童。”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后,一批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杰出女性,便在保育委员会主任曹孟君的带领下,深入炮火连天的台儿庄战区,展开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救孤行动。不久,由保育委员会副主任唐国桢和宣传委员会委员徐镜平率领的另一支前线抢救队,也深入豫北战区搜救难童。随着战事的推进,在继续于战区抢救难童的同时,保育总会又指挥几万名无家可归的孩子,开始了举世无双的难童大迁徙。同时,相继在重庆及川桂湘粤黔赣浙闽香港及陕甘宁边区,建立了长期收容难童的保育院。其中直属第十一保育分院就坐落在今天渝州大学的校园里。
再次走进渝州大学时,我的心情已经与方才截然不同了。穿过宽阔的校区,在一座题为“史迪威图书馆”幽静的后院里,我靠近一个石桌坐了下来。
周围一片浓绿,唯石墙上攀附的一种叫不出名的藤蔓已略显金黄。三三两两的学子,坐在阳光或树阴下安静地读书,无数秋虫组成的和声,让人听起来如此缠绵。我长久地坐在那里,仿佛在等待着与什么人会面。
许久,一个操着西北口音的小伙子,很有礼貌地凑了过来:“老先生,您是在这里等什么人吧?”他望着我,眼睛里充满了好奇。
“不。”我摇了摇头:“我是沿着前辈的足迹寻到这里来的,我只想在这里歇一歇。”
直到这时,我才豁然意识到,水绕山环不远万里,我今天终于来到这里的目的,其实只是为了坐下歇一歇。
之后,我和那小伙子谈到了这里曾经创办的战时儿童保育院,谈到了直属第十一分院的院长唐子清先生。
“我能和您照一张相吗?”那小伙子显然被我刚才讲的故事感染了:“还有,还有我的女朋友。”他指了指一直坐在邻桌聆听我们谈话的女孩子。我微笑着点了点头,思绪却早已行走在六十年前这片紫褐色的土地上了。
一九四三年暮春的一天,父亲与战时儿童保育会总会研训科科长田贵銮女士一起,从临江门码头乘木船北渡嘉陵江,在刘家台渡口登岸后不久,便听到从一片没人高的拔茅草后,传来了孩子们的歌声。
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
我们失掉了土地,我们失掉了老家,
我们的大敌人
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阀。
我们要打倒它!要打倒它!
打倒它!才可以回老家。
打倒它!才可以看见爸爸妈妈。
打倒它!才可以建立新中华!
循着歌声,父亲随田贵銮女士一起,走进了第十一分院简陋的校园。
一九四二年,保育总会将所属保育院男女保育生分院之后,直十一分院定为男童院,同时总会计划将重庆地区各保育院中的大龄男孩集中在这里,一则便于管理,二则着意探索大龄保育生的出路问题。
当父亲面对一张张尚未成熟的男孩子们的脸,问他们长大后打算做什么的时候,男孩子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喊道:“当兵去!打鬼子!”父亲心里顿时一热。
田贵銮女士走后,父亲的思绪开始飞快地跃动起来。他想到了徐维廉对昌黎汇文中学的教改设想,想到了晏阳初的平教会在定县实验区的成功实践,想到了管泽良生机勃勃的湖北农学院,想到了杨扶青目前正致力探索的培黎学校的办学道路。一个崭新的直十一分院的教改办学方向,逐渐明晰地呈现在父亲面前。他一连几天与部分教员及保育生交谈,并逐步完善了自己的设想。
一个多月之后,保育总会总干事长熊芷女士,在她的办公室里接见了父亲。
“你就是直十一分院的唐子清?”熊芷面无表情地问父亲。
“是。”父亲感到有些森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