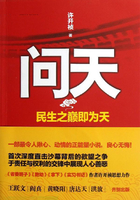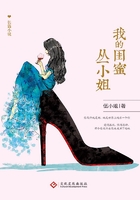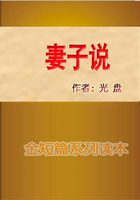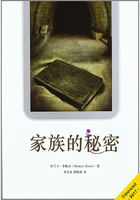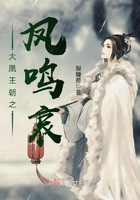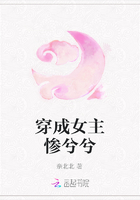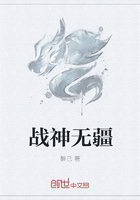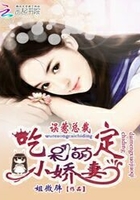尽管当时内战的硝烟已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华北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救济物资,仍坚持不分政治地域、一视同仁的发放原则。但令父亲困惑不解的是,所有计划向解放区运送的救济物资(主要是小麦),均被当地民主政府拒绝。联想到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八日,解放军冀东军区独立第十旅首次攻打昌黎时,从火车站及城内缴获走成堆的粮食和战略物资,而为配合那次昌黎战役,冀东各县六千多名武装起来的老百姓,将北宁铁路山海关至滦县段一夜之间掀翻多处。这一切让父亲开始感悟到了共产党的尊严与自信,因为它有能力凭借人民的力量,夺取它所需要的一切,它不需要施舍。
那年五月中旬,恰逢汇文中学老校友云集昌黎,参加母校校庆活动。这是抗战八年后老同学的首聚,所以父亲带母亲、姐姐与我一起去了。
我那时才两岁,对于昌黎之役,却留下些许挥之不掉的记忆。一个是凌晨战斗打响之后,母亲抱着我和许多校友及眷属,躲在汇文中学的一处半地下室里,盯着缠着绑腿的持枪战士,顺着我们藏身的窗前悄无声息地跃进潜行。再一个就是天亮后,人们发现学校附近一间平房的山墙,被染成一片刺眼的猩红。几个青年学生爬上房后大声喊道:“房上死了两个当兵的,还有一挺机关枪!”
时疏时密的枪声,令人窒息的地下室,草黄色的绑腿,一条条疾行拖带的步枪,凝结在山墙上的鲜血,成了我一生当中最初的记忆。
江擦胡同二十九号,是昌黎汇文中学及燕京大学老校友常来聚会的地方。其中抗战期间南下的患难弟兄,更常在这里回忆颠沛流离的战争岁月。记得父亲在院子的一个喷水池里,用太湖石修了一座假山,在靠近水面的一片石阶上,安放了几个陶制的小房子。父亲曾深情地对来访客人说:“这就是董家溪,这就是我的励新建设学园。”
抗战胜利后,仰山伯伯被国民政府委任到南京中央设计院工作。这期间,他去了湖南湘乡,拜见了从未谋面的岳父岳母。而正是这次省亲,辰一阿姨的妹妹珍一阿姨,便很快被这位风流倜傥注重情义的姐夫所吸引。不久,仰山伯伯再次与邓家女儿喜结良缘,一时在朋友之中传为佳话。
一九四七年初,仰山伯伯辞去南京的工作,在天津创办了自己的报纸《新星报》。这份自由主义立场的报纸一经出版,其发行量便很快达到四万份,对天津国民党的官方报纸《天津日报》及《益世报》,形成了很大的挑战。
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在驶往美国纽约的邮轮上,三舅妈杨英贞坐在阳光明媚的舷窗前,从皮包里掏出前不久一家三口在王府井中国照相馆留下的那张合影。一年来,经卫生署反复遴选,三舅妈终以优异成绩,获联合国卫生组织颁发的助学金,并促成此次赴美国克利夫兰大学进修公共卫生学及护理教育学的机会。
邮轮在浩瀚的印度洋上破浪西行,站在甲板上,一位美国绅士与三舅妈谈起了中国的前途。
“那里发生的一切,都是不正常的,是违反上帝意愿的。中国和平的最大障碍,在于国共两党相互压倒对方的心理。”那位绅士耸了耸肩:“而国民党的强力集团,又笃信武力结束共产党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办法。更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政府的巨额援助,使他们变得有恃无恐。”说着,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的脑袋生病了。”
当邮船驶进纽约湾,自由女神雕像从船舷一侧掠过的时候,那位年老的美国绅士握住三舅妈的手,热情地说:“Welcome to America!(美国欢迎你!)”
在徐维廉的全力推动下,一九四七年五月,由华北国际救济委员会拨款支持的滦榆区地方建设协进会,终于在昌黎成立了。徐维廉任驻会常务理事,父亲任总干事,驻北平负责向教会方面争取款物。
滦榆区地方建设协进会是徐维廉乡村建设思想的再一次实践。协进会以昌黎汇文中学为基地,以东起山海关(即榆关),西至滦县的冀东五县为实验区,试行农业机械培训,农作物新品种推广,贷款凿井扩大水浇地及妇孺保健工作。以“寓建设于救济”的办会宗旨,促进乡村社会的改良进程。
但随着解放区的迅猛扩大,及至是年年底,一场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如暴风骤雨般横扫冀东干涸的大地,成立仅半年的滦榆区地方建设协进会的所有努力,顷刻之间灰飞烟灭。
庄稼人对一些特殊的年份,有他们自己的纪年方法。他们把一九四七年称作是“耍大缸那年”、把一九四八年称作是“大上台那年”。因为一九四七年九月,共产党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庄稼人取的是“法大纲”的谐音,而“大上台”则指新解放区的扩军运动。
对于父亲来说,土地改革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从他在燕京大学主修乡村建设这一课题时起,“土地改革”一词就时常见诸学者教授的讲堂上。自先总理孙中山提出“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建国方略之后,多少年来,无数华夏有识之士,无不关注土地所有制问题。因为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土地即意味着民众的生存与国家的发展。
然而,真正面对由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时,父亲的心情是复杂的。
一九四七年底,三爷的儿子唐子藩与另一位父亲的远房族弟唐子舜,到北平跑单帮,期间找到了江擦胡同二十九号。交谈中,父亲得知,爷爷已在故乡的土改运动中,被划为富农,成为共产党的斗争对象。一直赖在家里的朱氏,与村中五六个地主富农家的年轻寡妇或尚未出嫁的老闺女,在土改斗争中被分配给贫雇农家做了媳妇,富裕中农被扩大成斗争对象,个别有民愤的地主分子,被贫农团活活打死,等等。
毛泽东曾告诫人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父亲却从感情上接受不了这种“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他请唐子舜将唐庄土改过程中的过激行为整理出来,寄给了仰山伯伯,希望见报予以批评。
不久,仰山伯伯将这纸材料退回了。在回信中,仰山伯伯劝父亲冷静,同时提醒父亲,切莫因一时感情用事而激化了唐庄的家族之争。
这件事情虽然到此为止了,但全国解放后,父亲还是在面对组织的反省中,主动交代了自己对土改的错误认识。但在父亲被定性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依据中,“……1947年,唐指示其族弟唐子舜搜集农村土改情况,企图登报等问题属实……”成为又一铁证。
江擦胡同二十九号的门楼中央,有两扇沉重的大红门。一尺多高的厚门槛,需两个壮汉合力方能卸下。而一旦有人去卸门槛了,我便会兴奋地站在那里,望着父亲驾驶一辆吉普车缓缓开出大门。
门外的世界对我来说是新奇而险恶的。保姆张妈曾不止一次警告过我:“别出去啊!街上有拍花子的!”据大人们说,拍花子的都是些白胡子老头,只要他在小孩头上拍上一掌,那小孩就会像傻子一样跟着他走,直到被卖给练杂耍的乡下人。
尽管如此,当春天来到古城的时候,大红门外也确实充满了生机。卖小金鱼儿的,卖芍药花的,卖蛤蟆骨朵儿的,那一声声悠长婉转的叫卖,实在让人难以无动于衷。
北京人管小蝌蚪叫蛤蟆骨朵儿,解放前,由于缺乏卫生常识,一些人误认为让小孩吞下活蝌蚪可以败火。故年年开春,胡同里常有些乡下人,挑着两只大木盆沿街叫卖,木盆的清水里,黑压压挤满了欢快的蛤蟆骨朵儿。
我那时很愿意用“然后”这个词。
“张妈,那蛤蟆骨朵儿喝到肚子里,然后再到哪儿去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哪儿也不去了。然后就变成一群小蛤蟆呆在肚子里了。”张妈认真地告诉我,同样也用了“然后”这个词。
我觉得很可怕,我发誓绝不喝蛤蟆骨朵儿。
一九四八年早春,当北平遭遇第一场浮尘天气的时候,东单大地东北角的空地上,每天拥挤着成百上千投机金融黑市的人们。
“买了卖了!卖了买了!”
“买了卖了!卖了买了!”
叫卖声与手中掂响的银元像群蝇一样在耳畔鼓噪,市民的口粮随之实行配给了。紧接着,米价带动所有物价如脱缰野马一日几涨。去买粮食的张木匠,常沮丧地对母亲抱怨:“唐太太,还是您亲自到粮店去看看吧,这粮价涨得连撒谎都跟不上了。”
一天,姥姥到江擦胡同二十九号来串门,没想到一进大门,老太太就在院子里喊:“完喽,完喽!老蒋这条大船,眼瞅着就要沉底喽。”
原来姥姥从东四五条坐洋车到江擦胡同后,拉洋车要的车费比往日竟多出好几倍。姥姥不干了:“干嘛呀?大清早上的,要砸杠子呀?”
不想那拉洋车的直作揖:“老太太,眼下我累死干一天,也挣不出二斤杂合面来,一家子七八张嘴,全靠我卖点力气养活着呢。”
“真活不下去了。”姥姥断言:“照这么下去,不出半年,这世道不变才怪呢!”
姥姥真是个活神仙。说这句话的时候,辽沈战役还没开打呢,可十个月之后,北平便和平解放了。
中秋节那一天,仰山伯伯约父亲和祁伯伯到什刹海喝莲子粥,姐姐和我都去了。那天晚上月朗风清,什刹海周边赏月的市民人头攒动,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荷叶与莲子的清香。人们忘却了世间的纷扰,远处甚至传来一阵西皮流水的琴声。
突然,湖边所有的路灯都暗了,周围的人们顿时紧张起来。黑暗中不知谁低声喊道:“戒严了!宪兵又要抓人了!”只见一排排戴着钢盔的军警,从湖边的西侧向这里涌来。父亲一把将我抱起来:“快走!”
仰山伯伯则不忘戏谑地对珍一阿姨说:“嗨,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待在家里,数我那些金圆券了。”
一九四八年,在杨扶青的提携下,仰山伯伯被增补为国民政府的国大代表。不久便有传言,说国府打算委仰山伯伯出任黑龙江省省长,只因黑龙江地界一直被共产党所占,所以任命迟迟未能下达。
十二月初的一个下午,徐维廉到江擦胡同二十九号,与父亲商讨有关华北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事情。天黑后,大家在一起共进晚餐。江擦胡同二十九号的餐厅,在二楼西侧一个很讲究的大房间里。因为厨房在地下室,厨师要将做好的饭菜放在一个托盘上,之后用力摇一个手柄,四根绳索便顺着一个直上直下的通道,将托盘平稳地升到二楼餐厅的窗口前。
每逢徐维廉在这里用餐,都坐在长餐桌的主位。那天因为停电,餐桌上点燃了三支蜡烛。大家分别落座后,母亲照例开始做饭前祷告。
“感谢上帝赐我一餐……”
蓦然,从远处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我扔掉筷子蹭地一下扑到母亲的怀里。大人们纷纷站了起来,徐维廉与父亲走到窗前向外望去,只见西南漆黑的夜空中,飘浮着一团暗红色的云翳。
“南苑飞机场。”徐维廉镇定地说:“看来共产党要断傅作义的后路了。”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叔叔从天津回来了。一进院子他就大声喊:“快去看呐,东单大地落了好几架大飞机!”说着,他就招呼着把姐姐、小和尚和我找到一起:“走,跟叔叔看大飞机去。”
叔叔潞河中学高中毕业后,仰山伯伯就让他进了《新星报》社。两年来一直常驻天津,平日很少回来。
从江擦胡同到东单大地并不远,出了苏州胡同西口,迎面便看见两架深灰色的军用飞机,正停落在荒凉的东单大地上。这里说的东单大地,原来就是东单路口西南方向一片开阔的荒地。它北起东长安街,南至同仁医院,东临崇文门大街,西傍大华街。多年来,这里除经常堆积些城市垃圾外,一直无人问津,成了北平东城浮尘天气的策源地。
南苑机场被解放军占领后,为维持空中运输这条生命线,傅作义竟将这里临时辟做简易机场,一时间引擎轰鸣黄沙四起。凡从一旁经过的路人,无不摇头替当局绝望。
十二月下旬,在十分平静的一场大规模的军事部署之后,北平终于被包围了。母亲和张妈、侯婶连夜将江擦胡同二十九号小楼上下所有的门窗玻璃都贴上米字形的纸条,以防炮轰时碎玻璃伤人。
“轰炸时,无论趴在哪里,都不要把胸口紧贴在地上,因为炸弹爆炸时,大地震荡得很厉害,容易把内脏震坏了。”母亲不时向女人们传授抗战时所总结出来的经验。
围城后不久,二舅和二舅妈就赶到江擦胡同二十九号,他们诚恳地希望母亲带孩子们到马匹厂去住。
“听说共产党的大炮,把城里的很多目标都算好了,你们这儿属美国教会的房产,万一打起来,一颗炮弹就轰平了。”二舅不无担心地说。
“放心吧,二哥。”母亲平静地说:“没听说吗?傅作义一直在跟共产党谈着呢。素心说了,既然他肯谈,他就不敢再打了,剩下的就是讨价还价了。”
二舅和新二舅妈是一九四六年结婚的。眼下他们又有了一个女儿,叫望霞。
圣诞节到来的时候,一九四八年冬的第一场雪,静静覆盖了这座帝国古都。自从回到北平后,母亲每逢周日必到后沟胡同的亚斯立堂去做礼拜,两年来风雨无阻。
四十八年前,为免遭义和团的捕杀,姥爷曾带全家人在这座教堂里避难。而兵临城下的今天,当全家人走进教会大门的时候,整个教堂内外已被虔诚的教徒挤得水泄不通。听不清牧师的布道,但每个人的心里都在默默地祈祷,为了自己和挚爱亲人的生存,为了这座历史辉煌的文化古城。
由于东单大地飞机起降的能力有限,这一年年底,傅作义命他的守城部队,将天坛公园内的四百多棵珍惜古柏伐掉,又修了一个简易机场。一时间,北平城内一些党国官员、富商及其眷属纷纷拥向机场,希望抢在城破之前逃离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