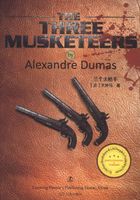十一月八日,美国战机分六批五十架次侵入浙江南部海域。十一月十一日,福建公安部门破获九起美蒋特务案,二十四人被判死刑、无期或有期徒刑。十一月十四日,解放军海军在浙江以东海面,击沉台湾太平号驱逐舰。十一月十八日及以后两天,解放军空军先后轮番轰炸了盘踞在披山岛、渔山列岛的国军阵地。一时间,台湾海峡波高浪急,全国军民同仇敌忾。而恰在这个月,我表演了一出万分荒唐的恶作剧。
十一月四日做完作业后,我又开始百无聊赖了。那是一个阴暗的星期四的下午,后天周六,父亲又答应带我们去海员俱乐部了。上次在那里看了苏联电影《母亲》,那是一部根据高尔基的同名小说改编的黑白故事片。我突然想起,母亲尼洛夫娜在圣彼得堡街头的群众集会上,散发革命传单时慷慨激昂的演讲。于是,我开始激动起来,我尽量模仿尼洛夫娜的语调,大声朗诵起电影里的精彩台词来。
“……我的儿子的话,是工人阶级的纯洁的话,是不能收买的灵魂所说出的话,你们可以看到,他的勇气是不能被收买的!”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豪情的激励下,我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了,写传单,对,写传单!我随手找来两张小纸条,开始用“金不换”慢慢在砚台里研起墨来。
“写什么呢?”我在认真地拿捏着,写“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这哪儿有一点尼洛夫娜的造反气派。那么……
墨研好了,很快,两张不大的纸片上,写满了字迹幼稚,内容却十分“反动”的文字,落款都是“国民党大官宣”。
我走到窗前向下看,大街上秋风萧瑟行人寂寥。于是,在尼洛夫娜“不幸的人们……”潜台词的激励下,我将那两张“传单”,毅然抛向窗外。
两张轻薄的纸片,很快便融入楼下飞舞的秋叶里,没有任何人理会,更没有产生预期中的“尼洛夫娜效应”。在不见棺材不落泪的魔鬼的诅咒下,我终于决定咎由自取了。
“尹安政,快来!”我将身子探到窗外,对正在明泽湖边玩耍的一个同班同学大喊。他家住在一楼,他姐姐是父亲非常得意的学生。
尹安政跑过来了:“什么事儿?”
我指着窗下那堆随风旋转的秋叶,压低声音:“有特务!”
“什么?”尹安政没听清:“你大点声说!”
“那儿有两张反动传单,是特务刚刚撒下的,不信你找。”说这话时,我已开始意识到其间潜在的险恶,便立刻将窗户关好,躲进屋里。
母亲下班后不久,派出所的老刘气喘吁吁地来到我家。老刘是枫林派出所的一位经常与街道妇女打交道的胖警察,老刘有严重的哮喘病,一入秋,更整日气喘吁吁的,给人一种十分敬业的感觉。
“你叫唐浩吗?”他一眼就认出了我。
“……”
“跟我去趟派出所吧。”老刘面无表情地说。“你也跟着去一趟吧。”他抬头对母亲说:“天黑了,小孩儿自己去不安全。”
母亲立刻意识到我惹麻烦了:“快说,怎么回事?”她有些气急败坏。
“我不知道呀。”我深知大难临头了,但却尽量装作没事人儿的样子。
“妈,小弟下午干什么去了?”母亲转而问姥姥。
“没干什么呀。”姥姥也感到很困惑,因为案发时她正与小妹在里屋睡觉呢。
枫林派出所在明泽湖南岸,由于天气寒凉,加之内心紧张,待我走进派出所大门的时候,早已口舌僵直浑身筛糠了。
我被带到走廊尽头的一间小屋里,母亲则被留在了大门边的长椅上。
“你叫唐浩吗?”一个从未见过的中年人笑着问我,他穿了一套深灰色的中山装,戴着一顶深灰色的前进帽。
“便衣。”我立刻确定了他的身份,目光迅速在小屋里扫了一下,还好,没见到一件刑具。只有那塌眼窝的派出所所长,拿着笔和纸,坐在我对面的小桌旁,脸上毫无表情。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那中年人依旧笑着问我,态度十分诚恳。
“不知道。”我决心打死也不说。
“你知道‘国民党大官宣’是什么意思吗?”那中年人突然问我。
“宣,就是说的意思。‘国民党大官宣’就是国民党大官说的意思。”我觉得问题太简单。
“那国民党大官说什么了?”中年人的语气骤然变得咄咄逼人,一双细长的眼睛像两把阿拉伯人用过的弯刀。
“说!”一直坐在他身后的派出所所长低吼了一声。
“那不是我写的……”我轻而易举地掉进了大人们布好的逻辑陷阱里。
审讯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其中漫长的时间在于启发我交代出我的“组织关系”,即谁让我写的。我心里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再信口开河了。十四年之后,在群众专政指挥部的刑讯室里,我也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没有的事情,打死我也不敢撒谎,因为撒谎的后果比死还可怕。
我在所有的笔录上按了手印,鲜红的清晰的一个九岁男孩的食指的指纹,散落在国共两党长期斗争的历史卷宗里。
十天之后,在所有班级都派代表参加的枫林小学的一次集会上,那个戴着前进帽的中年人,代表中山区人委教育科向全校师生通报了发生在十一月四日下午的那起“反革命事件”的全过程,宣布了“对唐浩问题的处理决定——记大过一次”。
我不知道“记大过一次”的处罚意味着什么,但听起来似乎比警告或开除都要柔和得多。
我那时的班主任已不是刘文超老师了。新来的李淑兰老师是一位从师范学校刚刚毕业不久的年轻老师。她的家族一定有色目人的血统,所以头发和瞳孔都黄黄的。李老师远比刘老师厉害得多。
“唐浩!你想不想好了!四年级三班的集体荣誉,这回算让你彻底丢尽了!”我想起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我觉得这一成语用得如此贴切。
“小祖宗,再看下去,你该发动世界大战了。”母亲把书柜底下所有的小人书都翻出来了:“你以为我和你爸都傻呀?”
父亲反而有意淡化了这件事情:“看书没有错,关键是不要再搞恶作剧了。”
直到父亲去世后,母亲才告诉我,因为我九岁时制造的那起“政治事件”,父亲在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不得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剖析自己“反动的阶级本性”,以及对子女成长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当然,这一切父亲在我们面前是只字不提,因为他十分清楚,儿童时代是人生成长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心理上的创伤一旦形成,他的儿子便极有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卑微胆怯懦弱不堪的人,一个有强烈负罪感的人,甚至可能成为一个因心理阴暗而仇视社会的人。
父亲在全力保护着自己的儿子。
一九五五年四月,遵照中苏两国领导人多年磋商而达成的协议,苏联军队从旅大地区全部撤离了。四月十五日午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正式接管了这一地区的沿海防务。至此,从一八九五年《中日马关条约》将辽东半岛割让日本起整整六十年,这片宽广美丽的土地上,一直存在的外国军事力量,终于彻底消失了。无论是帝国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
一九五五年五月末的一天,班主任李淑兰老师把我叫到教研室,李老师那时怀孕了,她挺着大肚子严肃地对我说:“这一阶段,你表现得还不错,学习也知道用功了,上课也没有小动作了,体育课也有进步了,总而言之,你已经达到了少先队员的标准。”
我的心在怦怦地乱跳,脸腾地一下子红了。
“经过中队委员会讨论,报学校大队委员会批准,同意你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请求,我在这里向你表示祝贺。”
我当时不敢看李老师一眼。
“谢谢老师!”我深深地给她鞠了一躬。
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我入队了。头天下午,在父亲的一再提醒下,我从大队辅导员那里买了一条绸质的红领巾(其他同学们都是布质的)。那天晚上,父亲一丝不苟地用熨斗将崭新的绸子红领巾熨得溜平。我接过那条温热的红领巾时,竟激动得语无伦次。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队旗下宣誓,我决心遵守队章,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做个好队员。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时刻准备着!”
这是我一生牢牢铭记的誓言,也是我高举右手,面对组织的旗帜,朗声宣读过的唯一一次誓言。在经历了近六十年的沧桑坎坷之后,我更加珍惜这个誓言,因为对于我来说,它意味着信任、理解与宽容。
一九五六年秋季开学后不久,在全国掀起的推广普通话的热潮中,操一口纯正北京话的我,又赢得了枫林小学全校师生的瞩目,成为学习和推广普通话的标兵。那一年我十一岁,嗓音清澈得像一支山间溪畔的芦笛。
在大海的深处,水是那么的蓝,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同时又那么的清,像最明亮的玻璃。然而,海水是很深很深的,深得任何铁锚都达不到底。要想从海底一直上升到水面,必须有许多许多教堂尖塔,一个接一个地连起来才成。海底的人们就住在这下面……
我最爱背诵的,就是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的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