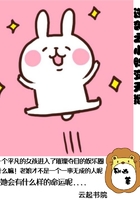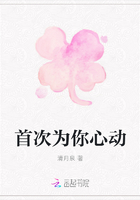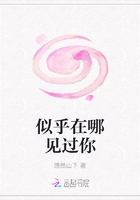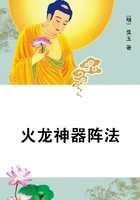一九五三年盛夏时节,小妹唐华出生了。唐华小我八岁,是父母最小的一个孩子。
唐华出生的第二天,即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深夜十点整,朝鲜半岛的枪炮声终于沉寂下来了。
一九五三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头一年。之前,在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人民以非常忘我的劳动热情,完成了诸如成渝铁路、陇海铁路、治理淮河、荆江分洪等众多工农业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结束了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局面,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确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
回想五十年代初叶的那段时光,经常有一个同样的情景不断在记忆深处浮现:一群无忧无虑的孩子们,在雨过天晴的明泽湖畔追逐嬉闹着,孩子们一边奔跑,一边趁机摇晃着路边的小柳树,后面赶来的孩子,沐浴在柳树抖落的雨水中,发出意外的尖叫和银铃般的笑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春天,当我再次漫步在明泽湖畔的柳阴下时,柔曼的柳条在和煦的阳光下舒缓地伸展着,白色的柳絮像一团团轻薄的雾气,从高大的垂柳间散发出来,将早已破败的清爽街二号,笼罩在儿时鲜活的记忆里……
我进一步认识自己的父亲,是在那洒满太阳雨的五十年代。
父亲对他的职工业余教育事业是全身心投入的。初到大连港时,他只是一位普通的语文教师,负责扫盲和低年级语文教学工作。学员是码头上的一线工人,其中大多数人都是殖民时代城市最底层的劳苦民众。
随着扫盲工作的逐步完成,大连港职工业余学校不久就成立了初中班,甚至中专班和大专班。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的岁月里,学校改名大连港红专学校。父亲则被升任教务主任,负责日常的教学工作。这期间,学校相继开设了港口管理及中文本科专业,学员全脱产,毕业时颁国家教育部承认的本科学历。
那时父亲经常奔走于大连海运学院、大连工学院、辽宁师范学院等高校之间,聘请那些专业对口的大学教授到红专学校兼职任课,自己则主动承担了大学中文教学的文学基本分类课程。每天披星戴月,辛勤而快乐。
父亲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同时,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形成了自己一套具有独特魅力的教学方法。在语文教学中,为了提高学员们对作家及作品的感性认知,他经常让我用整开图画纸依照《晚笑堂画传》,为他临摹荀子、墨子、司马迁、屈原的画像。同时,以《芥子园画谱》为素材,创作了许多首古典诗词的诗意图。他向学员们推荐大连话剧团当时正在公演的话剧《钗头凤》。他还向学员们介绍古典诗词传统的吟咏形式,等等。
一九八三年,我在大连市文联召开的一次业余作者座谈会上,认识了一位大连港的业余作者。当他知道唐子清是我父亲时,曾十分感慨地谈起父亲的一件往事。
一九六三年,他在大连港水运专科学校读书时,父亲曾是该校的教务主任。一天下午,听说老师们都到局里开会去了,他便与班里的另一个男生,在自习时间偷着跑到大走廊的一张乒乓球台前,打起球来。
那一年,庄则栋、李富荣、张燮林刚刚囊括了第二十七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前三名,并蝉联了男子团体世界冠军。全国城乡正掀起一股乒乓热潮。所以,当父亲出现在他们身边时,两个大汗淋漓的小伙子竟一无所知。
出人意料的是,父亲并没有批评他们。他十分平静地走到乒乓球台中间,分别向两位呆若木鸡的学生,深深地各鞠一躬,便默然离去了。两位学生深感惭愧,并将这件小事牢记了一生。
一九八〇年父亲的历史问题平反后,我曾去过大连港务管理局,办理相关善后事宜。
在门卫室,头发花白的老门卫在问清我的来意后,感慨地说:“无论刮风下雨,每天早晨最先走进港务局大楼的,就是你父亲。可一晃十四五年了,再没有见到他……”
在财务处,一位老会计默不作声地将父亲补发的工资全部核定之后,十分认真地将钱点好,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递出窗口。
“你是唐子清的儿子吗?”
我点了点头。
“唐老师可还健在?”他望着我。
我摇了摇头。
他也摇了摇头:“可惜啊……”
一一三号是一个套间公寓。父亲、母亲与唐宛、唐华住在里屋,我和姐姐、姥姥住在中间屋,外屋是一个餐厅兼起居室。每天晚饭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天南海北地高谈阔论其乐融融。父亲在去世前,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清爽街二号十三年的时光,是他一生中最稳定最充实的岁月。
在父亲的鞭策与监督下,唐家姐弟在这期间养成了许多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些习惯渗透于我们的进退揖让,饮食起居之中,成了唐家独特的家风。
父亲对每一个家庭成员的着装仪表要求十分严格的。我家的许多衣服,都是由铁路医院正门对面,一位姓栾的女裁缝量身定做的。父亲并不拘泥于程式化的制服,我们姐弟四人的衣服许多由他亲手设计,他为我和姐姐设计的学生夏装,为唐宛设计的墨绿色泡泡纱裙裤,放在今天也毫不逊色。
那时的衣料大多是纯棉和毛料的,所以全家人的衣裤都需熨好后再穿,不能含糊。父亲很在乎手绢、雨伞、头巾、鞋帽等细处,他的手绢从来是熨好再用,而雨伞则更讲究,绝不用坏伞。
“不要粗糙地对待生活。”这是父亲常说的一句话。
父亲从不挑食,但对每天晚饭时餐具的摆放,却格外挑剔。那时我家有几套餐具,母亲炒菜时,偶尔会将不是一套的盘子混在一起用。遇到这种情况,父亲总会皱起眉头,母亲再忙,也不得不将菜肴重新装盘。每逢这时,母亲都会暗自生气,我们也会从心里替母亲鸣不平。
最整齐和有条理是父亲要求我们必须做到的。他经常强调所有的东西都要放在最合适的地方,所以我家的所有物品都有它们固定的位置。父亲常说:“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十几年来雷打不动。
在日常生活中,父亲十分注意公共意识及自律能力的培养。他要求我们严格遵守时间,不许穿睡衣走出家门,公共场所要有礼貌,懂谦让,不喧哗,要善待下人。
遇到闲暇,父亲也会带一家人去位于职工街的国际海员俱乐部度周末。那是一个隶属于大连港的涉外机构,有很多中外文杂志的阅览室、小影院、理发厅等供外国船员休息的服务场所。大连港的知识分子们,偶尔也会光顾这里聊以自慰。
每逢去海员俱乐部前,父亲都要格外审视孩子们的穿戴,同时嘱咐我们,在外国人面前,要有礼貌,要挺起胸来。
父亲一生爱竹,这和他品格高洁、待人谦和的道德素养是密不可分的。在父亲的书桌上,一直放着一个龙泉窑的梅子青束竹笔筒,那是北平觧放前夕,父亲在东单旧货市场上淘来的。在那段兵荒马乱的日子里,父亲还从汇文校友孙德亮那里,求得一幅郑板桥咏竹对联:
未出土时先有节,
到凌云处仍虚心。
1969年农历二月初三,我曾吟诗一首,遥祝父亲六十岁生日。
红尘独素心,春秋满六旬。
凭生竹骨硬,风雨一狂人。
这时的父亲己被红卫兵遣返原籍务农,我则在狱中。
父亲平时除吸烟外,读书和收集剪报成了他唯一感兴趣的事情。他经常把报纸上一些他认为有用的文章剪下来,分门别类地粘贴在过期的《红旗》杂志里。时间长了,他收集的剪报竟成了一部内容丰富的百科全书。我就是通过这些整理好的剪报,才认识了诸如刘白羽、杨朔、秦牧、季羡林、宗璞等散文大师,认识了建筑学家梁思成、数学家华罗庚、地质学家李四光和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了解了包括拓扑学、人工合成胰岛素和晶体管计算机等陌生而神秘的未来世界。
当然,小学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课外读物还是小人书。因为从小崇拜英雄,同时喜好绘画,所以那时我对小人书几近痴迷。
为了买小人书,我学会了撒谎,甚至学会了从母亲的口袋里偷些零钱(整钱却从不敢拿)。而偷着买来的小人书,不得不藏在父亲的书柜底下。时间长了,书柜下面让我塞得满满的。所幸的是,由于我保密工作做得好,这一切父母竟全然不知。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北京百万市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发出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豪迈誓言,两岸关系骤然紧张起来。单从当年十一月份的大事件中,人们便会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险恶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