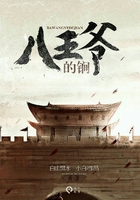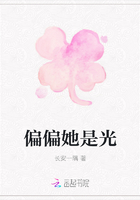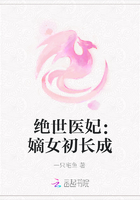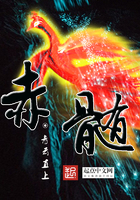从一九六二年入秋时起,母亲便几次将我的绘画习作,寄给徐悲鸿的遗孀廖静文夫人,希望她给予指点。因为我已下定决心,一九六三年夏天报考中央美术学院附中。
一九六三年六月初,我如期来到北京。在三舅家住下后的第二天上午,按照廖女士信中的地址,在北京火车站东侧的东受禄胡同,我找到了徐悲鸿纪念馆。
那是一个很大的中式四合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我来到院子一侧的一扇小门前。门旁钉着一块“参观者止步”的小木牌,推门进去,一栋白色的现代建筑掩映在花木繁茂的院落里。
女佣是一位很安静的中年人:“廖先生知道您今天来,她让您先坐下等一等,她很快就回来了。”
那是一个显得有些拥挤的大客厅。迎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徐悲鸿先生手书的对联:“生不知死,乐以忘忧。”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尊牧人驭马的铜雕,那显然是一件外国艺术家赠给徐先生的礼品。客厅的一侧兼做餐厅,阳光从窗外洒进来,餐桌上一束鲜花怒放着,散发着淡淡的香气。
院子里传来人声,廖先生回来了。
廖静文是一位风韵典雅的中年女人,她肤色皙白脸色红润,大概是刚从阳光下走进屋来,她显得有些疲倦。
“是大连来的客人吧?”廖先生笑着问我。
“我叫唐浩,李玉玺是我母亲。”我十分局促地向她致意。
“你妈妈还好吗?”廖先生十分平易近人:“先生去世之后,中央美院曾安排我去大连疗养,我知道你们在大连,但没有联络方式。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六年,我在大连住过一年多呢。”
坐下来后,廖先生和我说:“你的那些习作,我都转给美院附中的老师看了。基础很不错,所以教务处的陈主任同意你来北京参加考试。”
这些我都从廖先生的信里知道了。
“你现在就去附中,找陈主任,他知道这件事情。先报上名,考试大概还需等几天。”
我站起身来。
“你住在哪里了?”廖先生问我。我说住在三舅家。
“还好,东总布胡同离这儿不算远,美院附中在隆福寺。”廖先生详细地告诉我怎么走。
从徐悲鸿纪念馆走出来,我激动得难以自持。三年来,尽管我给父母添了天大的麻烦,但我终于依照自己的意愿,向我期盼已久的美术学院接近了。我有足够的把握考上中央美院附中,因为连孙继海都肯定地说,这一回我将留在北京了。
陈主任是一位戴眼镜的南方人,在看完我填写的履历之后,他皱起了眉头。
“你初中毕业之后,念过中专?”
“念过。在大连工业专科学校。”
“几年?”
“两年。”
“哎呀,廖先生没和我谈过这些。”陈主任为难地向我解释:“按国家教育部规定,凡接受过中等教育的学生,就不能再读中专了。美院附中和大连工业专科学校一样,同样是中等专业学校。看来,你没有资格报考附中了。”
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结果。那一瞬间,我大脑里竟一片空白。没有再解释的余地,更没有再争取的可能。我气急败坏地赶回廖先生那里。廖先生也通过电话与陈主任交涉了很长时间,但最终还是沮丧地挂了电话。
“我真没想到,他们还有这些规定。”廖先生有些赧然:“再准备一年吧,明年再来考美院本科吧。”她十分惋惜地安慰我。
轮船在一片漆黑的渤海里夜航,我独自一人伫立在海风呼啸的甲板上,高高的船舷下,一条灰白的航迹伸向黑暗里,望着头顶那迷乱的星空,我开始有些惶然了。十八岁了,当我面对这个告别少年时代的庄严时刻,我终于发现,自己竟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任性自负和不踏实,让我深陷困境。
“这三年等于买了一个教训。”父亲在他写字台的右手处,给我留下了一封长信:“……一切从头再来吧,从高一开始,老老实实地修完基础教育,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天上掉不下馅饼来。”
在这封信的下面,是他让我再次熟读的荀子的《劝学篇》,并对以下的篇章做了圈点。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螾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
于是,一九六三年秋季入学的时候,我和朱嘉禾一起考进了民办大连海群中学。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大批中等教育学校下马,大量学龄青年失学、辍学,给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为缓解这一压力,一些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孤军奋战,承担起了让这些失学青年重新走进校门的重任,民办中学应运而生。民办中学的身份虽入不了国家教育的正册,却也让这些游荡在社会上的年轻人,有一处权宜去所。至于今后的出路,便只能听天由命了。
海群中学,是一所由大连水运专科学校校长伊树志牵头创办,由大连港务局资助的民办中学。学校分初中部和高中部。分班之后,我在高一一班,朱嘉禾在高一二班。
在我们入学后不久,全社会开始利用强大的舆论工具,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是全党全民在今后漫长历史时期的工作重点”。几乎在同时,《人民日报》就苏共中央《公开信》,先后发表了九篇评论员文章,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终于白热化了。中国与东西方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开始了长期的对峙。
一九六四年早春,嘉禾家出事了。在朱妈妈的右派帽子刚刚摘掉后不久,朱伯伯因历史问题,被定性历史反革命分子,并被市政协清退,下放到长春路副食品商店调味部,成了一个五味杂陈的售货员。
嘉禾是在一次放学的路上,和我谈起这件事的。嘉禾素来不关心政治,但这一次他却忧心忡忡:“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四类分子子弟了,以这种家庭出身报考上级学校,看来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考进海群中学后,我和嘉禾都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高中毕业之后,我要冲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而嘉禾则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
比起其他正规高中来,海群中学是一所弥漫着自由主义情调的年轻人的庇护所。民办中学的师资来源,自然鱼龙混杂。其间,有教育界的前朝元老,有在五十年代因口无遮拦而马失前蹄的年轻人,有在博爱市场与我一样练过摊儿的失学青年等。其中有的老师与同学之间只两三岁之差,并最终成了朋友。
就学生成分而言,海群中学更毫无原则地招纳了许多正规高中不可容忍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子女,及曾在社会上有过非凡经历的社会青年。由于都曾经有过失学的经历,所以海群中学的学生年龄,要比正规中学偏高,社会阅历也复杂得多。
在这所不太讲政治的学校里,当然也必有另类。高二上半年,新来的一位姓杨的班主任就曾在同学中设立秘密监察组,并无时无刻地监视全班同学(包括学生干部)的一言一行。
监察组据说有六七个人,都是从班级里那些最不显山露水的同学中精心筛选出来的。他们只与杨老师单线联系,彼此之间仍可互相监督。监察组一经宣布组建,全班同学即刻噤若寒蝉,人人自危。
杨老师平日目光犀利,一头自然卷曲的头发精力充沛地耸立在头顶。直到今天,当年监察组的成员仍是一个谜。他们就这样长期潜伏着,成为海群中学高二一班同学们回忆中的一个悬念。
海群中学和海港俱乐部只一箭之遥,作为一个大型国有企业下属的文化宣传机构,当时的海港俱乐部不仅拥有一个半专业的文化演出团体,更有一座颇具规模的图书馆。俱乐部主任王斋是父亲的老朋友,从他那里,我搞到两张借书卡,并在两年的时间里,阅读了大量有关文学、地理、历史、建筑、国际关系、战争文化的书籍。应该承认,这种阅读对我是有帮助的。我的作文,经常被当成范文,从初一传到高三,而推动这一传播的,便是我高中语文课任王传珍老师。
王传珍长我四岁,是一位谈吐儒雅的年轻人。困难时期他被迫辍学,曾以卖冰棍养家糊口。作为一名文学青年,王传珍很早就在报刊上发表过散文,因此备受同学们的尊敬。二十年之后,在大连《海燕》文学月刊编辑部,王传珍成了我的责任编辑。又过了五年,在大连电视台电视剧部,我和王传珍最终成了同事。
当然,真正影响我文学审美取向的,应该还是鲁迅先生。
最先接触鲁迅先生的是他的《一件小事》。随后,在海港俱乐部的阅览室里,我一口气读完了先生所有的小说和散文,并就此沉浸在作家笔下江南岁暮那清冷潮湿的季节里。长此下去,我学会了沉默,习惯了孤独,开始了思考。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条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故乡》)
……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晴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傲僈,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在酒楼上》)
鲁迅的笔下,为我们塑造了一大批包括农民在内的中国底层社会的边缘人物,先生给予他们无限同情与悲悯的同时,也深刻地剖析了在封建社会几千年的重压下,留在他们身上那些丑陋的印痕。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象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故乡》)
鲁迅先生的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我,这影响延续至今,成为我世界观的一部分。
因为是一所民办中学,所以,海群中学的教学条件是很差的。大连港东部作业区一处空置多年的仓库权做教室,而学生课间活动,便只能分散在港湾广场的大街上了。
一天课间操时,朱嘉禾对我说:“听说了没有?昨天下午,我们班一个女生在街上掏包,让警察抓住了。”
“女生?谁呀?”我好奇地问,一边按照广播操的节拍做转身运动。
“前边穿粉红色条绒的那个女生,看见没有?”
我向前望去,心里突然感到莫大的惊诧与困惑,原因很简单,自打走进海群中学,那女生就一直在我的视野里。
“怎么可能呢?”我在为她辩护。
“嗨,知人知面不知心呀。”嘉禾开始做伸展运动了,他做课间操时很认真,而我却无端地沮丧起来。
那是一个看上去十分完美的女高中生。之后不久,她家也搬到清爽街二号了,但我们之间仍形同路人。这也是六十年代初叶,大多清高自负的男女高中生所共同拥有的一种性格——孤傲且矜持。
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嘉禾又和我谈到了小提琴演奏家帕格尼尼。嘉禾那时的提琴已炉火纯青,他拉琴的姿势非常潇洒,他常把提琴拎到学校去,利用午休时间,给大伙儿来一段《流浪者之歌》。
我发现那个女生,正在前面不远处独自回家。
“说实话,无论如何我也不相信,她会是个小偷。”我打断了朱嘉禾的“琴声”。
“谁呀?”嘉禾莫名其妙地问。
“前面那位。”我用下巴向前指了指。
“小偷?”朱嘉禾一凛:“谁说的?”
“你说的。”我提醒他:“上次做课间操时,你不是告诉我说,她掏包让警察逮着了吗?”
朱嘉禾在努力地回忆着。
“那时她穿一件粉红色的条绒上衣。”我进一步提醒他。
“嗨!”嘉禾大笑起来:“错啦!天呐!我是说另一个……”
那两年,女孩子当中流行穿条绒上衣,而其中最靓的色彩,便是粉红了。在海群中学,穿粉红色条绒上衣的女生,起码也有二十个。
“她是海港医院毛大夫的闺女。你怎么搞的?”嘉禾认为是我脑子出了问题。
毛大夫我认识,是海港医院著名的儿科专家。父亲和他很熟,那是一个慈祥和蔼的哈尔滨人。
我的心里一下子释然了。之后不久,在清爽街二号,我便主动与她搭讪了。
高中二年级开学不久,开始分文理科班了,高二一班被定为文科班,朱嘉禾和毛大夫的女儿便都转到我们班了。高二一班的班主任是英语老师李贤强,在新同学转班点名的时候,我才知道她叫毛宁。
“good morning,good name!”李老师望着她,风趣地点了点头。
随着困难时期的逐渐远去,中国人的革命浪漫激情很快又被重新点燃。与以往不同的是,自一九六三年之后,一种浸染了西部牛仔色彩的新的生活方式,出现在城市知识青年的面前。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党的召唤下,边疆、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青年垦荒突击队,一时间成了一代青年追求浪漫与自由生活的一种遐想。诗人贺敬之的那首《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更让多少富于幻想的年轻人如醉如痴。
在九曲黄河的上游,
在西去列车的窗口,
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
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
一九六五年早春三月,在我高二下半学期开学后不久,一次突然召开的全校动员大会,让海群中学全体同学沉浸在群情亢奋的震荡之中。
一位中山区委教育科的徐科长,用诗情画意般的描述,为同学们展现了一幅色彩浓郁的山水长卷,一个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相媲美的光荣与梦想。
徐科长始终面带着微笑。突然,我发现了那笑容如此熟悉,我确信这是一个曾经与我打过交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