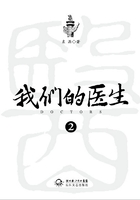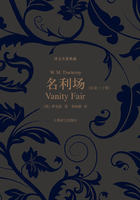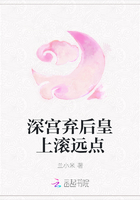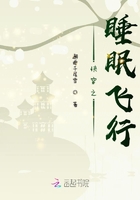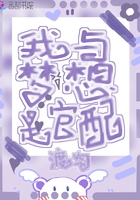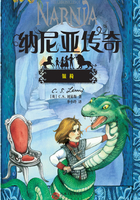一九六六年九月的最后一天,一辆从滦县开往迁安的长途汽车,在滦河爪村渡口前停下了。车上的乘客挤下车来,争抢着拥上一条泊靠在渡口的平底大木船。待我和唐宛相互搀扶着最终挤上木船后,三位艄公便吆喝着,将三根长长的竹篙插到岸边的鹅卵石滩上。
渡船离开了河岸。站在船头向北望去,在一片平坦的原野的尽头,延绵不断的群山像一道黛紫色的屏障,横亘在故乡的大地上。夕阳下,古老的万里长城,犹如一条时隐时现的金蛇,自东向西跌宕在群山的峰谷之间。向东望去,一座锥形孤山远远耸立在下游对岸的台地上,山顶上的一座古塔,在落日的余晖中熠熠生辉。
“哥,老家快到了。”唐宛惶惑地望着我。
我点了点头。
这就是我的故乡,这就是父亲出生和长大成人的地方。我曾多少次想象过故乡迁安的模样,但今天真的走近它时,心情却无限的忧惧。
在沈阳转车时,唐宛就决定跟我一起回老家了。当大连的家顷刻之间灰飞烟灭的时候,唐宛便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她无时不刻地惦念着父母,她希望尽快见到故乡的那个家。因为那将是一片让她继续生根的泥土,一座遮风避雨的石崖。
从渡口对岸重新登上一辆长途汽车后不久,我们见到了黄昏中的迁安县城。
“哥,咱们上哪儿去?”走出荒凉的公共汽车站,唐宛困惑地望着我。
“别怕。”我尽量安慰她:“咱们找唐桂瑞大哥去。”
“你认识他吗?”唐宛问我。
“不认识。但找到迁安高中,就能找到他。”
唐桂瑞是三爷的长房长孙。师专毕业后,一直在迁安高中当教员。由于工作出色,几年前被升任迁安高中的教务主任。这些年来一直与父亲有书信往来。
很快,我们就找到了灯火通明的迁安高中,但从踏进校园的那一瞬间,我就惊恐地意识到,我们自投罗网了。
在传达室,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问清我们的来历后,从校园深处便跑来一大群戴着红袖标的人。一个身穿草绿色旧军装头领式的人,从人群后挤了过来。
“你是唐桂瑞啥人?”他操着冀东那别样的口音,脸色阴沉地问我,手里攥着一条结实的军用皮带。
“唐桂瑞是我三爷的孙子,我是他的叔伯兄弟。”我慌忙解释说。
“你是干啥的?”他盯着我问。
“我……”我立刻意识到,此时绝不能实话实说。
“我们回老家探亲,天晚了,想找唐桂瑞帮我们找个旅店住下,明天再走。”
“她是谁?”那头领指着一直躲在我身后的唐宛。
“她是我妹妹。”我急忙解释。
“你们从哪儿来?”那头领摆出一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架势。
“我们从大连来。”我开始梳理自己的思路:“明天国庆节放假,我和妹妹想回老家玩几天。”
“你什么出身?”他突然问我。
“革命干部。”我把脖子一扬:“我爸在大连港军运处工作,你们可以打电话调查,我爸单位晚上也有值班的。”
这几句话,让挤在传达室里剑拔弩张的红卫兵们一下子松弛下来。
“大连我去过。”那头领人物掏出一盒烟来递给我一支,我慌忙摆了摆手:“不会,我不会。”
“我叔家的二姐,带我去过老虎滩公园。”他把手里的皮带束在腰上:“不瞒你说,唐桂瑞已经被我们专政了。他是迁安县教育系统典型的走资派,你们可得和他划清界限啊。”
我早已料到是这个结果,唐宛脸色苍白地望着我。
“还晕车吗?”我给她使了个眼色。
“晕。”唐宛颤颤地说。
“你们赶紧找个店住下吧。”那头领回头对几个女红卫兵说:“赶紧的,带他们找个店住下。”
我和唐宛走出迁安高中校园的时候,我的秋衣已完全湿透了。
“哥,要是他们万一给海港军运处打电话,今天晚上,咱们可就死定了。”住进旅店之后,唐宛惊魂未定地说。
“军运处的电话属部队专线,凭他们传达室的那部手摇电话,我料定他们也不会自讨没趣。”
话虽这么说,可我心里还是像刚从刑场上被人拖回来一样,狂跳不止。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就离开小旅店了。那是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即共和国十七周年的国庆日了。但此刻的迁安古城,仍沉浸在一片清冷的晨雾里。街上显得很萧条,街道两旁大都是上百年的灰砖老瓦房。整个县城显得低沉且荒寂。
父亲曾说过,从县城向东走,过了胡各庄、半坡营、李官营就是故乡唐庄了。这几个村庄均相隔五华里,唐庄距县城二十华里。
半坡营在一个漫长的沙坡台地上。从半坡营再向东走,原野变得格外辽阔而平坦。向北望去,海一样的燕山山脉自东向西延绵逶迤,山峦之上的长城烽燧参差错落、清晰可见,巍峨的秋云从燕山深处向平原上空涌来,巨大的云影在田畴河流间缓慢地移动着,让人感到一阵温暖,一阵苍凉。大地正值收获季节,色彩浓郁而斑斓。
这就是我的家族世代繁衍生息的故乡。走过李官营,在一位拾粪老人的指引下,远远地,我看到了那一片绿阴覆盖下的村庄。正在地里收获的男男女女,睁着惶惑的眼睛望着我和唐宛,我知道,这些陌生的庄稼人,就是与我骨肉相连的父老乡亲。
村庄在一片土坎子下面,顺着一条青石板铺就的斜坡,我们走进了唐庄。一个黑脸膛的男孩子站在路边,我走上前去向他打听三爷家的住处。
“唐宗合在北街东头住。”那男孩子指着村庄里一棵高大的老槐树:“过了大槐树,路北不远就是唐宗合家。”他站在那里望着我:“你是他家啥人?”
“唐宗合是我三爷。”我向他道谢。
“你是唐子清我大爷家的吧?”他直直地问我。
“是。”我有些紧张,我不知道父母被遣返回乡后,这里已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该叫你大叔啊。”他忽然笑着对我说。他的牙齿很整洁,笑容里透着一股机灵劲。
“我带你去。”说着,他便跟在我身边:“大队把你们家分到我们队了。就住在唐子廷的车门房里。”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他。
“我叫立春。我爷和你爹是一个太爷的孙子。”说着,他冲着站在北街上的几个村妇大声喊:“大奶呀,你们家来客啦!”
那几个妇人立刻转过身来望着我们,一个大眼睛的中年妇女忽然兴奋地朝院子里喊:“他大妈,快出来,他大哥来家了!”
“妈!”唐宛抢先朝前跑去。我看见唐华从一座门楼里探出头来:“二姐……”紧接着,母亲也出现在门楼里。
仅仅四天未见,母亲显得很疲惫。但她却一直微笑着,让我从心里感到无比的宽慰与温暖。
“回来了,回来了。”她高兴地望着我和唐宛,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光。
“大公子回来了。”随着一声吆喝,一个脸色红润的四十多岁的男人从门楼里走了出来。
“这是你四叔唐子玉。”母亲赶忙介绍说:“这几天多亏了你四叔和四婶,初来乍到的,给人家添了不少麻烦。”
四叔一直在笑,那笑容里透着一丝狡黠。
“回来好,回来就对了。”他望着我感慨地说:“你小时候,我还带你上街买过糖葫芦呢。忘了吧?”他嘿嘿讪笑着:“那时候你们住在江擦胡同二十九号,你爸成天开个吉普车,威风。”说着,他长吁了一口气:“唉,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唐子玉和父亲是一个爷爷的孙子,他们从小就按大排行论长幼。父亲最大,二爷家的唐子连排二,三爷家的唐子藩排三,二爷家的次子唐子玉排四,子洵叔叔排五,四爷家的唐子余排六。父亲继母生下的唐子波,因为从小在大家族中受排斥,所以没有再续上排行。
母亲走出来的这个门楼,就是太爷唐开欣当年亲手营建的老院。这是一座看起来十分殷实的冀东老宅。在正房东屋,母亲带我和唐宛,见到了已近垂暮之年的三爷和三奶。坐在炕上的三爷,眼睛已昏黄黯淡了,他懦懦地望着我:“在家住些时日吧,认认庄里的叔叔婶子。早晚还是要回去的。不碍事。”
唐桂瑞家的大嫂子听说我们去了迁安高中,赶紧凑上前来打听她丈夫的消息。唐桂瑞的父亲唐子藩三叔更狠狠地骂道:“王八蛋操的!一群活牲口。连县长都敢捆,真是要翻天了。”他朝地上吐了口痰:“呸!活腻了,小杂种们活腻了。”三婶赶紧在一旁劝:“小点儿声喊吧,我看你是活腻了。”
屋子里的人越聚越多了,男男女女的一时竟难以分清长幼尊卑来。六叔唐子余也来了,在他身后,跟着一群结结实实的小伙子。六叔有五个儿子,见面后称兄道弟的甚是温暖。
“回家来躲几天清净,挺好的。”六叔望着我:“要不然的话,哪儿有机会回趟老家啊。”
我感到心里很安然,这种安然是多少年来不曾感受到的。因为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我们竟然还有这么多血缘至亲。他们世代生活在故乡的青天黄土之间,你可以不去理会他们,而他们却一直关注着你。
父亲回来了。唐桂金赶着大车,帮父亲从夏官营买来了炕席、水缸、风匣、铁锅等一大堆农村生活必需品。几天没见,父亲显得精神了许多,动作也敏捷了许多。他给三爷带回一包茶叶,给三奶买了些日常药品。我看到,一向威严的父亲,在三爷、三奶面前却毕恭毕敬的。我感受到了家族那种难以割舍的凝聚力。
父母回到唐庄后,大队及贫农协会从家族亲疏考虑,决定将我们分到北街的唐庄一队,并从唐子廷家征来一间车门房,让我们暂时住下。唐子廷家与三爷住的老院只一墙之隔。上午进村时,那个大眼睛的中年妇女,就是唐子廷家的大婶。
两天来母亲已经和唐子廷大婶处得很熟了。大婶是一位热情大度快言快语的冀东妇女,子廷大叔长年在外教书,大婶一个妇道人家拉扯五个儿女,家里家外十分不易。唐子廷大叔虽然出身地主,但这些年来凭大婶不卑不亢上下周旋,在庄里始终让人高看一等。
所谓车门房,其实就是唐子廷家老院临街临门的一处平房。这是当年长工住的地方。子廷大婶和孩子们住在正房,我们两家一个院子前后住了六年,直到一九七三年我们在沙沟南盖起了新房。这期间,我们与大婶家冷暖相通、休戚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当天吃过晚饭后,挤在三爷家温暖的火炕上,父亲与三叔、四叔、六叔谈起了故乡的往事,母亲与几位婶子们则算计着过冬所需的柴米油盐。我依偎在三爷的身边,几天来心力交瘁的疲惫渐渐地缓释了。
当天很晚的时候,父亲带我去了唐子连二叔家。
唐子连与唐子玉是二爷的儿子,当初分家时,二爷家也分了五十亩地。但二爷生性乖戾,又染上赌博恶习,家境很快就败落了。二爷死后,唐子连与唐子玉不得不去关外闯荡,待土改时,自然因祸得福成了贫农。
站在二叔的面前,我发觉他一直在笑,那笑中含着难以言传的冷刻,让人感到他在侮辱我。
“你过去要回唐庄来,你是大公子,是块金疙瘩。现如今你回来了,连块土疙瘩都不如。”我没想到二叔竟如此绝情:“往后,你知道我是你二叔就行了。我这个家,你尽量少来。”
父亲坐在那里一直沉默不语。临走时,父亲只说了一句:“记住二叔说的话。”
我从此记住了二叔的教诲,更记住了二叔的那张幸灾乐祸的脸。
回到唐庄的第二天,父亲让我跟他去了老坟。
那是一个无风的早晨,父亲避开村庄里那些疑惑的目光,带我顺着村南一道弯曲的沙沟,绕过学堂后面的一个小操场,来到一面平缓的坡地前。四周静极了,一夜的寒露让路旁开始收获的田野如水洗般清冷而沉郁。
父亲急匆匆的脚步停下了。一片长满荒草的土坟,静卧在三五株枝干苍劲的古松下。父亲远远地站定了,他深吸了一口气,声音喑哑地对着那片坟地说:“……春莹回来了,春莹带唐浩回来了,春莹没做过一件对不起祖宗的事……”
这是我第一次拜谒家族宗墓。一个多月后,这片二百几十年来,为几代族人营造起来的墓地,便在破“四旧”群众运动逐渐向农村深入的呼啸声中,被一夜之间突然疯魔了的人们彻底夷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