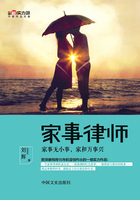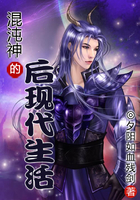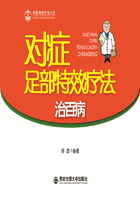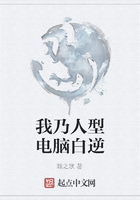在北京返回大连的火车上,姐姐却目睹了一幕惨剧。七八个男女红卫兵,将一个中年妇女的双手,吊在车厢的行李架上,那女人耷拉着脑袋,站在硬席椅子上无声无息。汗水和尿水将那条肮脏的裤子,紧紧贴在她的腿上,两个不大的孩子,浑身发抖地挤在她的脚下。孩子的哭声像小猫在哀泣。
一个扎着两只小辫的女红卫兵,抡着一条武装带,不断抽打那女人的脸:“我让你再跑,地主阶级的狗崽子……”那女红卫兵的音色好极了,胸腔共鸣极具声乐天赋。姐姐和同学们冷冷地看着她。
九月三日吃罢晚饭后不久,大连港水运专科学校的红卫兵敲开了港—十七我家的门,那一天是周六,父亲刚从海港农场赶回家。
这是我家经历的第二次抄查,第一次是北平解放后不久,抄的是江擦胡同二十九号。
连那盆万年青都被红卫兵倒扣在地上了。在港—十七这样简陋的职工宿舍里,只有这大花盆里,才能藏匿下一支勃朗宁手枪。
九月三日的抄家,抄走了许多对这个家庭来说极其珍贵的历史照片,包括冯玉祥将军的一幅中堂、孔德成先生的一副对联及大量的家庭及个人档案。值得欣慰的是,整个抄家过程是在一片无声无息中进行的,父亲曾代理过水运专科学校的教务主任,学生们知道父亲的为人。
九月的大连,在短短一周时间里,已剧烈地倾斜了。伴着高音喇叭的喧嚣,大街上不断出现游街的车队,造反的人们押着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于街头示众。路人们拥挤在车队周围,欣赏着那一张张失去血色的脸。每一个游街者的脖子上,都挂着一个沉重的牌子,上面书写着他的罪恶。被游街的女人们往往是观众瞩目的一个亮点,为此,兴奋的红卫兵会将那些女人的头发从中间剃掉一半,为了表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精神,红卫兵还会找些破鞋串在一起,挂在她们的脖子上。力图从道德上羞辱这些无法辩解的妇人。
在市委书记胡明和市长许西同志相继被押上游街车队的情况下,市民的根本人权更被施暴者彻底地践踏了。
石山农场刘双喜的父亲,大连中医医院的老院长便是在这暴乱的九月里,在游街车队行驶到胜利桥上的时候,不堪羞辱,纵身从汽车上跳下,随后翻身越过桥栏,摔死在铁道纵横的路基上。
在狂躁的九月里,父亲因一直在农场劳动,避开了游斗的风潮,这期间父亲很少回家了,母亲劝他说,此去农场倒不一定是什么坏事,母亲知道,父亲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倘若遭遇这样的凌辱,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和父亲这一阶段常有书信往来。一次,父亲在给我的来信中写了一段小诗。
“心满事,衣满尘,
收工路上思远人,
传达喊老唐,儿书抵万金。”
我从心里怀念清爽街二号那段平静的岁月,我无限挂念自己的父亲。
九月二十日,我借故请假回了大连。家里经过一次抄家,小妹唐华每天都提心吊胆地待在家里不敢出门。那一年她小学刚毕业,而上级学校的招生工作却迟迟没有进行。
唐华音乐天赋很强。小学毕业前已被沈阳音乐学院附中录取。担任招生工作的包满华老师是唐宛的师姐,曾到清爽街二号做过客。包老师很欣赏唐华,她肯定地说,只要努力,唐华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手。
但唐华的命运,从一九六六年九月起将被彻底改变。那一年,她刚满十三岁。
九月二十三日,也就是我回大连后的第二天中午,母亲突然提前从单位赶回家了。一进门,她就气急败坏地说:“要赶咱们下乡了,单位找我谈话了。”
那天上午,结核医院一位女书记,把母亲找到办公室:“你爱人单位来人了,大连港已准备将你们全家遣送河北原籍,你要理解这场革命的群众运动,尽快将手里的工作交代一下,至于你的个人问题,医院决定按提前退休处理。”
“假如我不退呢?”母亲如五雷轰顶,她打断了女书记的谈话。
“你不退对你是不利的,我们会让辽宁财经学院的群众组织,做你女儿的工作,一旦如此,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女人冷冷地说,话语间暗含杀机。
母亲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当天下午,一身风尘的父亲背着行李也赶回家了。进门后,他从母亲的眼睛里便明白了一切。
“我被单位处理了。”说着,他放下行李朝厨房走去。
“上午单位就通知我了。”母亲望着父亲,再也无话可说。
父亲从水龙头里接了一杯凉水一口气喝光。接着便是长时间的沉默,一家四口人就这样默默地坐着,直到屋子里渐渐地暗了。
黎明到来之前,躺在床上,我听见父母在厨房里的谈话。
“离婚吧。”父亲平静地说:“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放了你和唐华。”
“……”
“唐浩由我负责,唐华由你负责,唐棣和唐宛眼看就要毕业了,她们的事情我会提前安排好的……”
“……”
“离婚吧。”
“子清。”母亲终于说话了:“记得《圣经》里有这样一句话:求你阻拦我,不要让我明知故犯,不要让罪恶胜过我。唯有这样,我才能脱离罪恶,成为无过的人。这些年来,我一直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告诫自己,因为早晚有一天,我是要面对上帝的。”
长时间的沉默。
“难为你了,玉玺……”又一次,我听见父亲嘤嘤地哭了。
面对家庭突然深陷的灾难,母亲很快便平静下来。她开始有条不紊地清理着家里的东西,她将姐姐和唐宛的衣物整理出来,把要带走的和决定丢下的东西,一件件分清。不久,姐姐和唐宛都回来了,在一次晚饭后,父亲开始与我们谈到了今后的事情。
“我从此没有工资了。”父亲尽量平静地说:“唐棣和唐宛虽然都将毕业了,但考虑到眼下这难以预料的局面,估计你们暂时在经济上都难以自立。因为妈妈还有一部分退休金,所以今后唐宛的生活费我们将继续负责。我已写信给沈阳的徐叔叔了(徐维廉的长子徐志远),从下个月开始,徐叔叔每月给唐棣寄十元钱,权作生活费,实在不够,我们将为你贴补。”父亲望着自己的两个女儿,语重心长地说:“从今往后,你们两个就是爸爸妈妈唯一能留在城里的孩子了,你们一定要好自为之,在城里把脚跟站稳。”
父亲那一天的脸色很不好,他一直在拼命地吸烟,屋子里飘浮着青色的云霭。
“从现在看,这场运动的前景实在难以预测。为防备万一,你们三个都记一下几位亲友的通讯地址。”
我们慌忙找来纸笔,静听父亲几乎一字一顿地将徐叔叔在沈阳的地址,祁伯伯在重庆的地址,以及仰山伯伯和二舅在北京的地址记好。
“一旦失散了,就分别与这些亲友联系。我和他们几十年风雨同舟,即便当中有人也遭不幸,我想,总还会有人幸免于难的。”
从父亲的话语中,我已清醒地意识到,我们面临的将是一场战争般的劫难。
“爸,我跟你们一块回老家种地去。”我终于把两天来自己一直在考虑的想法跟父亲说了。
“你?”父亲愣愣地望着我。
“我决定跟您一起回老家种地了。”我望着父亲郑重地说:“你们走后,我立刻去南尖办理转户手续,顶多三四天,我就去唐庄了。不管怎样,我还是应该和爸妈在一起,这个家,无论如何不能分得太碎了。”
“不能分得太碎了。”父亲喃喃地重复我的话,他突然精神一振:“好,一块儿回去,一切都再从唐庄开始,你们还年轻,你们的路还长着呢。”
望着我,母亲宽慰地点了点头。
唐宛回沈阳前,我们兄妹四人在天津街的大连摄影社留下一张合影。照片上留下了一行文字:“分别留念。”
三十一年后,我们姐弟四人又拍了一张合影,那是在清爽街二号楼前拍的,也是我们姐弟四人几十年来唯一的一次团聚。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是这个家庭与这座城市诀别的日子。
下午三点,我们离开了港—十七家属宿舍。没有和任何人告别,也没有任何人出来送行,我们默默地走下五楼,父亲挽着母亲,谁也没有再回头。
在父亲的提议下,父亲和母亲在大连摄影社留了一张合影,这是父母结婚二十六年来的第一张合影,也是他们厮守一生留下的唯一一张合影。那一年父亲五十六岁,母亲五十一岁。
今天,当这张照片再次摆上案头的时候,父亲、母亲那坚毅的目光,依然默默地注视着我。
在站前广场指定的地点,我们见到了负责押送父亲遣返原籍的几个红卫兵。他们都是大连水运专科学校的学生,每个人的脸都很阴沉。
由于后天就是国庆节,所以大连火车站的站前广场上,人山人海地挤满了要去北京串联的红卫兵。人们希望此去能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朝圣般的喜悦与庄严。
在解放军战士的维持下,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小将高举着红宝书,用齐声的呐喊控制着混乱的步伐,向火车站的地下甬道拥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蓦地,一抹强烈的不安从姐姐的脸上闪过,她和母亲低声交谈了几句,便鼓足勇气朝那几个负责押送的红卫兵走去。
“同学,我想和你们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为首的那个红卫兵,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
“你们能不能把红卫兵袖标摘下来?”姐姐贸然地说。
“什么?”只见他顿时瞪起眼来:“你还想干什么?”
姐姐连忙向他解释。她把不久前在北京到大连的火车上所见的那悲惨的事情讲给他们听。
“今天的火车上,一定坐满了红卫兵,一旦他们知道我爸妈是被押送的四类分子,谁也说不准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求求你们了,大姐求你们了。”
那几个红卫兵迟疑了。只见他们背过身去低声商量一阵,便当真把胳膊上的红袖标悄悄摘下了。
“上车吧。”说着,他们将两个较沉的行李扛在肩上,我听见姐姐长舒了一口气。
在人性泯灭的那个黑暗的年代,我记住了这几个人性未泯的红卫兵。
送走父母和唐华之后,姐姐回学校了。我独自一人回到了港—十七那间空荡荡的房子。明天,我将返回南尖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这是我在大连的最后一个夜晚。
厨房里的那只铝锅里,还有半锅中午剩下的饺子汤,一个盘子里,还有十几个没吃完的饺子。父亲临行前把其他所有用过的餐具都洗得干干净净,摞在碗橱里。就连那块抹布,也洗好后晾在水龙头旁的橱架上。我再也忍不住,任泪水打湿胸前的衣襟。
有人在敲门,一位我并不熟悉的邻居探进头来:“走了吗?唐主任。”
我点了点头。
“没事吧?孩子。”那大婶盯着我问。
“没事。”
“你?”那大婶不解地。
“我明天早上回庄河办户口。”我说。
“那就早点儿休息吧。唉……”说着,她又转过身来:“晚饭吃了吗?”她关切地问我。
我点了点头。
在人情如纸的那个黑暗的年代,我记住了这个人情似火的邻居大婶。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离开了这座令人心碎的城市。
长途汽车在庄河的大地上蜿蜒行驶,峥嵘的雨云像山一样从天边升起。色彩浓郁的秋天即将过去了。
当天傍晚,朱嘉禾陪我去了木耳山。在山脚下的小场院里,我见到了毛宁。
毛宁和几个妇女一起,坐在金黄色的玉米堆里剥玉米。见我走进场院,她仿佛没太留意。待到我在她身旁坐下,她才和我打了声招呼。
“我明天就要走了。”坐了很长时间,我才鼓足勇气说。
“听说了。”她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
小场院在木耳山的东坡上,从这里可以看见山坡下的那块生产队的菜地,那眼孤独的压水井。
“明天几点走?”毛宁依旧在干活。
“七点。坐小客先到栗子房,然后转车去丹东,沈阳,滦县……”我的心一直在颤抖,我知道,这只是一个不曾开始的爱情故事。
“还能回来吗?”她低着头问我。
我不敢看她,摇了摇头。
“保重……”声音低得像一声叹息。
第二天,当我和嘉禾扛着行李走出石山农场的时候,从兴隆岗开来的小公共汽车,已拖着尘烟出现在木耳山下的大坝前了。
“别跑了,来不及了。”朱嘉禾气喘吁吁地说。
“来得及。它还得拐一个大弯呢。”我不愿意在这里再多呆片刻,因为对于我来说,南尖已经是一块难以言传的伤心之地了。
我们和小公共汽车几乎同时进站。朱嘉禾将行李帮我扔上车时,脸上挂着泪水。
“保重……”
车门关了,汽车开上了村庄后的那座小石桥。一切都将结束了,望着渐渐远去的木耳山,我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
“坐下吧。”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赫然,我发现毛宁就坐在我身旁,她显然是从前站木耳山上的车。
“你?”这一瞬间掀翻了我心里的五味瓶。
毛宁却平静地解释说:“我去栗子房办点事……”
车上的人不多,我坐了下来,紧紧坐在毛宁身边,但彼此却再也没有什么话了。
二十分钟之后,栗子房站到了,她和我一起下了车。在车站旁的一棵高高的白杨树下,我们依旧无话可说。我的心已彻底冻结了,我真希望这一时刻尽快结束。
一辆从庄河开来的长途汽车,拖着滚滚的尘烟出现在栗子房西街的坡路上。毛宁替我搬起了行李。
黄尘与长途汽车一起扑进了车站,分别的时刻终于到了。
“一路保重……”毛宁帮我将行李推上车时,满脸挂着泪水。
一片黄尘遮住了车后的一切。许久,当烟尘消散的时候,我看见远远地,在那棵高高的白杨树下,站着一个粉红色的孤独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