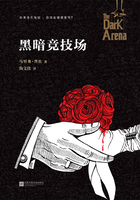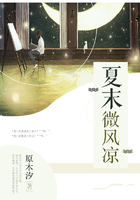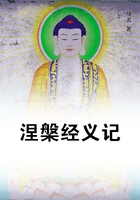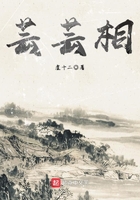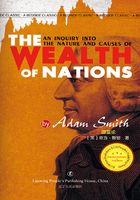当然,在全国经济处于几乎完全瘫痪的状态下,以一个城市行政区的力量解决一百多名学生的工作分配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农村回流城市的本身就已经犯了大忌。为了能争取到留在城里的合法地位,我们曾去省城上访,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
从沈阳上访回来的路上,我们顺便游了趟千山。早春时节,但见一座座被红卫兵洗劫的千年古刹,已成断壁残垣,龙泉寺藏经阁也被掘地三尺,被遗弃的经卷如残雪般飘零在东北第一山的山涧野壑里。放眼望去,心情格外寥落。
从我回大连后,父亲就给祁伯伯写信,求他每月给我寄十元钱生活费。新中国成立后,祁伯伯被调离北京,一直鳏居重庆。父亲与他时常通信,但直到去世,父亲也再没与祁伯伯见过面。
每月十八日,我都会准时接到祁伯伯发自重庆青年路九十四号的十元钱汇款,这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我那时每天中午和晚上,在中山区人委食堂吃饭。早饭就不吃了,只有这样,这十元钱才能勉强维持到下个月祁伯伯发饷。
户口从南尖转回大连后,我因家里已被销户,只能把户口暂时落在朱嘉禾家。朱妈妈为此特别叮嘱我:“千万别跟人家瞎跑,咱们的身份不同其他人,只能低着头过日子。”
春天来了。华灯初上的时候,我常独自一人徜徉在斯大林路这条当年大连最宽阔的大街上。一九五二年秋天,刚刚从码头下船的我们,就是乘一辆古老的四轮马车从这条大街驶过,驶向清爽街二号的。那时车上坐着姥姥、母亲、姐姐、唐宛和我。如今,马车早已不见了,姥姥也去世了,姐姐和唐宛天各一方,而父母和唐华竟然被发配到远在天边的故乡,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
路灯下,身后的影子被拖得很长,我深知自己在这座城市中的位置。望着街道两旁那一扇扇散发出温暖灯光的窗子,我心里充满了难以名状的凄凉,我多么希望身旁能有一个愿意听我倾诉的人。两年无家可归的城市流浪生活,在我内心深处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直到今天,我仍摆脱不了咀嚼孤独的习惯,在阴冷潮湿的季节里,我仍渴望身边有一个愿意听我倾诉的人。
很长时间没见到毛宁了。户口回城后,她很少参加同学们组织的学习,即便偶尔来了,也与几个不爱说话的高中女生远远地躲在角落里。不知为什么,从我回归集体之后,毛宁一直在回避我,两个人即便街头偶遇,也形同陌路。朱嘉禾很奇怪:“你在老家给她写的那封信里,还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吗?”
“没有呀。”
“那她为什么要把那封信交给刘功敏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
“她一定担心有些人胡乱猜想,她想尽量让大家知道,她与你之间是清白的,她是无辜的。”
我知道嘉禾的分析是对的。我知道,在强大的社会现实面前,毛宁胆怯了。
就在这年的春天,初中时代的班主任王玉瑞老师,被暴虐的红卫兵拖上街头。王老师三十年代初在河南老家加入共产党,不久被捕入狱,在狱中,十七岁的王玉瑞与其他被捕的年轻人一起,集体登报脱党,这成了她必须用余生偿还罪孽的铁证。
一九六七年四月下旬,我回了趟唐庄。由于此次还乡自己的身份与上一次不一样了,所以,我始终没有随生产队下地,因为我已经不是唐庄一队的社员了。
“唐浩大叔,你那红卫兵袖标为啥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呀?”立春问我。
“这是因为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所区别。思想兵是极左的一派,我们和他们的观点不一致。”我说。
玉环姨连来了几封信,希望我能去开封住些日子。考虑到我总待在家里影响不好,父亲决定让我到玉环姨家认认亲。因为除了母亲之外,我们家的任何一个人都没见过玉环姨,尽管我们经常通信,尽管我们都知道和子洵叔叔一样,玉环姨是我们最亲的亲人。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黄昏后不久,当我走出开封火车站时,立刻被站前广场上纷乱的人群所震悚。一辆辆满载男女的卡车,在不大的广场上挑衅似的穿行。车上手执棍棒的人们不时拼命呼喊着派系间互相攻击的口号,广场上的人们不时地相互对骂,难分难解,与广场周围小贩豫剧道白一样的叫卖声,三轮车夫粗鲁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中原这片沃土烫得让人窒息。
玉环姨家住在双龙巷九号。推开一扇广亮门楼的大红门,迈过一道高门槛,我走进一处安静的大四合院里。玉环姨和奶奶正在月台上纳凉,玉环姨和我想象中的差异很大,她身材消瘦,嗓音喑哑,一头灰白的短发看上去显得很苍老。对于我的到来,玉环姨惊喜万分。因为对玉环姨来说,我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唯一一个来自娘家的亲戚。
当天晚上,我与玉环姨谈到很晚。奶奶始终安静地坐在一旁为我们添茶。作为玉环姨的婆婆,自从儿子锒铛入狱后,老人便一直与儿媳相依为命。几十年来,风雨同舟,出生入死。在老人和玉环姨身上,你能看到中国节烈妇女最值得尊崇的隐忍与尊严。
表妹马纪平是我到开封第三天请假回家的。高中毕业后,由于家庭出身的关系,纪平表妹无法继续学业,遂于一九六六年自愿报名下乡了。马纪平小我一岁,是一个热情爽朗的姑娘。从她走进双龙巷九号院子的那一刻起,你就会听到她与邻居们热情的对话及率直开朗的笑声。高兴时,这个身材高大的表妹还会认真地清理一下嗓子,用纯正的河南方言为你唱一段豫剧或河南梆子。我从心里钦佩在开封双龙巷九号正房里蜗居的这三位至亲,她们的功德将永远被镌刻在家族的青史上。
双龙巷是开封古城一条很有名的街巷,之所以被称之双龙,实因宋太祖赵匡胤与其弟晋王赵光义皆出生于此。双龙巷长约千米,小街两侧灰砖高墙,门楼庄重气派,尽显宋代达官显贵之气度。每逢雨夜,家家门楼里便会挤满沿街乞讨避雨的流民。乞丐,成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清明上河图》中一道难以忽略的风景。
在开封的日子里,我独自乘火车去了趟兰考。“文化大革命”前夕,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的感人事迹,让兰考一夜出名。我计划去兰考,是因为我自幼就有一种崇拜英雄的情结。玉环姨也希望我去兰考看一看:“那是一个相当贫困的地区,你应该到那里走一走。”
开封火车站的站台上,挤满了陇海铁路沿线农村流向城市的乞丐。时值小满季节,中原一带的小麦开始收获了。从徐州、商丘至兰考一带的地方政府,每年在这个季节,都要派出大批基层干部,深入开封、郑州、洛阳等城市,收容自春节后便一直在城里沿街乞讨的贫苦农民返乡夏收。
一位手持扬声器的中年干部,汗流浃背地大声召唤着要回兰考的乡亲们:“火车进站后,千万不要拥挤,要往后站。大家都不要着急。人全上车后,火车才能开。谁也落不下。”
从洛阳开来的一列慢车缓缓地进站了。在这些地方干部的努力下,流民们在登车的过程中,秩序井然得令人出乎意料。
这几乎是一趟流民专列。每到一个小站,这些地方干部便提前用扬声器大声通报着站名,并扶老携幼地将流民们送下火车。
这是一幕让我终身难以忘怀的情景。只见一位筋疲力尽的地方干部,向依依不舍的流民们大声地劝说着:“夏收了,千万别再出来乱跑了。眼下城里乱得很,咱们都是庄稼人,种地是咱们的本分呀!”
火车重新启动时,站台上的许多流民纷纷转回身来,向送他们回家的地方干部挥手致意。
站在这位可敬的不知名的地方干部身旁,望着他黄瘦的脸庞,我从心里升起一股崇高的敬意。在一九六七年那动荡的岁月里,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地方基层干部,以他们的身体力行努力维护着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与声誉。是一批优秀的人民公仆,是一群忠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开封的日子里,纪平表妹陪我去了龙亭、大相国寺,去了铁塔和禹王台,玉环姨还抽出空来,陪我在一家很有名的饭店吃了黄河大鲤鱼。那些天来玉环姨每天需要去学校参加运动,只有晚饭后她才会抽出时间来与我长谈,玉环姨是个十分坚强的女人,谈起那些让人难以承受的往事,她竟没有落过一次泪,因为玉环姨早已清楚,只有心冷似铁才能应对生活。
一个月后,我离开了开封。十个月之后,玉环姨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开封八中造反派的学生们暴虐摧残了长达一年半之久,那些豆蔻年华的少女,那些风华正茂的少男们用钉了钉子的木棒抽她,直到把木棒抽断。他们把她吊在单杠上,用匕首割她的耳朵,逼着她在大雨中爬行。他们给她上电刑,直到将人彻底击昏。他们逼她喝下一大碗人屎,同时逼她吞下一根蛔虫。他们……罄竹难书!
整整十六个月,玉环姨被他们彻底打聋了,打傻了。这个早就放弃了基督教信仰的玉环姨,在一次电刑之后,竟记起了多少年前自己曾记下的《圣经》中的一句话:“众人都喜爱恶行的时候,恶人就横行无忌了。”(《圣经》诗篇十二至十八)
再次回到大连时已是盛夏。在武汉事件的波及下,早已日渐激化的派性斗争,瞬间便转化成全市规模的武装冲突。一时间,大连三大群众组织纷纷将全市为数不多的高层建筑抢到手里,并建起了戒备森严的武卫点,每个武卫点都有重兵防守并在楼顶安上高音喇叭,开始了从早到晚喋喋不休的对骂。
大凡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于当时无产阶级内部的派性斗争,都会留下深刻的记忆。这记忆最初酷似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的现实主义作品,充满了血与火的激情和剑拔弩张的戏剧性。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记忆幻化成了十九世纪印象派的光影与色彩的主观感受,变成了模糊不定的红黄蓝白的点彩。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推移,这记忆最终定格在集表现派、抽象派、野兽派、立体派及未来派于一体的二十世纪现代派作品之上。充满了非理性和传统束缚的另一种下意识的荒诞。
派性斗争是中国那段非常时期的非常产物。其间充满了后人无法理喻的愚顽、狭隘与冷酷。派性最初起于造反与保皇之争,继而延伸到权力之争,最终延伸到军队介入之后的宠幸之争。
派性斗争的形式最初只局限于不同观点的辩论,像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雅各宾派内部的理论纷争。继而升级到枪林弹雨的“文攻武卫”阶段,又升级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实践阶段。这期间,每次武斗都会出现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即进攻的一方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杀掩过去。而抵抗的一方也会高呼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宁死不屈。双方在下死手的那一瞬间,高呼的最后口号竟惊人地相似:“毛主席万岁!”
八月二十四日,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大连通往旅顺的黄泥川隧道口,遭到另一派的武装伏击,制造了多人伤亡的“八·二四”事件。
几天之后,一门从兵工厂拖出来的山炮,轰击了白山路边的大连卫校武卫点。
南尖农校红卫兵指挥部,在一系列的武装冲突中,观点上发生了变化,但尽管如此,我们依旧坚持文斗,并开始出版了我们自己油印的报纸《向北京》。
应该承认,《向北京》的出版其实只是我的个人行为,因为实事求是地说,这份报纸无论从编辑、撰稿,到插图、排版、印刷,几乎都是我一人所为。我当时为此投入了极大的创作热情,我把每一期报纸都看成是自己文艺创作的实践,报纸质量在当时遮天蔽日的造反小报中间鹤立鸡群。每期出版后,我便和王重铭、刘家仁、葛松远一起拿到商业区的大街上叫卖,挣点小钱后,哥儿几个就到小饭店里大醉一番,酣畅淋漓。
这个时期,酗酒成了我的一大嗜好。和那个年代许多青年人一样,我无法排遣积郁在心底的彷徨与苦闷,在拼命闹“革命”的同时,精神颓废到了极点。一次酩酊大醉之后,我躺在中山区人委楼前的人行道上,任同学拖拉不肯进楼。恍惚中,我看见毛宁裹在几位高中女生中间,从我身边挤过,我顿时心如刀绞。我十分清楚,在这沸腾的城市里,自己只是一个令人鄙视的流浪者。我从心里渴望有人理解我,理解我拼命革命的初衷,理解我流浪中的孤独。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从大连港传来一件令中国人民无法忍受的“反华暴行”,一艘名为“斯维尔斯克号”的苏联货船上的一名船员,公然将一枚毛主席像章吐上唾沫后抛到大海里。消息一经传出,整个城市被激怒了。三派对立的群众组织,一时竟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数不清的各派广播车高呼“打倒勃列日涅夫反华集团”的口号,从全市各地云集海港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