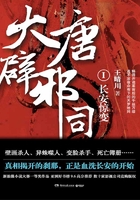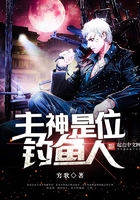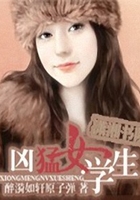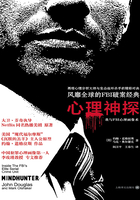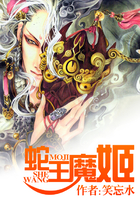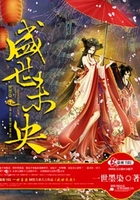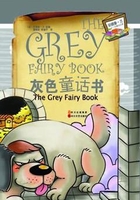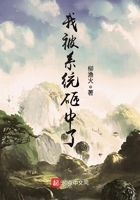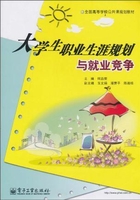当天晚上,在机车俱乐部,在银川市歌舞团巡回演出的现场,在观众暴风雨般的掌声之后,我又听见了久违了的《流浪者之歌》。
一九六九年,费尽周折的朱嘉禾在离开庄河之后,被银川市歌舞团招安,直到一九八三年,朱嘉禾一直行吟在阿拉善荒漠与祁连山之间的这座穆斯林小城。
一九八四年,朱嘉禾终于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干部专修班,与音乐家孟卫东、指挥家郑健、歌唱家关牧村、王秀芬一起完成学业。
一九九一年,朱嘉禾被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特招入伍。二〇〇五年退休前,他已成为一名正军级国家一级作曲家,并享受国家政府津贴。机会终究留给了有准备的人,朱嘉禾实现了自己一生的梦想。
一九八一年夏天,总务科将我调到洗衣房,做了洗衣工。在整日满地肥皂水的洗衣房里,我见了我的师傅老刘和两位能干的大婶。
洗衣房的正中间,是一台庞大的卧式工业洗衣机。每天上午,从各病房科室送来的医护人员的隔离服,住院患者的病号服及各种被服,像山一样分类堆放在洗衣房里。刘师傅开始不紧不慢地工作了。作为洗衣房里最年轻的生力军,我自然要多出一把力。我们将如山的脏衣服,塞进那台工业洗衣机里,刘师傅开始添加洗涤液,之后,电门一推,一片轰鸣声。
那是一台功率很大的工业洗衣机,顶多三锅,成山的衣被便全被它吞噬并洗净了。天气渐渐地暖了,晾在绳子上的雪白的衣被,在阳光耀眼的照射下,散发出像小麦纯熟后飘过的味道,心里一阵阵竟感受到庄稼人收获前的陶醉与满足。
“和小郑过得还行吗?”工作间歇的时候,刘师傅卷上一袋旱烟,坐在阳光下关心地问我。
“还行。”我也点上一根烟。
“人家没嫌弃你?”刘师傅漫不经心地问。
“没。”我说。但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
十五年前,我所在的家庭,在这座城市里,一直拥有自己的位置。而十五年之后的今天,作为一家之主,自己已沦为城市社会的底层。一个医院里的杂役,一个穿着高腰水鞋,每天与大叔大婶们忙着洗衣服的非技术工种的工人。我深知自己当下的境况,我更知道自己对家庭应负担的责任。这一年夏天,在蒸笼一样的简易房里,我开始提笔进入文学创作了。
那是一篇以父亲为背景的短篇小说,一位被红卫兵遣返原籍的老教师,在规劝辍学儿童返校读书的时候,在顽童们提出要他驯服一头公牛的时候,毅然走向死亡的悲壮故事。
小说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太阳偏西了,当洁白松软的河滩即将吸尽他全部血液的时候,唐子清似乎苏醒了,一件褴褛不堪的孩子的小褂,丢在他身边不远的河滩上。四周静得出奇。脑后,从河对岸台地上的小学堂里,隐约飘来了孩子们的读书声:
一加一等二!
二加一等三!
三加一等四……
在钟声的奏鸣下,在孩子们的读书声里,唐子清俯在这温暖的河滩上,终于安静地睡了……
这是一篇用血泪写成的短篇小说,小说的题目是《沙滩上的梦》。
早就读过《海燕》文学月刊,那是一本大连市文联领导下的纯文学杂志。今天,当我推开当年北洋军阀孙传芳的私人官邸的大门,顺着吱吱作响的木楼梯,走上堆满书刊杂志的二楼走廊时,心情既紧张又兴奋。
院子里高大的银杏树,将浓密的树影洒在偌大的房间里。只一位老者,坐在满桌的稿件后面认真地阅读着来稿。
“这儿是《海燕》编辑部吗?”我轻轻地问。
“找谁?”那老者从老花镜的上边望着我。
我走进门来:“我写了一篇稿子,想让老师看看。”我毕恭毕敬地说。
“进来,把门关好。”那老者一直望着我:“坐。”
我坐在了他的对面。
“您贵姓?”我惴惴地问。
“张琳。”他望着我:“稿子带来了吗?”
“带来了。”我从书包里掏出书写工整的手稿:“写得不好。请张老师……”
他接过稿子,认真地翻了两页。
“你来得不巧,近来有一个笔会,编辑们都去组稿了。这里只剩我一个人看家。”说话时,他目光一直盯在稿子上:“你可以先看些书报杂志。这篇稿子不长,我很快就看完了。”说着他站起身来,为我倒了杯水:“你叫……”
“唐浩。”他点了点头,坐下后便一动不动地看起稿来。
张琳,青年时代即被打成右派分子。先后在厂矿和乡村被劳动管制二十多年。落实政策后,方才回城。
我一直在注意张琳的表情,他读得很认真。甚至用一支铅笔轻轻地在稿件上开始批注。我很高兴能碰见这样的老师,我开始有一种成功的预感。
阳光从细高的窗户外渐渐斜去。张琳终于抬起头来。“唐子清是你的父亲?”他问我,眼睛是湿润的。
“是。”我点头回答。
“老人还在吗?”他继续问我。
“不在了。”我回答。
沉默,许久,张琳站起身来:“是不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是。”我点头望着他。
“写吧。”他拍拍我的肩“把想说的话都写出来吧。”
他转身拿起了那份稿子:“这份稿子就留在我这里吧。我是《海燕》杂志社的主编,我希望还能看到你的作品。”
走出南山街十号那座绿阴浓郁的庭院,我被迎面西斜的阳光刺得睁不开双眼。
据说,当天晚上,张琳就赶到那个业余作者创作的笔会上,一进门,他就兴奋地对大家说:“我又发现了一位作者!”
“两年,顶多三年。”当天晚上我就对淑玲发誓:“这个家庭将重新赢得在这座城市中的位置。”
淑玲只沉默地望着我,怀里的呢喃却咯咯地笑了。
之后,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我先后完成了短篇小说《长城冷暖》和《一颗修补的心》的创作,并相继送到张琳老师的手里。张琳老师让一位经验丰富的女老师,做我的责任编辑。石砚老师是个上些年纪的老文化工作者,她和蔼可亲,认真负责。我与她像师生一样无话不谈。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但稿子却迟迟不见发表。我不好意思一再追问,只是每天晚上将蜂窝煤炉子压好后,便披着一条毛毯坐在写字台前埋头创作。
简易房里冷得出奇,后墙上挂满了冰霜。蜂窝煤炉烧红时,那冰霜开始融化,后墙下一片积水的泥地上,甚至长出了几棵耐寒的小草。
一九八一年腊月的一天,接到编辑部的电话,我匆匆赶到南山街十号。
还是在那个编辑部里,张琳表情阴郁地接待了我。
“首先我要自我检讨。”坐下后,张琳将我三篇小说的手稿拿在手里:“是我处理晚了。我原来已经和编辑们商定好了,准备一连三期,将你这三篇小说发表在月刊的头条。目的是推出你这样一位文学新人。但由于稿件压得太多,这一计划迟迟未能实施。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前不久,新上任主持文联工作的吴斌同志,在看过你这三篇作品之后,特意来编辑部了一趟。他告诉我们,近来中央有文件,‘伤痕文学’作品不要再发了。考虑你写的这三篇小说,都是典型的伤痕文学,吴斌同志再三强调,为了保护作者,这三篇只能退稿……”
望着张琳老师那双无奈的眼睛,我接过了稿子。像接到一份癌症确诊证明,我当时恨死了吴斌。
人生的道路就是这样,像初秋的云一样变幻莫测。回到家里,我发誓不再写小说了:“一群胆小怕事的官员,一群鸡蛋里挑骨头的政客!”
淑玲只沉默地望着我,怀里的呢喃却咯咯地笑了。
不久,我和这位从未谋面的吴斌同志成了挚友。再后来,他做过我的电视嘉宾,回忆过他们那一代人经历过的风雨历程。
然而,《海燕》文学月刊社却一刻没有忘记我。这期间,在编辑部组织的与国内知名作家联谊的各种活动中,我先后与包括冯牧、丁玲、姚雪垠、李陀、陈建功、茹志鹃、王安忆、张抗抗、李国文等在内的二十几位作家进行了讨论与交流。并与以邓刚、素素、杨道立、孙慧芬为首的大连作家群结成了紧密的联系。我先后参加了多次大连业余作家的笔会,但作品却一直写不出来。
一九八二年春天,因肠道不适,小呢喃住院了。在儿童医院二一八号病房,我与同室的另三位孩子的父母相处了四天。
出院结账时,我问淑玲花了多少钱,淑玲点了点收据:“二十七块五。”
“没关系,这笔钱我很快就挣回来了。”我很有把握地说。
这一年七月《海燕》杂志刊登了我的处女作《二一八病房》。这篇小说不仅为我赢得了九十二元稿费,而且被评为当年《海燕》杂志优秀短篇小说。从此,我正式踏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而我的本职工作,也由一名杂役工,升为结核医院的伙食采购员。
我刚升任食堂采购员的第一天就遇到了麻烦。
那天清晨,我换了一套灰色的涤卡制服,趁天还未亮,就赶到位于泉涌街的蔬菜团购供应点。初夏的小街上行人寥落,淡淡的晨雾中,十几个附近单位的伙食采购员渐渐汇集在了一起。由于是刚入道儿,我和他们并不熟悉,所以我开始故作谦恭地与他们搭讪。很快,我就认识了其中的辽宁师范学院的采购员,一个虎背熊腰的东北汉子。大连铁道学院的采购员,一个戴深度眼镜的刀削脸。大连汽修厂的采购员,一个身材瘦小的瘸子。我求各方老大多多关照,大家勾肩搭背好不仗义。
突然,小街深处传来一声鞭响。霎时,聚在一起的人们像同时听到了总攻的信号,轰地一下便朝菜车奔去,那场面活像一群狮子扑向一头受伤的角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