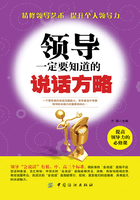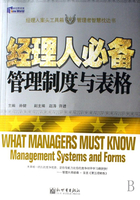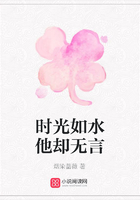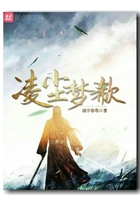孔祥熙继承了山西人天生就会经商的才干,在一战期间,他将山西所产铁矿砂出口到了美国,从中大获其利。他还创建了裕华票号,并对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进行了投资。1928年3月,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的工商部长。
与宋子文和蒋介石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不同,孔祥熙是死心塌地追随蒋介石的。当初蒋介石向宋美龄苦苦求婚之时,宋庆龄和宋子文曾表示过反对,只有他在一力撮合。在蒋介石被孙科等人逼迫下野之后,孔祥熙也宣布辞去工商部长职务,以此来表示与蒋介石共进退,于是深得蒋介石的欢心。
随着蒋介石的再一次掌权,孔祥熙迎来了他人生的辉煌时期。1933年4月,孔祥熙便被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随后又出任了行政院副院长以及财政部长两个要职。由此开始,中国的财政金融大权被他控制长达11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成了全中国的新贵。
孔祥熙在中国经济史上曾经做出过一次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举动,那便是将中国金融业的民营传统掐断了。在1935年之前,私人银行家们一直牢牢掌握着中国金融业的主动权。国民政府直接控股的银行不过是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两家,总资产在全国银行总资产仅占11.7%,剩下的资产之中九成以上集中在上海银行同业公会的成员手中,其中,实力最为雄厚的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它们的资产占到全国银行总资本的三分之一以上,比中央银行规模的三倍还要多,虽然政府在这两家银行中各有20%的股份,但是经营权仍然被私股掌握。而张公权作为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大股东,成了银行业的魁首。
1935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爆发产业危机,此时的形势异常严峻。就在这时孔祥熙发挥他的合纵连横之术,对中国银行进行了突袭,于是一场孔张之役就此展开。他深知一己之力难以击倒张公权,于是便暗中联合宋子文和杜月笙。
1935年2月13日,杜月笙邀请上海实业界和金融界的大佬们开会商议应对经济危机的策略。会上,孔祥熙作为政府代表抛出一个建议,他建议将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以及中国银行组成一个“三行小组”,对此时已经陷入绝境的上海企业界给予“尽可能的贷款援助”。这个议题立刻得到实业家们的欢迎,他们非常认同孔祥熙的这个建议,杜月笙等更是从旁推波助澜。面对这一局面,张公权并不知道孔祥熙到底要做什么。于是张公权便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贷款可以,但必须对细节进行讨论,并且所筹集到的资金必须全部贷给工厂。孔祥熙当场一口答应。
半个月之后,金融界与实业界再度举行会议,还是由杜月笙主持,不过这次孔祥熙并没有出席,而是通过《申报》发表倡议成立“三行小组”。与此同时,宋子文也利用自己在上海金融界的影响力频繁活动,还策动一些中小工厂主成立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对银行家集团形成了强大压力。由此一来,上海的企业家们被撕裂成了金融与实业两个阵营,一时间孔祥熙成为了上海经济复苏的“大救星”。随后,3月9日,各方人士在孔祥熙的主持下进行第三次会议,会上决定,以中国银行为首组成援助财团,向实业界提供500万元无抵押贷款和一亿元抵押贷款。3月20日,孔祥熙向中央委员会正式提交议案,以海关税为保证发行一亿元的公债,张公权、陈光甫等人还提出,此公债必须用于援助实业界,张公权还迅速就贷款的相关细节事宜进行具体安排。可是,孔祥熙接下来的转变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当一亿元公债被确定之后,1935年3月23日,孔祥熙宣布了一个让众人瞠目结舌的决定:出于管制的需要,政府要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增发它们的股票,一亿元的公债将不再贷给工商业者,而是要用来购买两行的股票。对此,孔祥熙给出了这样的理由:通过政府购买两行股票可以增加两家银行的信贷能力,从而更好地克服经济萧条所造成的困难。同时他还以财政部的名义,指定3000万元用作增加中央银行的资本,2500万元用于购买中国银行的股票,1000万元用于购买交通银行的股票,剩下的3500万元作为弥补政府的欠债,对于工商业界的直接救济贷款则一分没有。
由于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股本便是2500万元和1000万元,孔祥熙的这个计划使得政府成了两家银行的绝对控股大股东。与此同时,孔祥熙直接将张公权的总经理职务免去,由宋子文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之职。面对这样的局面,张公权也曾经让人给蒋介石带话说,如果这么干,中国银行的钞票将会一钱不值,但是蒋介石却置若罔闻。至此,在这场毫无悬念的孔张之役之中,孔祥熙以绝对的实力将张公权赶下了台。
在撤掉张公权职务的一个月之后,交通银行对董事会进行了改选,孔祥熙又如法炮制将交通银行纳入官家之手。
在此之后,孔祥熙继续鏖战。在当时的上海金融界之中,除了两大银行之外,他还拿下了中国实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三家实力比较强大的民营资本银行。相对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他拿下这三家银行的手法简单了许多,在随后的三个月里,他大量囤积三家银行的通货,然后一下子拿出来兑现,从而使得原本就已经陷入困境的三行束手就擒。半年之内,孔祥熙利用经济危机一举收编上海五大民营银行,张公权等人已经是溃不成军。中国金融格局陡然乾坤逆转,国营资本在全国银行中的资产比例猛增到72.8%。10月,上海银行同业公会改选,杜月笙、宋子良等人被选为理事,职业银行家手中的领导权被彻底剥夺,公会沦为政府的一个附庸。
可以说,孔张之役具有非常重要的标志性意义,作为当时国营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一次大决战,国民政府的决定性胜利标志着国民政府已经将金融业收入囊中,自由经济之脉从此断绝。
投机的官商:大肆敛财的孔宋家族
孔宋家族作为民国时期地位显赫的家族,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便开始疯狂的敛财。那么孔宋家族是如何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增加自己资本的呢?
在金融业方面,孔祥熙长期担任国民党的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等要职,从而使得孔氏能够直接控制四大银行,同时还设立了邮政储金汇业局以及中央信托局,进而形成了四行两局的金融管理格局。为了方便自己敛财,孔祥熙打着孔氏家族的旗号先后创办、接收了中国国货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山西裕华银行、庆记商行、祥记商行等大小金融机构,在1942年7月,国民党政府发布规定称全国的货币发行都要集中统一于中央银行。由此一来便进一步加强了孔宋家族资本在全国金融行业之中的垄断地位。到了抗战开始时四大银行的存款数额比原来增加了六倍还要多,是各大银行之中增长速度最快的。在全部银行存款中,四行的存款占到了百分之八十甚至是九十,而1936年只占百分之五十九。而毫无疑问,这四行的控制权是完全掌控在孔宋家族手中的。
孔宋家族的资本在商业方面形成了公开的垄断。贸易委员会、专卖事业管理局、物资局等机构的成立及专卖、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是孔宋资本实现商业垄断的重大步骤。除此之外,原属孔家系统的农本局福生庄,后改组为花纱布管制局,统制花纱布的贸易。作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组成部分,孔宋家族假借抗战的名义,利用投机活动开始垄断了中国的对内以及对外的所有贸易往来。孔宋家族还以私人名义成立了不少商业公司。著名的有:孔家的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宋家的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兴业公司等等。这类公司既有政治特权,又有极大的金融势力,具有操纵市场的垄断地位。它们帮助孔宋家族实现了资本的超额积累,在孔宋家族的敛财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孔宋家族对于工矿业的垄断在抗战前还较小,1935年底全国官营、民营工厂资本总额中,官营部分只占百分之十一。随后设立了工矿调整委员会,对官营工业做进一步的扩张,开始吞并民营工业,实行国家垄断工矿业的机构。孔宋家族的官营工业主要隶属于军政部兵工署和资源委员会两大直属系统。孔宋家族除官营工业外,还有商办形式的私营工业。
在农村,孔宋家族是最大的高利贷主。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农民的借款来源之中,受孔宋家族直接间接操纵的银行、合作社、合作金库所占比重在逐年升高,最高时曾经达到所占比重的一半还要多。1937年9月,国民党政府设置了农产调整委员会,作为控制和垄断农业生产的机构。抗战时期蚕丝、猪鬃、棉花、茶叶、桐油等由国民党政府统购统销,这进一步方便了孔宋家族对贸易的控制。在征购征借的措施下,大量的粮食纳入孔宋家族直接掌握之中。此外,孔宋家族还直接占有大量农村土地。
通过对城市的工商业以及农村的信贷业的垄断,孔氏家族和宋氏家族在抗战之前便聚集起了超乎想象的巨额财富,这些通过投机活动和行政权力取得的财富为保住孔宋家族的显赫地位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其在中国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孔宋家族在抗战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积累如此巨大的财富令人惊讶,这也确实和他们手中掌握着的权力有非常大的关系。孔宋家族通过投机活动的敛财行为也确实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同时也促进了国民党政府的倒台,民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将国家当成自己的后花园来为个人牟取巨额利益却又不注意维护,这样的国民政府倒台是迟早的事情,这也是历史给后人的沉痛教训,值得后人时刻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