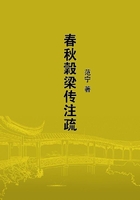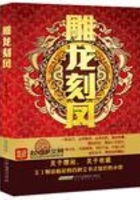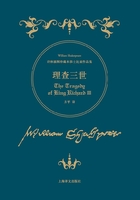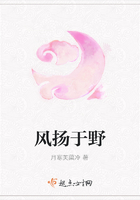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接触到西方音乐,在小提琴上把中国革命歌曲拉出欧洲小夜曲的味道。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与老木、大头等人下乡前偷袭了一次学校围墙那边的省社科院图书馆,在天花板上挖洞,下面果然是满地堆成米多高的书海。我们跳入软软的书海里,凭着中学生的眼光,在这些临时封存的书堆里胡乱寻找,见形容词华丽的就要,见爱情故事和警匪故事就要,最后在书海里拉了一泡尿,各种书刊塞满了两个大麻袋。其中有古典名著也有青春格言和卫生指导一类手册,当然还有我们满世界寻找的乐谱。对于当时很多青年来说,异端与正统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唯有好听的异端和正统,与不好听的异端和正统,才构成差别。所谓政治限制,还有对付这种政治限制,仅仅是文字性的区区小事,与忠字舞的感官愉悦没有太大关系。大队党支部书记四满带着民兵来检查时,看到歌本,只瞪大眼睛检查歌词,对舒曼练习曲一类看也不看,而《外国民歌两百首》这一类书上,只要有“大毒草仅供批判”,还有重重的惊叹号,也就被他们放过。倒是我日记本里的一句话被他们大惊小怪:“我想随着列宾的步伐漫游俄罗斯大地”,是我随意写下来的,无非是用点酸词来赞扬列宾的油画。四满书记是读了书的人,知道俄罗斯就是苏联,就是修正主义,拍着桌子大骂:“你好不老实,还有一个人没有交代出来!”
“我真的什么都交代了。”
“硬要我点破是吧?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
“我能说的都说了,真的没有了。”
“还有一个姓列的,是什么家伙?”
这句话被他憋了三天,总算说出来了,但我不明白他说什么。
“你们还想一起偷越国境投靠苏修?这瞒得了谁?”
我更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他把我的日记本甩在我面前,铁证在此,看我如何狡辩。我这才哭笑不得地解释列宾何许人也。他听了好一阵,半信半疑,丢下我去猪场看饲料发酵去了。
俄国歌曲
俄国歌曲有中欧音乐的高贵,却多了一些沉重;有印度和中亚音乐的忧伤,还有中国西北音乐的悲怆,但多了一些承担和前进的力量。这种歌曲属于草原或者雪原,属于牧民的篝火,不适宜在宫殿里唱,不适宜在集市里唱,更不可以像爵士乐那样拿去酒吧助兴,是一种最为贴近土地和夜晚的歌曲。
黎明或者黄昏的时候,在霞光和火光相接的时候,一种声音若明若暗地波动。此时你从被子里探出脑袋,发现床前有瓦缝里飘入的积雪,窗前也有窗缝里飘入的积雪,而遮窗的塑料薄膜被狂风鼓得哗啦啦响个不停,透出了外面一片耀眼的洁白,天地莫辨。在这个热被窝难舍的时候,不知是从什么地方,开始有了一两个音符的颤动,然后像一条小溪越流越宽广,最后形成了大河的浩荡奔涌,形成了所有工棚里不约而同的大合唱。《三套车》,《小路》,《茫茫大草原》,人们此时不可能唱别的什么。
每一种歌曲都有它最宜生长的地方和时机,俄国歌曲就是知青们在风雪中的歌曲,甚至成了一代人永远的听觉标志。只要你听到它,听出了歌声里的情不自禁,你就可以判断歌者内心中的积雪、土地、泥泞、火光、疲乏、粗糙的手以及草木的气息。有一次,我在火车上认错了一个人,呀呀呀地大声招呼和紧紧握手之后,发现了对方脸上的陌生,发现对方也从呀呀呀中清醒了过来,目光中有搜索记忆的艰难,还有最后的茫然。到这个时候,我们都意识到进退两难,而且无勇气承认这种荒唐,于是有话没话地敷衍,但愿能敷衍出必要三言两语之后,再想办法从尴尬中体面脱身。幸好我们是在车上相遇的,幸好对方这一铺组刚才有人唱起《伏尔加船夫曲》,这就有个近便的话题。
我镇定下来了,避开人名一类可以露馅的东西,试探着谈俄罗斯歌曲,谈插队岁月一晃就过去了这么多年,谈当时早上起床时的浑身疼痛,夜晚远行时的边走边眠,抓捕野鸡时的激动不已……当然也谈到当时对乡下的厌恶和眼下对乡下的怀念。我后来发现自己其实过于谨慎了。对方居然有话必接,竟与我越谈越近,虽然是张冠李戴却也珠联璧合,没有什么不合适。当他谈到猪场里的种猪凶得将他咬过一口时,我差一点觉得他肯定就在当年的太平墟公社干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知情者,而不是被我错认的什么陌路人——因为凶悍种猪同样在我的记忆里呲牙裂嘴嗷嗷乱叫。
我们哈哈大笑,全身轻松,意犹未尽,没有料到可以谈得这么久,可以谈得这么投机和会心。以至我告别离去以后,我一直怀疑自己真认错了人——尽管我确实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他是一个陌生的老熟人,只是不叫“老周”。他后来也不叫我姚什么,一直对我的姓名含含糊糊。
《红太阳》
数年前一种名为《红太阳》的系列歌碟在中国内地突然畅销,响彻某些歌厅、出租车以及中老年人聚会的场所,其中收录了很多文化革命中的歌曲,让人联想到当年的“忠字舞”。知识界对此做出了敏感的反应。有些左翼人士的解释是:人民大众对贫富日益分化的现实深感失望,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强烈不满,所以唱出了对毛泽东及其革命时代的怀念。有些右翼人士则在报刊上深深忧虑或拍案而起,指此为极“左”思想回潮的铁证,是一种极端势力企图对抗改革开放的危险讯号。有一些西方观察家甚至断言:这是中国执政当局在“89政治风波”以后强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阴谋。
这些反应其实都是一些书呆子的反应,都是一眼就盯住了歌词并且努力研究歌词的反应——他们一肚子文墨当然擅长这种手艺,正像他们经常操着同一种手艺去历史文献中寻找历史,去政治文献中寻找政治,去道德文献中寻找道德,目光从不能探出文词之外。其实,我所认识的很多人在唱歌时对歌词基本上不上心。老木就是其中一个。他早已移居香港,成了个房地产大老板,经常带着一些风水先生、职业打手或者副省长的女婿去夜总会,把一长溜陪坐小姐叫进包厢来挑鼻子挑眼,又动手动脚要领班妈咪亲自献身服务,总之要在风尘女子面前把威风耍足。他打开了千多元一瓶的XO以后,最爱唱的卡拉OK就是俄国的《三套车》、美国的《老人河》、还有《红太阳》里那些革命歌曲,诸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或者“铁道兵志在四方”。
三陪小姐不会唱这些歌,也不觉得这些歌有什么意思,通常会给他推荐走红的港台歌碟,有一次竟惹得他勃然大怒。他踢翻了茶几,把几张钞票狠狠摔向对方的面孔,“叫你唱你就唱,都给老子唱十遍《大海航行靠舵手》!”
他是在怀念革命的时代吗?他提起自己十七岁下乡插队的经历就咬牙切齿。他是在配合当局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灌输吗?他怀里揣着好几个国家的护照,随时准备在房地产骗局败露之后就逃之夭夭。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对往日革命歌曲的爱好何来?关心《红太阳》的读书人们该如何解释他唱歌时的兴奋、满足乃至热泪闪烁?
作为他的一个老同学,我知道那些歌曲能够让他重温自己的青春,虽然是残破却是不能再更改的青春——他的天真,他的初恋、他的母亲或者兄弟,他最初的才华和最初的劳苦,还有他在乡下修水利工程时炸瞎了一只眼睛,都与这些红色歌曲紧密联系在一起,无法从中剥离。他需要这些歌,就像需要一些情感的遗物,在自己心身疲惫的时候,拿到昏黄的灯光下来清点和抚摸一番,引出自己一声感叹或一珠泪光。他不会在乎这些遗物留有何种政治烙印。他甚至曾经告诉过我:他十三岁时看到的第一张“色情”照片是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剧照。他当时没法压抑自己的冲动,几次解开裤子,偷偷对着画报封面上的红军女战士自慰。在那一刻,他不会在意那个剧目是不是革命宣传。
在我看来,像独眼龙老木这样的人,其实是九十年代以来《红太阳》歌碟最主要的消费者。他们肯定不知道,自己为何被左翼的读书人高兴了那么久,又被右翼的读书人痛恨了那么久。
富特文格勒
我在编辑《天涯》杂志的时候发表过一篇文章。文章谈到1948年芝加哥乐团邀请当代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富特文格勒担任指挥,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在抗议的传单上,印着另一位意大利伟大指挥家托斯卡尼尼的话:“只要在纳粹德国演奏过的人,就无权演奏贝多芬。(见单世联《演奏贝多芬的权利》)”
富特文格勒因此而未成行,演奏贝多芬的权利也就成了一个长久的话题。
为纳粹德国效力过的音乐家当然不止他一人。大师级的理查.斯特劳斯,还有后来名震全球的卡拉扬等等,也有类似的历史污点。他们曾出任纳粹的音乐总监或地区音乐总监,甚至用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为希特勒庆寿。凡是受到过纳粹德国伤害的人,凡是珍惜人类生命的人,都有权谴责他们在政治上的这种怯懦。就像中国众多感时忧国之士曾经有权痛惜“戏子无义”式的现象。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语)”演艺圈里有人不悯国事,不守义节,其所占圈内人数的比例,可能既不会多于其它行业,也不会少于其它行业,只是他们社会知名度较高,更容易引人注目。文化革命系列歌碟《红太阳》在九十年代的重新流行,其政治原义大失,更使我相信演艺作品以声色内容为主,而以文字内容为次,与义节的关系,不似文字作品那么直接和紧密。演艺是多种表达方式的合成,具有特别的多象性和多义性,既在国事之内,更在国事之外,一时的神思恍惚,更可能使演艺人员在声色的梦幻中迷失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富特文格勒等诚然是可悲的失足者,但他们为纳粹演奏时闪烁的泪花并不一定都是为希特勒而流,泪花中我们所不知道的一切,我们所难以洞察的心弦颤动和忆绪暗涌,也许藏有诸多未解之义。
声色之义难解,演艺人员大多又不擅文墨,很难用文字将他们在声色世界里的感受表达出来,从而进入报刊评论和我们的分析。
乡戏
第一次在乡下看戏让我有些吃惊。禾场里用几张门板架起了一个戏台,台上光线暗淡,有一盏汽灯,还有两、三盏长嘴油壶灯,都靠草绳从台顶吊下来,冒出滚滚的黑烟。台上两个演员是若隐若现的鬼影,其中一个正旋着一把什么油布伞,与另一个肩并肩高抬腿原地大跳,大概是作爬山涉水态,直跳得脚下的门板吱吱有声和摇摇晃晃。伞旋得越来越快了,激起台下一阵叫好。后来我才知道,这里正在演出一个打土匪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我不记得这出戏有革命战士打伞的情节,大概是某演员有快速旋伞的绝活,不旋给乡亲们看看是不行的,剧中的解放军就只好旋着伞上山剿匪了。
农民剧团买不起布景和道具,一切只能因陋就简,蓑衣代替了斗篷,草绳代替了皮带,晒垫上涂些黄泥墨汁就是山水远景。又因为没有剧本,便由一个略知剧情的小学老师说说大体梗概,演员们即便是文盲,也可记住以后上场自编自演,随编随演,即兴发挥。这叫演“乔仔戏”,是否就是最早见录于汉代典籍里的“乔”,不得而知。
台下一片黑压压的人头,但真在看伞的也不多。娃娃们在人缝中钻来挤出兴奋不已,经常发出追逐的叫喊或摔痛了的嚎哭。后生们也忙着,不时射出一道道手电筒的光束,照到不远处的少女堆里,照在某一张脸上或某一个屁股上,于是招来破口大骂,是“三狗子你照你娘呵”一类,引得少女们开心大笑,挨骂的后生们也浪浪地乐不可支。中年妇女们则三五成群说着媳妇生娃或者鸡婆下蛋之类的家务,或者在给孩子喂奶,给孩子抽尿抽屎。相对来说,只有老汉们才端坐得庄严一些,孤独一些,对剧情和台词也较为关切,伞能旋出这样的水平,得到他们的啧啧称赞。他们没有我的吃惊,已经习惯了台上的狭小和混乱,比如打鼓佬和胡琴手说是坐在台侧,其实已经逼近了台中央,都混到演员中来了;比方正是剧中战事激烈之时,突然有人跨过尸体悠悠然走到台前,不是新角色出场,也不是报幕员有事相告,而是一个村干部来给渐渐暗下去汽灯加气,加完气再猛吹哨子,大吼一番,警告娃娃们不得爬上台来捣乱。
我差一点误会这也是剧中的情节。
我不大可能看明白剧情,相信大多数观众也把剧情看得七零八落,甚至觉得他们压根就不在乎这一点。他们没打算来看戏,只是把看戏作为一个借口,纷纷扛着椅子来过一个民间节日,来参与这么热闹的一次大社交,缓解一下自己声色感觉的饥渴。在乡下偏僻而宁静的日子里,能一下看到这么多的人面,听到这么多的人声,嗅到这么多的人气,已经是他们巨大的欢乐。何况还有台上的闹腾,有伞在飞快地旋转,有举枪时的炮竹炸响和硫磺味,有一溜披戴蓑衣的人在翻斤斗,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戏装——有位村干部曾大为不满地对我说:去年给剧团制了六件红衣服,花了队上两担谷呵,他们这次居然没有穿出来,王麻子他搞什么鬼么!
革命样板戏当然是含有意识形态的,但那些意识形态同这样的观众有什么关系吗?有多大的关系?同样的道理,革命样板戏所宣称要打倒的那些旧时代文艺,那些以前也在这里上演过的剧目,同这些观众有没有关系或者有多大的关系?在这样一个乱轰轰热腾腾的戏场里,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不可接受而且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不可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