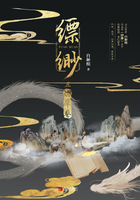血。热乎乎的血,顺着吴技术员的破毛衣袖子向桌子上流了一摊。一定是热的,章柿想,刚流出来的,从喉管里“咕嘟咕嘟”冒着泡泡流出来,好像还有热气往上飘。血源源不断从喉管里向外涌,顺着他的毛衣、裤子,流到地上。他的右手里拿着个刀片,男人刮胡子用钝了的刀片。用它刮胡子,只会把脸刮得生疼却刮不掉胡子,双手修长美好的吴技术员却用它割破了自己的喉管。
章节高媳妇骂的多是跟她差不多年纪的女人,只要她看到章节高跟谁说话,就指着那女人的脸骂人家破鞋货,狐狸精。当胡爱花扛着锄头路过她家门口的时候,她的咒骂突然就像河水决口般地敞开。胡爱花装作没带耳朵,径直向西走去。章节高媳妇追出自家院门,向着她的背影,像打架的孩子般想用嘴里飞出的石子撵上她,最好是一下敲到她的头上流血才解气。胡爱花走得更快,想把那身后的骂声远远地甩开。她一声不吭,下到地里只管低头锄地。这女人快把生产队里的妇女骂遍了,我犯不着跟她对骂,我也骂不过她。婆婆说了,绣花鞋不踩臭狗屎,婆婆还说,啥贵不吃啥,谁烈不惹她,我躲她几天,看她还能咋?
胡爱花上工下工,不再走街里,也不路过她家门口。
那女人不知啥时从县医院开来一张有精神病的证明,交到生产队,就可以常年不上工,拿着低工分,只在家里一天做三顿饭,干少量家务活,捂得白白胖胖。她的大闺女安玲的性子一点都不像她,在村上见人不笑不喊不搭腔,这天专门在地里锄着地就来到胡爱花身边,亲亲热热地喊:“婶儿,我妈有病,见天在家把我们姊妹们也是挨个撅哩,一点法儿都没有,你别跟她一般见识。”胡爱花脸上怪不自然地说:“我不往心里去。”
咋可能不往心里去,见天被人指着追着骂,咋说都是叫人恼火的事。直到有一天,那女人在街里大声喊着西芳跟章节高长得像,不信大家都来看看。本是要出工的胡爱花扛着锄扭身往家里走,把锄扔到院子里,钻到东屋再也不出来。
季瓷来到大队办公的院子,大声喊:“节高,你出来。”
章节高从屋里出来,叫声“婶儿”,装着啥事都没有发生。
“你等着看着她把俺家胡大姐气死不中?谁不知胡大姐几个孩子都是秋天里生,她再不精细也得知这个理吧,她这样没窟窿犯蛆,我今儿不依了,你看这事咋弄吧。”
季瓷在村里很少与人争执,可这回她既然挑开了这事,那就不能轻易了结:“俺家可不是没人,是人不在家,俺那楝要是愿意趴叉到家里,想在大队或者公社跟谁争抢,想叫俺全家不受人欺没,不是办不到的。如今这事你要是管不了,我就一时三刻翻电报叫柿和楝回来。你可知胡大姐娘家有几个兄弟吧,在沙河上班的上班,在商桥工作的工作,最小的是给牲口看病的,骟猪骟驴一把好手,反正没一个孬种。你也知俺娘家有个从小在土匪窝里长大的侄哩吧,脾气赖得没人降得住,三天两头集上惹事,二里地,他抬抬脚就蹿来了,你信不……”
“信,信,婶儿,别说了,我知了。”章节高转身出了大队办公的院子,回到自己家。立时,从他家院里传来女人凄厉的哭号声,一下子震惊了整个村庄。天爷呀,谁敢把这女人惹下?当人们真的搞清是大队书记教训他那没人敢惹的婆娘时,都聚集在街里远远地看着他家院门,也就看到了季瓷穿戴整齐地从大队院子里走出来,她走得有点款款信步的样子,脚脖上的绑腿打得紧紧的。见了人不像平常那么说笑,而是阴沉着脸,拿着那么几分,走到自家门口的时候,不往家里去,站下来向西瞄。
章节高其实也没有打自己媳妇多狠,他只是比画一下罢了。他在这村上不怯谁,可多少怯着章守信一家。也不是怯他们,是不想惹他们。章守信年轻时候脾气孬,那年刚记事他说过章柿带肚儿,章守信跑到自家门口,叫着自己爹的名儿跳着脚骂仗,爹愣是没敢出门。现在这事,或许是他章守信想着这是女人又是晚辈的事不便于管,要是他真的豁出去耍一回老二杆子,冲到俺家院里把俺媳妇揪住头发扯到街里打一顿,你还真拿他没法,或者他们叫娘家那些二货们来闹一场,那还不胜我自己打几下算了。
他拍拍手从自家院里出来,路过章守信家门口,见季瓷还站在那儿,他摊开双手:“咦,婶儿,你看看,手都打疼了,狠狠给了她几耳巴。中了吧,恁消消气,别跟她一般见识,她这,有毛病。”他指指自己的头。
“我也没想叫你打她,她有病,挨你一顿也怪可怜的,只要她今后不撅人就中,谁都不要撅,撅人折自己寿哩。”
章节高已经走了,他很忙,有许多革命工作等着他去干,季瓷后面的话是冲着他背影说的。
他家院子里的哭号并没有停,不但没有停,还更大更烈,好像是那女人的病发作了。有几个胆大的蹭进院子一看,大呼不好,唉哟,要上吊哩。几个人冲进屋,手忙脚乱把正在往房梁上搭绳的白胖子救下来,她还是又哭又闹,跳来跳去,好像中了邪气。有人从地里喊回她大闺女,安玲跑回来把她安顿住,眼看快晌午了,就生火做饭,嘴里说当妈的不是。白胖子在床上躺着,一会儿“呜呜”地哭,一会儿又“咯咯”地笑。安玲说:“妈,你以后别再撅人了,弄得俺姊妹们在庄里不好做人。你说俺柿婶,恁老实个人,她咋惹你了,你真是的,吃了饭我引你去给赔个不是,中不中啊?”
白胖子在床上“咯咯咯”笑,阴阳怪气的:“叫我给她赔不是,中啊,叫她来吧,她来给我跪下,喊我一声姑奶奶,我给她赔不是……”声音轻下去,“呼噜呼噜”睡着了。安玲做好了晌午饭,叫她起来吃,她扭来扭去在床上不起来。晌午饭后,安玲给手巾里包了几个鸡蛋,叫上他兄弟安金来到季瓷家里,坐着说了好一会儿的话,替她妈赔不是。季瓷连说妥了妥了,这事过去了,难得她有你们这么懂事的孩子。
夜里,季瓷给胡爱花说:“我约莫着,咱这样不中,柿在西安打着光棍,你在家里受人欺没,两头不划算。你们年轻,老是分着,不是个长事。你找柿去吧,把孩子搁家里,我给你带着。”
胡爱花腾地红了脸:“再等等吧,北京快生了,啥活都干不成,我一走,这家里一摊子咋弄?”
“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一走就了了,有我在家里撑着。”
罗北京人没进门,肚子先进来了:“嫂,你去吧,家里有我哩,我能在家干点轻活,支应爹娘,你去找俺哥吧,省得在家受这气。”罗北京手指头抠着门框,低下了头。她从小在富足与疼爱中长大,没为啥事作过难,操过心,脸皮就分外地薄,现在又算是新媳妇,一来就怀上,没有太去上工,村里人也认不全,她愿意躲在家里,整天洗洗涮涮手脚不停地忙。不干不中啊,婆婆见不得哪没收拾好,在身后不停地指派。她不怕出力不怕累,可她总是想不到这世上还有那么多需要动脑筋的事,还有那么多人要恶语相向,大家和和气气相处不中吗?
胡爱花说:“不中,我放不下你们,要不这样的吧,柿回来过完年我再跟他去,这样能等北京生了,慢慢出门挣工分。”
也是刚过完八月十五,罗北京生下个男孩儿。胡爱花爱得不行,憨着一张笑脸跑前跑后地忙着。
罗贫农走起路来腿脚不太灵便了,他来到院子里的时候,先是大着声给自己解释:“嘿,北乡赶会哩,走到这儿使得慌,歇歇,寻口茶喝,总是中吧?”他自己也觉着怪不好意思的。孙女生孩子还没出满月,他不请自来,他从前是不会做出这样不合身份的事的,可是,唉,人老了可不就没成色了,常常把握不住自己,变得像小孩一样,人家笑话也就笑话吧,我真的是去北乡赶会哩,咋走到他们村头,不由得就拐进来了。
“太中了太中了!”章守信大声搭腔,赶快从堂屋迎了出来。罗贫农执意不进屋,两人就在院里坐下。胡爱花钻进灶火烧鸡蛋茶去了。季瓷不在家,可能到谁家还啥家什或借啥东西去了。
罗北京在堂屋的西间住着,她爷和公公就坐在她窗外的枣树下,罗贫农隔着窗问孙女,小孩胖不胖?闹人不闹?罗北京给爷爷一样样说着。可能是大人说话惊醒了小孩,“吱吱啦啦”哭了两声,罗贫农喜得龇了牙。
“叔,你给小孩起个名吧。”章守信说。
“咦,不中不中,得你这当爷的起哩,轮不到旁人起,我算哪一角儿呀?就这,不到时候就跑来,够没成色的啦。”
“叔,‘四旧’都破完了,哪还那么多说辞哩。”章守信说着话,胡爱花端出了鸡蛋茶,里面卧着六个荷包蛋。“咦,这哪吃得完呀,不中不中,吃俩就饱了,拿个碗拨出来吧。”罗贫农说着要去灶火拿碗,章守信起身相拦:“吃吧吃吧,吃不了剩碗里,我吃。”这样一说,也就是逼着人吃完六个鸡蛋。罗北京在窗子里说:“爷,提劲吃啊,吃饱了去赶会,还有那么远的路走哩。”说着话,季瓷也回来了,进灶火把墩搬到门口,远远地坐着说话。
眼看他吃完四个鸡蛋,说再也吃不下了,双方又推让一番,胡爱花接了碗端回灶火,进自己东屋做活去,不再出来。
章守信又说叫罗贫农起名的事,季瓷也随声说:“是啊叔,你就给起吧,北京说,从小就数你最亲她,你这个老姥爷起吧。”
“那,你看,你家大孙子叫西平,因为他爸爸在西安,那这二孙子,我看就叫津平吧。”其实,他这个老姥爷来的路上就想好了,却没想到章家真是实心叫他起名。
罗北京躺在窗子里的床上吞儿一声笑了:“咱的名儿都跟着大地方起哩。”
津平满月吃面条时,章柿、章楝都回来了,罗贫农领着一群几十口人来了。这有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后一回支应门事,就表现出很高的兴致。见了河西章的人,认识不认识的都一律亲切地打招呼。他知道,人们都是认识他的,他想起了一个词,平易近人,是的,他配得上用这个词。他是革命烈属,他大儿子在北京是大干部,他最亲的孙女又嫁给了在天津上大学的人,头胎就生了带把的。我将来有一天躺到南北坑里,也能安生闭上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