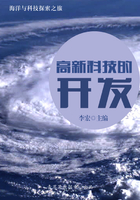“嗐,花冤钱!没看见你闺女在‘美乐’餐厅前边卖货?那么多纸箱,要一个得了!”
李斌脸“刷”地红了。
幸好同屋的胖子聊起了深圳特区的酒吧间和夜总会,“美乐”餐厅的性质和夜总会差不了哪儿去!去年我们出差到深圳,恰巧国内的几个知名作家也在那儿,可谁敢进去?咱们内地人觉得花那钱是当冤大头!可人家‘万元户’,在里边可神气了。
“没错,卖这批货的这些人,”另一个拉着毛巾衫掂了掂,“在‘美乐’餐厅足吃海塞了一顿,出来拉几根绳,就卖开了货!”
李斌注意到,他们在有意地岔开小伙子刚才贸然地提到自己女儿卖货的事儿。这使内心的隐痛重又涌上心头。他开始埋头收拾东西。先把箱子底上铺上废报纸,把石头、贝壳之类不怕压的放在底下。然后是虾仁、虾皮之类的东西。贝壳工艺品怕磕怕碰,他把随身带的几本书围成一个牢固的圈子,以专门存放工艺品,空隙都用纸塞实,以免在颠簸中支离破碎……一切都装妥了,大纸箱仍空出三分之一。
那三位还聊着有关个体户的传闻,但已大都是溢美和赞赏之词。瞧瞧,得着点实惠态度就来他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似乎,他们已从个人好恶中超脱出来,而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来认识这批新商人。看他们那神态,一个个仿佛精通历史的学者,正挥臂驱散历史的尘埃,让历史的明天光辉地显现出绝美的画面……这神态,让他蓦地想起刚才,他们谈到女儿时那种讳莫如深的神情……嗨!这丫头,不回来帮爸爸收拾东西,却帮助人家卖货!怎么,难道被围在众多的抢购物品的顾客当中,象电影明星被围在崇拜者中间那样,能够得到虚荣心的满足吗?显然,这种抛头露面让她无比兴奋!他眼前闪现女儿胸衣上挣脱的钮扣和那个隐约闪现的白乳罩……
他突然火起,把枕头旁放的一个漂亮的布书包——那里装有女儿和他换洗的几件衣服,往纸箱里一扔。居然,它刚好填满那个纸箱的空余部分。真是歪打正着!他正愁没东西填满它呢!他用草绳把纸箱一箍箍捆绑起来。然后他到旅馆门口,找来一个拉平板车的小伙子,和他讨了半天价,最后商妥花一元钱把他和货物拉到火车站。在车站他又忙了一通:一列货车正在装货呢!他赶紧办了慢件托运手续。直到看着货物上了车,他才走出货运站口。
他抻着被汗水粘在身上的衣服,欣赏小镇风情。车站广场笼罩在夕阳昏黄的光线里。房屋大都是砖砌的平房,几栋新的高层建筑正在施工。一条皱巴巴的公路穿过广场通向田野。狗在墙根噢来噢去。一辆马车经过,洒下一串清脆的蹄音;人是走动的;远处,几个小茶摊正接待喝茶的顾客。黄昏因而在这人来人往的车站广场,更显出意味深长的寂静。火车启动了,一团白烟喷向天际。最后,玫瑰色的天际,只剩下一缕缕象银灰色的缎带一样的烟雾,升高,散去……
难道就这样离开这里?简直就象落荒而逃!唉,女儿……不,他不怪她;可又怪谁?那帮混小子?他也并不认为他们有什么“坏”,谈不上。他只是,怎么说呢?他们让他想起自己……咳,怎么说呢?想到自己结婚时简朴的房间,想到自己清清淡淡的生活,他从来没想到要买一辆摩托车……如今,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年轻人已步入摩托车时代,他呢,他什么时候能……摆脱他们的纠缠!算了,别这么心狭量窄!何必呢!然而,正当他踱到车站售票处的门口时,他却突然丧魂落魄般地站住了,他右手拍着左胸的上衣兜,瞪大眼睛张着嘴:天呀!糟透了!他们的大宗款项,已经随着慢件托运箱跟着火车走了!原来,因为怕遭偷儿盗窃,他兜里只装少许零花钱,大笔款子都装在一个信封里,为了不至于太招人耳目,又把信封放在一条备穿的裤兜里,然后塞进那个专装衣物的书包里。这书包,刚才他一怒之下已经投入纸箱……
天似乎黑了许多;小镇的车站广场突然显得出奇地肮脏、丑陋;一股股马粪味随风飘荡……他茫然四顾,怎么办?他在这里无亲无故,两眼一抹黑,上哪儿去借贷?旅馆费用还一分没交呢!
八
六神无主的慌张感控制着他。一只黑狗拖着肮脏的尾巴,在他身边噢来噢去,他扬脚踢去,那狗“嗷”地叫了一声,跑了。
他站在公共汽车的站牌下。已经六点出头了,小镇上的公共汽车却总不来。他恨不能揪住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死乞白赖地求他帮助驮往海滨。但愿女儿有个“小金库”。她既然能躲开父母的眼睛去谈恋爱,难道就不会有自己的积蓄?
突然一阵摩托车声从树林后的公路上响起。唉,要有辆……那车转眼间沿着公路拐进广场。分明是女儿搂着邓力强的腰,风驰电掣地驰到车站候车室门口。
这是够扎眼的。广场上没几个人不注视那辆海蓝色的雅马哈!女儿甚至在跳下车时,也没忘记保持体态的优美。她听任风儿掀动裙裾,潇洒地扬起手臂,双手举到肩后捋着被吹散的乌黑长发,一边疾步走进候车室。在微微摇摆的身姿消失之后,仍引起人们长久的注视。
他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学会的卖弄风骚!过去他喜欢女儿爱美,姑娘嘛!但此刻,却只有反感。他往候车室走去。在绕过摩托车时,他决定要比那把“瓦刀”更旁若无人。
“欵,伯父……”“瓦刀”略带迟疑地叫道。
他沉着脸,略微偏一下头,算作了回答。正是此时,女儿步履匆匆地走出来。
“爸!”她兴奋地叫起来。立即看出他脸色不好,“爸,您……怎么了?”声音低了很多。
爸爸阴沉着脸,折身往隔开广场与铁路的栏杆走去。李莉无声地跟在后边。
“你兜里有多少钱?”
“三块多吧。”女儿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就这么点?”
“爸,我是义务帮他们卖货……”
“你没私下里积蓄点?”
“爸——”女儿噘着嘴摇着肩膀,“您干嘛呀?”
他瞪了她一眼。“我一时疏忽——你能想象我为什么疏忽,忘了把信封里的那些钱取出来。它们随着纸箱托运走了。现在,旅馆费没缴,买车票钱也不够。”
“啊!”女儿吃惊地盯着爸爸。
他皱着眉头,目光随着脸扭到一旁。这瞬间,他甚至产生了某种近乎残忍的快慰:着急吧!你的行动引出这样的结果——看你怎么办?到头来,还得靠你老子吧?!你跟着他们跑个什么劲?除了引起一系列的噩梦,什么也捞不着!着急吧!哼!
“那咱们怎么办?”她声音和表情都透着着急。
“怎么办?你不是一向很有主意吗?”
“我哪里有什么主意呀!”她虚弱地说。
“嘀嘀、嘀。”候车室门前的摩托喇叭响了。“瓦刀”缓缓地驰到他们身边。
“发生了什么事儿?”
“我们家的事儿。”爸爸说。
“李莉,什么事儿?”“瓦刀”并不理会爸爸的话。
“哦,没什么……”
“是不是因为帮我们卖货,影响了你们的行程?”他对她爸爸说,“我正是带着她来给您赔不是的……”
“请你不要参与我们家的事儿!”爸爸终于对他板起面孔,“走吧,小莉。汽车进站了。”
小莉低着头跟在爸爸后边。摩托车和她几乎是并排着慢慢往前驶。人们仍无声地注视着他们。
邓力强象鱼似的把嘴一张一合地动着。李莉从他口型中看出是在问:“什么事情?”李莉也无声地动着嘴。邓力强以为她在说:“我们不走了”,便高兴地点头。但李莉告诉他理解错了。他看着她的表情及嘴的张合,恍然大悟:“没钱了?”她面目沉痛地点头。在旁人看来,这是对配合默契的恋人,由于受到长辈的干涉,在悄悄商量对策。他们和老头的距离越拉越远了。
事情竟那么巧:正当老头愤怒地扭回身,目光灼灼地盯着他们时,小伙子恰好驱车驶到老头身旁。他刹住车,伸手掏出一叠十元钞票,手指沾着唾沫,“哗啦”地捋了它一下,点也没点地递到老头面前:
“伯父,我全知道了。给,拿去交旅馆费、买车票吧。这是一百元;五十是李莉劳动所得,五十元是预支给您的讲课费。”他手一抖,那叠钱一下塞到愣神儿地站在那里的老头上衣兜里,“拜拜!回去我们要找您上几课!”
他挥着手,摩托车一溜烟地驶去。
嘿!看他抖钱的动作!看他把钱往他兜里一塞的功夫!纯粹是捞鱼虫的老手,在表演混水摸鱼的把戏!那是谁也难迅速作出反应的动作!
他先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但当女儿含着担心的微笑走到他面前时,他脑海里蓦地涌出这个想法: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帮“怪胎”、这把“瓦刀”,是不会从他的生活中消逝了,他们将一起裹夹在生活的长河里流淌而去……
他朝着女儿尴尬地笑了一声。只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