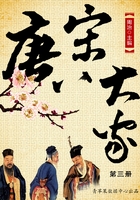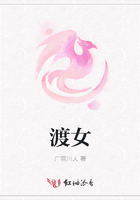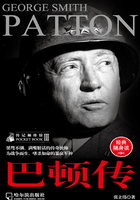我在天津一中读书时,音乐课唱过两首歌,一首是《黄水谣》,一首是《五月的鲜花》,从此,记住了词作者光未然。后来参加中学生合唱团,排练《黄河大合唱》,更是牢牢记住了词曲作者:光未然、冼星海。这两个名字跟这部作品,伴随着我整个成长过程,即使在进入老年的今天,聆听《黄河大合唱》的演唱,我依然会激动犹如当初。那年去冼星海故乡广州番禺参加笔会,给《人民日报》写的散文《寻觅记忆的声音》,灵感就是来自这部《黄河大合唱》。
年轻时进入报刊界,多年编辑文学稿件,知道文学界的张光年,却不知道张光年即光未然,有次翻阅《作家大辞典》,这才知道文学评论家张光年,即是著名诗人光未然。可是万万不曾想到,我“右派”问题改正后,调入《新观察》杂志社,此时,中国作家协会主要领导人,正是这位仰慕已久的光未然。
尽管那时作为普通编辑,跟张光年先生接触不多,但是关于他的为人处事,特别是他对新时期文学的推进,对中青年作家的扶持培养,都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和几位中国作家协会当时领导人成了新时期文学事业的标志性人物,许多优秀作品的出现,都倾注着他们的心血。那时的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如同一块磁铁紧紧地吸引着作家,如今有些作家谈论新时期文坛,无不对张光年那代领导人充满敬意,怀念中国作家协会那种“家”的感觉。
张光年先生任中国作协领导时,我被任命《新观察》杂志社组长职务,想不到还跟他有一定关系。那时中国作家协会刚恢复,行政建制还未被准确定位,各报刊社中层部门都叫组,主编戈扬有意让我担任组长,她找我谈话时,我说:“我一个白丁,这怎么行呢?”后来主编再找我时,明确地说:“我跟光年请示了,光年说,不是党员该用照样用。”就这样,我被任命为《新观察》杂志社领导班子成员、时事杂文组组长。
这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给我的第一直接感觉是,张光年在任用干部方面比较务实。
还有一件跟我有关的事,也是发生在张光年主政时。作家白桦电影《太阳与人》放映后,在社会上引起不同凡响,对白桦有种种不实传言。出于澄清事实的目的,我建议请白桦写篇文章,刊登在《新观察》杂志上,当时恰好主编戈扬不在北京,副主编杨犁和编辑部负责人张凤珠同意我的建议并指派我跟白桦约稿。
白桦文章《春天对我如此厚爱》,1981年在《新观察》杂志第14期刊出,未曾想跟电影一样引起轩然大波。
一天傍晚,主编戈扬匆忙跑到我家告诉我,在一个刚刚结束的会议上,胡乔木给冯牧和她写了张便条,批评《新观察》发表白桦文章。戈扬征求我的意见,看如何处理这件事。这是由我惹的“祸”,以为会像过去那样,肯定追究我的责任,起码得写篇检讨文字吧。我表面镇定,心里却不安。为此曾向我敬重的艾青、秦兆阳等前辈作家讨教。
令我未想到和感动的是,杨犁和张凤珠作了说明,责任则完全由中国作协揽了去。张光年让中国作协秘书长杨子敏化名冯明(奉命谐音)写了篇文章《也谈春天的“厚爱”》,委婉地批评白桦文章,发表在1981年第17期《新观察》杂志,这件惊动中央领导的事才算暂时平息。
从这件事可以清楚地看出,以张光年为首的中国作协领导层,在处理突发“政治事件”上,特别是在保护下属上,远比过去更有谋略和智慧。
1988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决定,我从作家出版社副社长任上调出,到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主持工作。到任后查阅相关档案资料知道,倡导成立这家出版机构的人,正是评论家张光年和翻译家陈冰夷、杨宪益,由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排除出版业内的干扰(坚持对外翻译出版,只外文局一个渠道)最后批准。宗旨就是向海外翻译推介中国文学。从名称到经营方式都是全新的,完全有别于传统出版机构,却与世界出版机构紧密接轨。用今天出版社改制眼光来看,这家新型出版机构的成立,其思路和做法整整超前了三十年,在改革开放初期是绝无仅有的一家,即使现在好像也未听说过哪家出版社名称和经营方式全如此,足见胡耀邦和张光年、陈冰夷、杨宪益,他们在文学事业上的远见卓识。我接手后翻译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中国军事文学作品选》英文版,而后又出版《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本索引手册》,并且很快跟多家国外出版机构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或意向,初步实现了张光年等老一辈文学家,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愿望。可惜在1989年那场风波中,刚刚起步的中外文化出版公司,跟《新观察》《小说选刊》《散文世界》一起,被迫停办并撤销了社号,我和我的年轻同事们从此赋闲,再也无心思干别的正经事情,为排遣烦恼和时间就到处跑。不过就我个人来说,那是我一生当中最值得怀念的时光。非常感谢张光年、陈冰夷、杨宪益三位前辈,由于他们的远见卓识,搭建这么好的一个文学平台,由我主持做成了他们想做的事,使我前半生坎坷、平庸的生命在最后时日闪出一点微弱光亮。这无论对他们还是对我都是个安慰。遗憾的是,可以认真做事的日子,转瞬即逝。
我真正接触张光年,是在赋闲之后,1991年的西北之行。中国作协组织作家访问西北,知道我情况的创联部朋友们,为让我解脱精神上的苦闷,安排我参加作家团造访河西走廊。跟我们同行的就有张光年夫妇。光年是我们这一行人中级别最高、年龄最大、资历最老,却毫无一点架子和傲慢,乘一样车,吃一样饭,说一样话,连称谓都是直呼其名,对光年最多加上“同志”,或者叫“张老”以示尊重,无论是中国作协的人,还是外地来的作家,没有一人称呼他职务,他总是乐呵呵地答应。
这时的张光年在我们眼中就是一位老作家、老朋友,彼此间相处得非常融洽。可惜这样亲切、平等的风气,后来在中国作家协会消失,职务称谓跟机关完全一样。每每想起此事格外怀念张光年,以及他那代领导人的好作风。
那时作家出去采风没有现在这么威风——火车坐软卧,宾馆住星级——费用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当然也无人计较此类事情。我们一行十多人中,够级别的有好几位,软卧票却只有三张,除光年夫妇外,还剩一张软卧票,几个人互相推让,谁也不肯去坐,除了朋友间的友爱,还怕跟光年一起拘谨,最后只好留给后到的江西省作协主席陈世旭。
事后听陈世旭讲,跟光年相处得非常好,一路上有说有笑,根本没有隔辈之感。
我们从兰州启程,乘坐一辆面包车,开始向敦煌进发。在茫茫戈壁滩,荒凉障目,车声塞耳,时光显得漫长。为了排遣寂寞,大家互相取笑,笑声充满车厢。光年显然被笑声感染,他也跟着开怀大笑,如同一位普通长者。直到到了莫高窟,他在关照我们时,我们才忽然记起张光年是中顾委委员。
参观莫高窟有规定,重要的窟考虑保护,严格按照级别开放,只允许张光年一人参观。光年就跟接待方说:“跟我来的都是作家,来趟敦煌不容易,请你们破个例,让他们跟我一起看吧。”我们这次的敦煌之行,沾光年的光参观多个窟,当然,多数人也就是看看而已,其中收获最大的当属青年作家徐小斌,她有个酝酿多年的故事,在敦煌突然找到叙述环境,回来写成小说《敦煌遗梦》。
这次的西北之行,大家相处得非常好,无年龄之别,无职位之分,彼此说笑逗闹起绰号,是一次很快乐的笔会。光年对我们这些晚辈,有所了解有了感情。从西北返回北京不久,光年请他的秘书吴桂凤特意给我送来他的字幅,内容是他的诗《鸣沙山》。诗曰:“莫嫌沙粒小,聚沙可成山,莫笑沙不语,长啸如雷喧,,沙峦八十里,护此月牙泉,涉沙腿脚软,小坐叹奇观”。这既是老诗人的感受,这也是我们经历的情景,我感到特别的温暖和亲切,这使我对光年的为人,有了进一步的具体了解。
我把这件墨宝镶框,悬挂在我家客厅里,现在有时睹字思人,那次西北之行情景,就会油然再现眼前,仿佛光年并未远去。
其后,光年又赠《惜春文谈》《光未然脱险记》《向阳日记》和歌词选等新书给我,可见这位老诗人、老领导多么看重西北之行的友谊。有人说,书生人情纸半张,请问,现在的书生们,这半张纸的人情,究竟还有多少呢?
比这更让我感动的是,1994年盛夏在北戴河创作之家,遇到先来避暑的光年,他在二楼阳台上看到我,笑着脱口叫了声我的绰号,让我上楼去他房间坐坐。亲自给我倒了杯水,而后就忙不迭询问我的近况和家人情况,作协是否安排了我的工作,等等。当我如实把安排意向告诉他,他推心置腹地为我出主意,没有丝毫的芥蒂和保留。这使我隐约地觉得,尽管光年从政多年,处于文坛领导地位,但是气质依然是个诗人。
作为学者、文学评论家的张光年,生前有多种学术和评论著作,然而真正让他享誉华人世界的,还是他和冼星海共同创作的那部《黄河大合唱》。那年去延安开会回来路过壶口,面对着滔滔的黄河之水,那铺天盖地的澎湃气势,让我们一行人简直看呆了。这些平日善于言辞的作家、诗人,一时却找不出表达心声的方式,个个表情严肃地凝视着河面,仿佛在向这条伟大的母亲河致敬。
突然,一位诗人冒出一句:“啊,朋友!黄河以它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它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顿时启开众人心灵闸门,大家激动地唱起来:“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金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歌声汇入滚滚浪涛,流向天边奔向远方,骄傲和豪迈的情感充盈在每个人胸膛。
在黄河之滨唱《黄河大合唱》,其情其景令我们热血沸腾,如同依偎着母亲的怀抱,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自然而然从心底生起,不禁想到黄河的歌者——冼星海、光未然。在决定国家存亡的关头,他们以饱满的革命激情创作出这部大合唱,鼓舞全民族奋起抗日,他们不愧为黄河之子。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黄河千年百代地流淌,《黄河大合唱》就永远传唱。音乐家冼星海,诗人光未然,这两个耀眼的名字,将会长久地活在黄河的魂魄中。
2012年10月2日
同是荒原沦落人
忘记是谁告诉我的,黄苗子先生病故了,时间好像是2012年初。听后我的心中咯噔一下:唉,最后一位年长“老同学”走了。随之我脑海里立刻翻起记忆波澜。
那是北京“右派”刚到北大荒,经过漫长的冰雪严冬,终于等来第一个春天,冰雪消融,花草展容,云雀歌唱,蛮荒的大地充满勃勃生机。我们这些流人压抑的心绪,好像也渐渐有些好转,不过在寂寞清冷的晚上,依然能听到长吁短叹声,能看到独饮消愁人。看来“柳暗花明”的生活,对于我们还蛮遥远、很艰难。
有天傍晚收工回来,难友们拖着疲惫身躯,无精打采地走到工棚,忽然发现五颜六色的野花,组成一个大的“乐”字,用绿草衬托放在脸盒里。立刻吸引住众人眼球,都在久久地观望欣赏,谁也没有说什么,却又仿佛在说:“这是谁植的花儿,在这时候,还有这样的心思?”后来听说,黄苗子见满地花草,鲜嫩可爱,就随手采撷回来,精心组成这盒花,用以鼓励难友忧中找乐。从此,我记住了书画家黄苗子。
论年龄,我跟黄苗子相差二三十岁哪,他又是著名书画家,年龄地位相差甚远,怎么是“老同学”呢?欲求答案就得问老天爷了,他老人家开玩笑,有时不知高低深浅,常常是不考虑人的感受,胡乱地取闹寻乐,让当事人都不好意思。我现在说起我的“老同学”,就多少有点忐忑不安,怕人说我这是高攀名人。不过,那可就冤枉死我了。
其实不光是苗子先生,还有多位文化名人,如艾青、丁玲、吴祖光、丁聪、尹瘦石、聂绀弩、陈沂、沈默君、李景波等前辈,都是我的“老同学”。您觉得我的口气大了吧?的确是大了点儿。只是您得听清楚,这“老同学”称呼,是他们先叫我的,不是我主动叫他们的,给我三个胆儿都不敢张嘴。即使他们不是名人,摆在那里的年岁,我也不能如此造次呵。
为什么说是老天爷开玩笑呢?年轻人是不知道了,年纪大的人还记得,1957年那场“阳谋”运动,按官方正式公布的数字,全国划了五十五万“右派”,其中不乏响当当的名人。可是一顶帽子戴上,就不分尺码大小了,统统都是“右派分子”,像我前边说的多位名人,都曾经是我仰慕的人物,他们被戴上“右派”帽子,就跟我这个无名小“右派”,划等号成了“一小撮儿”,统称“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完全没有了高低贵贱之分。
1958年早春,国家机关和驻京部队机关近三千名“右派”,同乘一列慢车出山海关,被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上了火车犹如鸟儿出笼,尽管头上戴着“紧箍儿”,但是毕竟都是一水儿的老“右”,大家彼此彼此,再无冷眼横眉,说话做事都无人监督,神经反而比在北京松弛。认识不认识的都一起聊天儿。在漫长寂寞的旅途中,渐渐地彼此混熟了,不知不觉就无防备了,真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原来人跟人只要平等,再警惕的心也会毫无芥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