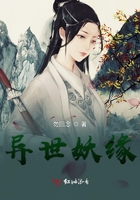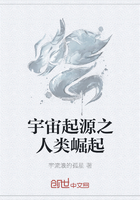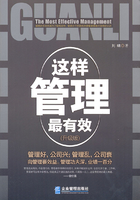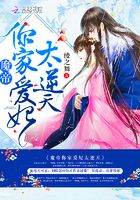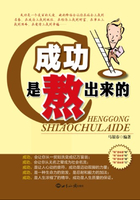福虚篇第二十
世论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福祸之应,皆天也,人为之,天应之。阳恩,人君赏其行;阴惠,天地报其德。无贵贱贤愚,莫谓不然。徒见行事有其文传,又见善人时遇福,故遂信之,谓之实然。斯言或时贤圣欲劝人为善,著必然之语,以明德报;或福时适遇者以为然。如实论之,安得福佑乎?
禁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问:“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废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国人闻之也;谴而行诛乎?则庖厨监食者法皆当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见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贺曰:“臣闻天道无亲,唯德是辅。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为伤。”是夕也,惠王之后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积皆愈。故天之亲德也,可谓不察乎!曰:此虚言也。案惠王之吞蛭,不肖之主也。有不肖之行,天不佑也。何则?惠王不忍谴蛭,恐庖厨监食法皆诛也。一国之君,专擅赏罚;而赦,人君所为也。惠王通谴菹中何故有蛭,庖厨监食皆当伏法。然能终不以饮食行诛於人,赦而不罪,惠莫大焉。庖厨罪觉而不诛,自新而改后。惠王赦细而活微,身安不病。今则不然,强食害己之物,使监食之臣不闻其过,失御下之威,无御非之心,不肖一也。使庖厨监食失甘苦之和,若尘土落於菹中,大如虮虱,非意所能览,非目所能见,原心定罪,不明其过,可谓惠矣。今蛭广有分数,长有寸度,在寒菹中,眇目之人犹将见之,臣不畏敬,择濯不谨,罪过至重。惠王不谴,不肖二也。菹中不当有蛭,不食投地;如恐左右之见,怀屏隐匿之处,足以使蛭不见,何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误在菹中,可复隐匿而强食之,不肖三也。有不肖之行,而天佑之,是天报佑不肖人也。不忍谴蛭,世谓之贤。贤者操行,多若吞蛭之类。吞蛭天除其病,是则贤者常无病也。贤者德薄,未足以言。圣人纯道,操行少非,为推不忍之行,以容人之过。必众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疾病,天之佑人,何不实也?或时惠王吞蛭,蛭偶自出。食生物者无有不死,腹中热也。初吞时蛭未死,而腹中热,蛭动作,故腹中痛。须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积,殆积血也。故食血之虫死,而积血之病愈。犹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类相胜,方药相使也。食蛭虫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物无不死,死无不出,之后蛭出,安得佑乎?令尹见惠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当死出,因再拜,病贺不为伤。著已知来之德,以喜惠王之心,是与子韦之言星徙、太卜之言地动无以异也。
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改,家无故黑牛生白犊。以问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即以犊祭。一年,其父无故而盲。牛又生白犊。其父又使其子问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复以犊祭。一年,其子无故而盲。其后楚攻宋,围其城。当此之时,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此独以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军罢围解,父子俱视。此修善积行神报之效也。曰:此虚言也。夫宋人父子修善如此,神报之,何必使之先盲后视哉?不盲常视,不能护乎?此神不能护不盲之人,则亦不能以盲护人矣。使宋、楚之君合战顿兵,流血僵尸,战夫禽获,死亡不还。以盲之故,得脱不行,可谓神报之矣。今宋、楚相攻,两军未合,华元、子反结言而退,二军之众,并全而归,兵矢之刃无顿用者。虽有乘城之役,无死亡之患。为善人报者,为乘城之间乎?使时不盲,亦犹不死。盲与不盲,俱得脱免,神使之盲,何益於善!当宋国乏粮之时也,盲人之家,岂独富哉?俱与乘城之家易子 骸,反以穷厄独盲无见,则神报佑人,失善恶之实也。宋人父子前偶自以风寒发盲,围解之后,盲偶自愈。世见父子修善,又用二白犊祭,宋、楚相攻独不乘城,围解之后父子皆视,则谓修善之报、获鬼神之佑矣。
楚相孙叔敖为儿之时,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对其母泣。母问其故,对曰:“我闻见两头蛇死。向者出见两头蛇,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曰:“今蛇何在?”对曰:“我恐后人见之,即杀而埋之。”其母曰:“吾闻有阴德者,天必报之。汝必不死,天必报汝。”叔敖竟不死,遂为楚相。埋一蛇,获二佑,天报善明矣。曰:此虚言矣。夫见两头蛇辄死者,俗言也;有阴德天报之福者,俗议也。叔敖信俗言而埋蛇,其母信俗议而必报,是谓死生无命,在一蛇之死。齐孟尝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婴让其母曰:“何故举之?”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何也?”婴曰:“五月子长与户同,杀其父母。”曰:“人命在天乎?在户乎?如在天,君何忧也;如在户,则宜高其户耳,谁而及之者!”后文长与一户同,而婴不死。是则五月举子之忌,无效验也。夫恶见两头蛇,犹五月举子也。五月举子,其父不死,则知见两头蛇者,无殃祸也。由此言之,见两头蛇自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一蛇,获二福,如埋十蛇,得几佑乎?埋蛇恶人复见,叔敖贤也。贤者之行,岂徒埋蛇一事哉?前埋蛇之时,多所行矣。禀天善性,动有贤行。贤行之人,宜见吉物,无为乃见杀人之蛇。岂叔敖未见蛇之时有恶,天欲杀之,见其埋蛇,除其过,天活之哉?石生而坚,兰生而香。如谓叔敖之贤在埋蛇之时,非生而禀之也。
儒家之徒董无心,墨家之役缠子,相见讲道。缠子称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赐之十九年,缠子难以尧、舜不赐年,桀、纣不夭死。尧、舜、桀、纣犹为尚远,且近难以秦穆公、晋文公。夫谥者,行之迹也,迹生时行,以为死谥。穆者误乱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误乱之行,天赐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夺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过晋文;晋文之谥,美於穆公。天不加晋文以命,独赐穆公以年,是天报误乱,与“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寡,恶人众。善人顺道,恶人违天。然夫恶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长。天不命善人常享一百载之寿,恶人为殇子恶死,何哉?
祸虚篇第二十一
世谓受福佑者,既以为行善所致;又谓被祸害者,为恶所得。以为有沉恶伏过,天地罚之,鬼神报之。天地所罚,小大犹发;鬼神所报,远近犹至。
传曰:“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无罪也?吾与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间,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异闻,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曰,汝何无罪欤?’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以久矣!’”夫子夏丧其明,曾子责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盖以天实罚过,故目失其明,已实有之,故拜受其过。始闻暂见,皆以为然;熟考论之,虚妄言也。夫失明犹失听也。失明则盲,失听则聋。病聋不谓之有过,失明谓之有罪,惑也。盖耳目之病,犹心腹之有病也。耳目失明听,谓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谓有过乎?伯牛有疾,孔子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子言,谓伯牛不幸,故伤之也。如伯牛以过致疾,天报以恶与子夏同,孔子宜陈其过,若曾子谓子夏之状。今乃言命,命非过也。且天之罚人,犹人君罪下也。所罚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过,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换三罪。且丧明之病,孰与被厉之病?丧明有三罪,被厉有十过乎?颜渊早夭,子路菹醢。早死、菹醢,极祸也。以丧明言之,颜渊、子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误矣。然子夏之丧明,丧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亲者人所力报也。丧亲民无闻,丧子失其明,此恩损於亲而爱增於子也。增则哭泣无数,数哭中风,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议,以著子夏三罪。子夏亦缘俗议,因以失明,故拜受其过。曾子、子夏未离於俗,故孔子门叙行,未在上第也。
秦襄王赐白起剑,白起伏剑将自刎,曰:“我有何罪於天乎?”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杀。白起知己前罪,服更后罚也。夫白起知己所以罪,不知赵卒所以坑。如天审罚有过之人,赵降卒何辜於天?如用兵妄伤杀,则四十万众必有不亡,不亡之人,何故以其善行无罪而竟坑之?卒不得以善蒙天之佑,白起何故独以其罪伏天之诛?由此言之,白起之言过矣。
秦二世使使者诏杀蒙恬,蒙恬喟然叹曰:“我何过於天,无罪而死!”良久,徐曰:“恬罪故当死矣。夫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径万里,此其中不能毋绝地脉。此乃恬之罪也。”即吞药自杀。太史公非之曰:“夫秦初灭诸侯,天下心未定,夷伤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救百姓之急,养老矜孤,修众庶之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与乃罪地脉也?”夫蒙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何则?蒙恬绝脉,罪至当死。地养万物,何过於人,而蒙恬绝其脉?知己有绝地脉之罪,不知地脉所以绝之过。自非如此,与不自非何以异?太史公为非恬之为名将,不能以强谏,故致此祸。夫当谏不谏,故致受死亡之戮。身任李陵,坐下蚕室,如太史公之言,所任非其人,故残身之戮,天命而至也。非蒙恬以不强谏,故致此祸,则己下蚕室,有非者矣。己无非,则其非蒙恬,非也。作伯夷之传,列善恶之行云:“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卒夭死。天之报施善人如何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独遵何哉?”若此言之,颜回不当早夭,盗跖不当全活也。不怪颜渊不当夭,而独谓蒙恬当死,过矣。汉将李广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常不在其中,而诸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然以胡军攻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终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常有恨者乎?”广曰:“吾为陇西太守,羌常反,吾诱而降之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恨之,独此矣。”朔曰:“祸莫大於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李广然之,闻者信之。夫不侯犹不王者也。不侯何恨,不王何负乎?孔子不王,论者不谓之有负;李广不侯,王朔谓之有恨。然则王朔之言,失论之实矣。论者以为人之封侯,自有天命。天命之符,见於骨体。大将军卫青在建章宫时,钳徒相之,曰:“贵至封侯。”后竟以功封万户侯。卫青未有功,而钳徒见其当封之证。由此言之,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钳徒之言实而有效,王朔之言虚而无验也。多横恣而不罹祸,顺道而违福,王朔之说,白起自非、蒙恬自咎之类也。仓卒之世,以财利相劫杀者众。同车共船,千里为商,至阔迥之地,杀其人而并取其财,尸捐不收,骨暴不葬,在水为鱼鳖之食,在土为蝼蚁之粮;惰窳之人,不力农勉商,以积谷货,遭岁饥馑,腹饿不饱,椎人若畜,割而食之,无君子小人,并为鱼肉:人所不能知,吏所不能觉。千人以上,万人以下,计一聚之中,生者百一,死者十九。可谓无道至痛甚矣,皆得阳达富厚安乐。天不责其无仁义之心,道相并杀;非其无力作而仓卒以人为食,加以渥祸,使之夭命,章其阴罪,明示世人,使知不可为非之验,何哉?王朔之言,未必审然。
传书:“李斯妒同才,幽杀韩非於秦,后被车裂之罪,商鞅欺旧交,擒魏公子卬,后受诛死之祸。”彼欲言其贼贤欺交,故受患祸之报也。夫韩非何过而为李斯所幽?公子卬何罪而为商鞅所擒?车裂诛死,贼贤欺交,幽死见擒,何以致之?如韩非、公子卬有恶,天使李斯、商鞅报之,则李斯、商鞅为天奉诛,宜蒙其赏,不当受其祸。如韩非、公子卬无恶,非天所罚,李斯、商鞅不得幽擒。论者说曰:“韩非、公子卬有阴恶伏罪,人不闻见,天独知之,故受戮殃。”夫诸有罪之人,非贼贤则逆道。如贼贤,则被所贼者何负?如逆道,则被所逆之道何非?
凡人穷达祸福之至,大之则命,小之则时。太公穷贱,遭周文而得封。甯戚隐阨,逢齐桓而见官。非穷贱隐阨有非,而得封见官有是也。穷达有时,遭遇有命也。太公、甯戚,贤者也,尚可谓有非。圣人,纯道者也。虞舜为父弟所害,几死再三;有遇唐尧,尧禅舜。立为帝。尝见害,未有非;立为帝,未有是。前时未到,后则命时至也。案古人君臣困穷,后得达通,未必初有恶天祸其前,卒有善神佑其后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结发终死,前后无异。然一成一败,一进一退,一穷一通,一全一坏,遭遇适然,命时当也。
龙虚篇第二十二
盛夏之时,雷电击折树木,发坏室屋,俗谓天取龙,谓龙藏於树木之中,匿於屋室之间也,雷电击折树木,发坏屋室,则龙见於外。龙见,雷取以升天。世无愚智贤不肖,皆谓之然。如考实之,虚妄言也。
夫天之取龙何意邪?如以龙神为天使,犹贤臣为君使也,反报有时,无为取也。如以龙遁逃不还,非神之行,天亦无用为也。如龙之性当在天,在天上者固当生子,无为复在地。如龙有升降,降龙生子於地,子长大,天取之,则世名雷电为天怒,取龙之子,无为怒也。且龙之所居,常在水泽之中,不在木中屋间。何以知之?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传曰:“山致其高,云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龙生焉。”传又言:“禹渡於江,黄龙负船。”“荆次非渡淮,两龙绕舟。”“东海之上,有A丘欣,勇而有力,出过神渊,使御者饮马,马饮因没。欣怒,拔剑入渊追马,见两蛟方食其马,手剑击杀两蛟。”由是言之,蛟与龙常在渊水之中,不在木中屋间明矣。在渊水之中,则鱼鳖之类。鱼鳖之类,何为上天?天之取龙,何用为哉?如以天神乘龙而行,神恍惚无形,出入无间,无为乘龙也。如仙人骑龙,天为仙者取龙,则仙人含天精气,形轻飞腾,若鸿鹄之状,无为骑龙也。世称黄帝骑龙升天,此言盖虚,犹今谓天取龙也。
且世谓龙升天者,必谓神龙。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天地之性,人为贵,则龙贱矣。贵者不神,贱者反神乎?如龙之性有神与不神,神者升天,不神者不能。龟蛇亦有神与不神,神龟神蛇,复升天乎?且龙禀何气而独神?天有仓龙、白虎、朱鸟、玄武之象也,地亦有龙、虎、鸟、龟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兽。虎鸟与龟不神,龙何故独神也?人为倮虫之长,龙为鳞虫之长。俱为物长,谓龙升天,人复升天乎?龙与人同,独谓能升天者,谓龙神也。世或谓圣人神而先知,犹谓神龙能升天也。因谓圣人先知之明,论龙之才,谓龙升天,故其宜也。
天地之间,恍惚无形,寒暑风雨之气乃为神。今龙有形,有形则行,行则食,食则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体之类,能行食之物,不得为神。何以言之,龙有体也。传曰:“鳞虫三百,龙为之长。”龙为鳞虫之长,安得无体?何以言之,孔子曰:“龙食於清,游於清。龟食於清;游於浊;鱼食於浊,游於浊。丘上不及龙,下不为鱼,中止其龟与!”
《山海经》言:四海之外,有乘龙蛇之人。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尾。由此言之,马、蛇之类也。慎子曰:“蜚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雨霁,与蚓蚁同矣。”韩子曰:“龙之为虫也,鸣可狎而骑也。然喉下有逆鳞尺余,人或婴之,必杀人矣。”比之为蚓蚁,又言虫可狎而骑,蛇、马之类明矣。传曰:“纣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极也。夫有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盈,象箸所挟,则必龙肝豹胎。夫龙肝可食,其龙难得。难得则愁下,愁下则祸生,故从而痛之。如龙神,其身不可得杀,其肝何可得食?禽兽肝胎非一,称龙肝豹胎者,人得食而知其味美也。春秋之时,龙见於绛郊。魏献子问於蔡墨曰:“吾闻之,虫莫智於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智,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智。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曰:“是二者,吾亦闻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谓也?”对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嗜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舜,而锡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鬲川,鬲夷氏是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於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於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龙。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亨之。既而使求,惧而不得,迁於鲁县,范氏其后也。”献子曰:“今何故无之?”对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低伏,郁湮不育。”由此言之,龙可畜又可食也。可食之物,不能神矣。世无其官,又无董父、后刘之人,故潜藏伏匿,出见希疏;出又乘云,与人殊路,人谓之神。如存其官而有其人,则龙,牛之类也,何神之有?以《山海经》言之,以慎子、韩子证之,以俗世之画验之,以箕子之泣订之,以蔡墨之对论之,知龙不能神,不能升天,天不以雷电取龙,明矣。世俗言龙神而升天者,妄矣。
世俗之言,亦有缘也。短书言:“龙无尺木,无以升天。”又曰“升天”,又言“尺木”,谓龙从木中升天也。彼短书之家,世俗之人也。见雷电发时,龙随而起,当雷电击树木之时,龙适与雷电俱在树木之侧,雷电去,龙随而上,故谓从树木之中升天也。实者雷龙同类,感气相致,故《易》曰:“云从龙,风从虎。”又言:“虎啸谷风至,龙兴景云起。”龙与云相招,虎与风相致,故董仲舒雩祭之法,设土龙以为感也。夫盛夏太阳用事,云雨干之。太阳火也,云雨水也,水火激薄则鸣而为雷。龙闻雷声则起,起而云至,云至而龙乘之。云雨感龙,龙亦起云而升天。天极雷高,云消复降。人见其乘云则谓“升天”,见天为雷电则为“天取龙”。世儒读《易》文,见传言,皆知龙者云之类。拘俗人之议,不能通其说;又见短书为证,故遂谓“天取龙”。
天不取龙,龙不升天。当A丘欣之杀两蛟也,手把其尾,拽而出之至渊之外,雷电击之。蛟则龙之类也。蛟龙见而云雨至,云雨至则雷电击。如以天实取龙,龙为天用,何以死蛟不为取之?且鱼在水中,亦随云雨,蜚而乘云雨非升天也。龙,鱼之类也,其乘雷电犹鱼之飞也。鱼随云雨,不谓之神,龙乘雷电独谓之神。世俗之言,失其实也。物在世间,各有所乘。水蛇乘雾,龙乘云,鸟乘风。见龙乘云,独谓之神,失龙之实,诬龙之能也。
然则龙之所以为神者,以能屈伸其体,存亡其形。屈伸其体,存亡其形,未足以为神也。豫让吞炭,漆身为厉,人不识其形。子贡灭须为妇人,人不知其状;龙变体自匿,人亦不能觉,变化藏匿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
狌狌知往,乾鹊知来,鹦鹉能言,三怪比龙,性变化也。如以巧为神,豫让、子贡神也。孔子曰:“游者可为网,飞者可为砫。至於龙也,吾不知其乘风云上升。今日见老子,其犹龙乎!”夫龙乘云而上,云消而下。物类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圣,尚不知龙,况俗人智浅,好奇之性,无实可之心,谓之龙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雷虚篇第二十三
盛夏之时,雷电迅疾,击折树木,坏败室屋,时犯杀人。世俗以为“击折树木、坏败室屋”者,天取龙;其“犯杀人”也,谓之有阴过,饮食人以不洁净,天怒,击而杀之。隆隆之声,天怒之音,若人之呴吁矣。世无愚智,莫谓不然。推人道以论之,虚妄之言也。
夫雷之发动,一气一声也,折木坏屋亦犯杀人,犯杀人时亦折木坏屋。独谓折木坏屋者,天取龙;犯杀人,罚阴过,与取龙吉凶不同,并时共声,非道也。论者以为“隆隆”者,天怒呴吁之声也。此便於罚过,不宜於取龙。罚过,天怒可也;取龙,龙何过而怒之?如龙神,天取之,不宜怒。如龙有过,与人同罪,杀而已,何为取也?杀人,怒可也。取龙,龙何过而怒之?杀人不取;杀龙取之。人龙之罪何别?而其杀之何异?然则取龙之说既不可听,罚过之言复不可从。
何以效之?案雷之声迅疾之时,人仆死於地,隆隆之声临人首上,故得杀人。审隆隆者天怒乎?怒用口之怒气杀人也。口之怒气,安能杀人?人为雷所杀,询其身体,若燔灼之状也。如天用口怒,口怒生火乎?且口着乎体,口之动与体俱。当击折之时,声着於地;其衰也,声着於天。夫如是,声着地之时,口至地,体亦宜然。当雷迅疾之时,仰视天,不见天之下,不见天之下,则夫隆隆之声者,非天怒也。天之怒与人无异。人怒,身近人则声疾,远人则声微。今天声近,其体远,非怒之实也。且雷声迅疾之时,声东西或南北,如天怒体动,口东西南北,仰视天亦宜东西南北。或曰:“天已东西南北矣,云雨冥晦,人不能见耳。”夫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共雷。《易》曰:“震惊百里。”雷电之地,云雨晦冥,百里之外无雨之处,宜见天之东西南北也。口着於天,天宜随口,口一移普天皆移,非独雷雨之地,天随口动也。且所谓怒者,谁也?天神邪?苍苍之天也?如谓天神,神怒无声;如谓苍苍之天,天者体不怒,怒用口。且天地相与,夫妇也,其即民父母也。子有过,父怒,笞之致死,而母不哭乎?今天怒杀人,地宜哭之。独闻天之怒,不闻地之哭。如地不能哭,则天亦不能怒。且有怒则有喜。人有阴过,亦有阴善。有阴过,天怒杀之;如有阴善,天亦宜以善赏之。隆隆之声谓天之怒,如天之喜,亦哂然而笑。人有喜怒,故谓天喜怒、推人以知天,知天本於人。如人不怒,则亦无缘谓天怒也。缘人以知天,宜尽人之性。人性怒则呴吁,喜则歌笑。比闻天之怒,希闻天之喜;比见天之罚,希见天之赏。岂天怒不喜,贪於罚,希於赏哉?何怒罚有效,喜赏无验也?
且雷之击也,“折木坏屋”,“时犯杀人”,以为天怒。时或徒雷,无所折败,亦不杀人,天空怒乎?人君不空喜怒,喜怒必有赏罚。无所罚而空怒,是天妄也。妄则失威,非天行也。政事之家,以寒温之气,为喜怒之候,人君喜即天温,怒则天寒。雷电之日,天必寒也。高祖之先刘媪曾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此时雷电晦冥。天方施气,宜喜之时也,何怒而雷?如用击折者为怒,不击折者为喜,则夫隆隆之声,不宜同音。人怒喜异声,天怒喜同音,与人乖异,则人何缘谓之天怒?且“饮食人以不洁净”,小过也。以至尊之身,亲罚小过,非尊者之宜也。尊不亲罚过,故王不亲诛罪。天尊於王,亲罚小过,是天德劣於王也。且天之用心,犹人之用意。人君罪恶,初闻之时,怒以非之;及其诛之,哀以怜之。故《论语》曰:“如得其情,则哀怜而勿喜。”纣至恶也,武王将诛,哀而怜之。故《尚书》曰:“予惟率夷怜尔。”人君诛恶,怜而杀之;天之罚过,怒而击之。是天少恩而人多惠也。说雨者以为天施气。天施气,气渥为雨,故雨润万物,名曰澍。人不喜,不施恩。天不说,不降雨。谓雷,天怒;雨者,天喜也。雷起常与雨俱,如论之言,天怒且喜也。人君赏罚不同日,天之怒喜不殊时,天人相违,赏罚乖也。且怒喜具形,乱也。恶人为乱,怒罚其过;罚之以乱,非天行也。冬雷人谓之阳气泄,春雷谓之阳气发。夏雷不谓阳气盛,谓之天怒,竟虚言也。
人在天地之间,物也。物,亦物也。物之饮食,天不能知。人之饮食,天独知之。万物於天,皆子也;父母於子,恩德一也。岂为贵贤加意,贱愚不察乎?何其察人之明,省物之暗也!犬豕食,人腐臭食之,天不杀也。如以人贵而独禁之,则鼠洿人饮食,人不知,误而食之,天不杀也。如天能原鼠,则亦能原人,人误以不洁净饮食人,人不知而食之耳,岂故举腐臭以予之哉?如故予之,人亦不肯食。吕后断戚夫人手,去其眼,置於厕中,以为人豕。呼人示之,人皆伤心;惠帝见之,疾卧不起。吕后故为,天不罚也。人误不知,天辄杀之,不能原误,失而责故,天治悖也。
夫人食不净之物,口不知有其洿也;如食,已知之,名曰肠洿。戚夫人入厕,身体辱之,与洿何以别?肠之与体何以异?为肠不为体,伤洿不病辱,非天意也。且人闻人食不清之物,心平如故,观戚夫人者,莫不伤心。人伤,天意悲矣。夫悲戚夫人则怨吕后,案吕后之崩,未必遇雷也。道士刘春荧惑楚王英,使食不清。春死,未必遇雷也。建初四年夏六月,雷击杀会稽鄞专日食羊五头皆死。夫羊何阴过,而雷杀之?舟人洿溪上流,人饮下流,舟人不雷死。
天神之处天,犹王者之居也。王者居重关之内,则天之神宜在隐匿之中。王者居宫室之内,则天亦有太微、紫宫、轩辕、文昌之坐。王者与人相远,不知人之阴恶。天神在四宫之内,何能见人暗过?王者闻人进,以人知。天知人恶,亦宜因鬼。使天问过於鬼神,则其诛之,宜使鬼神。如使鬼神,则天怒,鬼神也,非天也。
且王断刑以秋,天之杀用夏,此王者用刑违天时。奉天而行,其诛杀也,宜法象上天。天杀用夏,王诛以秋,天人相违,非奉天之义也。或论曰:“饮食人不洁净,天之大恶也。杀大恶,不须时。”王者大恶,谋反大逆无道也。天之大恶,饮食人不洁清。天人所恶,小大不均等也。如小大同,王者宜法天,制饮食人不洁清之法为死刑也。圣王有天下,制刑不备此法,圣王阙略,有遗失也?或论曰:“鬼神治阴,王者治阳。阴过暗昧,人不能觉,故使鬼神主之。”曰:“阴过非一也,何不尽杀?案一过,非治阴之义也。天怒不旋日,人怨不旋踵。人有阴过,或时有用冬,未必专用夏也。以冬过误,不辄击杀,远至於夏,非不旋日之意也。
图画之工,图雷之状,累累如连鼓之形;又图一人,若力士之容,谓之雷公,使之左手引连鼓,右手推椎,若击之状。其意以为雷声隆隆者,连鼓相扣击之音也;其魄然若敝裂者,椎所击之声也;其杀人也,引连鼓相椎,并击之矣。世又信之,莫谓不然。如复原之,虚妄之象也。夫雷,非声则气也。声与气,安可推引而为连鼓之形乎?如审可推引,则是物也。相扣而音鸣者,非鼓即钟也。夫隆隆之声,鼓与钟邪?如审是也,钟鼓不而空悬,须有笋虡,然后能安,然后能鸣。今钟鼓无所悬着,雷公之足,无所蹈履,安得而为雷?或曰:“如此固为神。如必有所悬着,足有所履,然后而为雷,是与人等也,何以为神?”曰:神者,恍惚无形,出入无门,上下无垠,故谓之神。今雷公有形,雷声有器,安得为神?如无形,不得为之图象;如有形,不得谓之神。谓之神龙升天,实事者谓之不然,以人时或见龙之形也。以其形见,故图画升龙之形也;以其可画,故有不神之实。
难曰:“人亦见鬼之形,鬼复神乎?”曰:人时见鬼,有见雷公者乎?鬼名曰神,其行蹈地,与人相似。雷公头不悬於天,足不蹈於地,安能为雷公?飞者皆有翼,物无翼而飞,谓仙人。画仙人之形,为之作翼。如雷公与仙人同,宜复着翼。使雷公不飞,图雷家言其飞,非也;使实飞,不为着翼,又非也。夫如是,图雷之家,画雷之状,皆虚妄也。且说雷之家,谓雷,天怒呴吁也;图雷之家,谓之雷公怒引连鼓也。审如说雷之家,则图雷之家非;审如图雷之家,则说雷之家误。二家相违也,并而是之,无是非之分。无是非之分,故无是非之实。无以定疑论,故虚妄之论胜也。
《礼》曰:“刻尊为雷之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为相校轸则鸣。”校轸之状,郁律垒之类也,此象类之矣。气相校轸分裂,则隆隆之声,校轸之音也。魄然若{敝衣}裂者,气射之声也。气射中人,人则死矣。实说,雷者太阳之激气也。何以明之?正月阳动,故正月始雷。五月阳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阳衰,故秋冬雷潜。盛夏之时,太阳用事,阴气乘之。阴阳分争,则相校轸。校轸则激射。激射为毒,中人辄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坏。人在木下屋间,偶中而死矣。何以验之?试以一斗水灌冶铸之火,气激{敝衣}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体。天地为炉大矣,阳气为火猛矣,云雨为水多矣,分争激射,安得不迅?中伤人身,安得不死?当冶工之消铁也,以士为形,燥则铁下,不则跃溢而射。射中人身,则皮肤灼剥。阳气之热,非直消铁之烈也;阴气激之,非直土泥之湿也;阳气中人,非直灼剥之痛也。
夫雷,火也。火气剡人,人不得无迹。如炙处状似文字,人见之,谓天记书其过,以示百姓。是复虚妄也。使人尽有过,天用雷杀人。杀人当彰其恶,以惩其后,明著其文字,不当暗昧。《图》出於河,《书》出於洛。河图、洛书,天地所为,人读知之。今雷死之书,亦天所为也,何故难知?如以殪人皮不可书,鲁惠公夫人仲子,宁武公女也,生而有文在掌,曰“为鲁夫人”,文明可知,故仲子归鲁。雷书不著,故难以惩后。夫如是,火剡之迹,非天所刻画也。或颇有而增其语,或无有而空生其言,虚妄之俗,好造怪奇。何以验之?雷者火也,以人中雷而死,即询其身,中头则须发烧燋,中身则皮肤灼焚,临其尸上闻火气,一验也。道术之家,以为雷烧石,色赤,投於井中,石燋井寒,激声大鸣,若雷之状,二验也。人伤於寒,寒气入腹,腹中素温,温寒分争,激气雷鸣,三验也。当雷之时,电光时见大,若火之耀,四验也。当雷之击,时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验也。夫论雷之为火有五验,言雷为天怒无一效。然则雷为天怒,虚妄之言。
难曰:“《论语》云:‘迅雷风烈必变。’《礼记》曰:‘有疾风迅雷甚雨则必变,虽夜必兴,衣服、冠而坐。’惧天怒,畏罚及己也。如雷不为天怒,其击不为罚过,则君子何为为雷变动、朝服而正坐乎?”曰:天之与人犹父子,有父为之变,子安能忽?故天变,己亦宜变,顺天时,示己不违也。人闻犬声於外,莫不惊骇,竦身侧耳以审听之。况闻天变异常之声,轩迅疾之音乎?《论语》所指,《礼记》所谓,皆君子也。君子重慎,自知无过,如日月之蚀,无阴暗食人以不洁清之事,内省不惧,何畏於雷?审如不畏雷,则其变动不足以效天怒。何则?不为己也。如审畏雷,亦不足以效罚阴过。何则?雷之所击,多无过之人。君子恐偶遇之,故恐惧变动。夫如是,君子变动,不能明雷为天怒,而反著雷之妄击也。妄击不罚过,故人畏之。如审罚过,有过小人乃当惧耳,君子之人无为恐也。宋王问唐鞅曰:“寡人所杀戮者众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曰:“王之所罪,尽不善者也。罚不善,善者胡为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毋辨其善与不善而时罪之,斯群臣畏矣。”宋王行其言,群臣畏惧,宋国大恐。夫宋王妄刑,故宋国大恐。惧雷电妄击,故君子变动。君子变动,宋国大恐之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