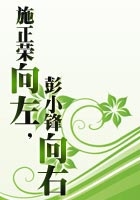1921年春天,张幼仪征得徐家二老以及二哥、四哥的同意,一个人坐着邮轮远赴欧洲。在徐志摩眼中,三年时光眨眼间已经流逝,还没来得及回首,就已成为永久的记忆。可在张幼仪眼中,三年显得那么漫长。她痴痴地等待,痴痴地守候,只为如今的相逢。
第一次坐上邮轮,第一次看到茫茫大海,也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去看一个她这辈子深深爱着的男人。可一想到他那双冷冰冰的眼睛,还有一句句如针扎的话,所有的兴奋在一刹那间灰飞烟灭,徒留下浅浅的呼吸,在微风中飘摇。
不知道过了多少日子,也不知历经了多少海风、多少大浪,她终于看到了朗照的旭光,看到了绵延不绝的海岸线,还有一座座已然熄灭的灯塔。那里就是法国的马赛港了,徐志摩说要在港口接她。
矗立在甲板上,任海风吹动长长的秀发。她紧张得心脏仿佛要跳出来,寸寸急促,寸寸不安。就要见到他了,也终将抓住那双炙热的手。一辈子那么短,她不想在孤寂的岁月中悄然走过。张幼仪下了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梭。她的视线在繁华的马赛港扫过,又轻轻闭上眼睛,任无比惬意的海风吹着自己。
可睁开眼的那一刻,她的视线突然被一个人抓住。
他穿着黑色的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白丝巾。清晨的柔光穿过行人的肩膀,笼络住那人极不情愿的眼神。他在东张西望,又不断地打着哈欠,仿佛来接她只是一个义务,一个身为丈夫应尽的责任。
可那不是爱,不是两厢情愿,更不是在花前月下,轻声许下不变的誓言。张幼仪沮丧地垂下头,心中瞬间划过一个不好的念头: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因为他是那堆接船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儿的表情的人。
想到这里,张幼仪的心突然冷了一大截。就像被人活生生地泼了冷水,在孤寂的灵魂深处又结了冰,开启了漫长的冰封。
走在陌生的小道上,他一言不发,只是沉沉地抽着烟,随后又灭掉烟丝。
张幼仪垂下头,余光时不时掠过那双紧蹙的眉宇。她不敢正眼瞧他,从结婚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彻彻底底地败给了他。
很久之后,她才从嘴角挤出几个字:“我们……我们要去哪里住?”
徐志摩冷冷地吐了一口气:“放心,肯定比乡下的房子要好很多。”
张幼仪哦了一声,不敢再往下说。他的话总是那样伤人,以一句乡下人的冷语,狠狠戳中她柔软的心脏。他不知道的是,那是她多年来最痛心的地方,一次两次,她已经伤痕累累。
几经周转,两人终于在伦敦郊外的一所民居中安稳下来。初来伦敦,她常常不敢出门,更不敢一个人去买东西。一想到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张幼仪心中总会有小小的怯懦。
可徐志摩整天在外面奔波,又在伦敦大学攻读学习,也只有晚上才能回来,算作陪她。所以,很多时候她要学着独立。有些东西真的需要,即便害怕得两腿哆嗦,她还是会出了门一个人去买。遇到不熟悉的人时,她只能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晚上回到家,她早早做好晚饭等他来吃,又将地板拖得干干净净,生怕他嫌脏。有时候徐志摩的衣服脏了,她就会第一时间帮他洗了。在伦敦比不得家中,徐志摩常常有很多应酬。上个星期,他的衣服晚洗了一天,第二日清晨没有晾干,张幼仪正在厨房做早饭,不想被一句叱骂惊扰。她走出厨房的时候,徐志摩已经拿着那件衣服来到她的跟前,没好气地问:“不是说今天干的吗?你看现在,我哪还能穿?”
张幼仪迟疑了好大一会儿,最后才从唇角挤出一句话:“对不起,我去帮你吹干。”
徐志摩看也不看地紧锁了下眉心:“不用了,我再去买一件新的吧!”说完,兀自转过身去,一边拿着湿淋淋的衣服,一边没好气地说:“还不如雇个保姆,想什么时候洗就什么时候洗呢!难不成我还要求着她洗,她不洗我就不能穿了?我徐志摩何时要看着别人脸色行事!”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像针扎般刺入张幼仪的内心。也许她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每一次打击都将成为努力改变的原因。
在伦敦住的这段日子里,徐志摩的一个好朋友狄更生常常来家中玩耍。他们二人谈起来常常毫无节制,有时候很晚也不睡,有时候甚至要通宵。
张幼仪白天做了很多工作,又是买菜,又是洗衣服、做饭,空闲的时候也会做小兼职,赚些外快贴补家用。所以,她的作息时间很严格,往往十点不到就睡觉。但徐志摩和狄更生一谈就到午夜时分,她常常被吵得睡不着,便一个人坐在床头看书。实在困得受不了了,就躺下眯一会儿。但屋子外的两个人哪有停歇,嘈杂的议论声总是没完没了。她沉沉地睡着了,没一会儿又被巨大的吵声惊醒,方再起床看会儿书。
日子在不温不火中流逝,她宁愿自己承受无尽的委屈,也不愿离开他一分一秒。张幼仪和徐志摩在伦敦住了一段时间后,由于徐志摩荒废的学业和兴趣爱好的转移,他在英国的好朋友狄更生的帮助下,从伦敦大学开始往剑桥(旧时译作康桥)大学转移,夫妻二人也便搬到了距离大学六英里的小镇沙士顿。
张幼仪每天都起得很早,踏着清冷的晨光一路小跑,到附近的集市收罗便宜的青菜和生活必需品。而她的那些被现实积淀的理想并没有在欧洲生根发芽,她也没有如愿获得继续学习深造的机会。只有无穷无尽的生活负担压着她,让她喘不上一口气。
徐志摩的挥霍是无度的,尽管徐申如给他寄来不少的学费,但在剑桥大学攻读的那段时间里,他常常跟着一群中国留学生抑或是英国好朋友没日没夜地聚会。无论什么时间,只要有了兴致,都会成为取乐的好日子。
渐渐地,他的生活费紧了,就将贴补家庭的费用降到最低。迫于无奈,张幼仪不得不减少各种开销,自己又打些零工来维持微薄的生活。
一天清晨,她起床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干呕。起先只当是昨晚吃得过多伤了胃,但到医院去查才得知一个又惊又喜的消息——她怀孕了,她要当妈妈了。
这是在异国他乡得到的最好的消息,也是缓解她和徐志摩感情的灵丹妙药。
张幼仪心中想着,如果徐志摩知道她有了身孕,那冷冷的眼神,冷冷的不屑,会不会在晋升为父亲后烟消云散?一定会的,她从来都没有这么自信过。
傍晚时分,徐志摩一个人踉踉跄跄地回到家中。他醉醺醺的,应该是在外聚会时喝了很多酒。张幼仪小心翼翼地扶他坐在沙发上,又取来热毛巾,轻轻放在他的额头。正当她出去换洗的时候,只听堂屋里传来一声沉沉的呵斥:“你过来!”
她战战兢兢地走过去,放下刚要系在腰间的围裙:“什么……什么事情……”
徐志摩拿起茶几上的医院检查单,没好气地问:“你怀孕了?”
张幼仪点点头,脸上浮现出一丝喜悦,浅浅的,如同含苞待放的花儿。她在憧憬着以后美满的生活,徐志摩不再冷傲,家庭不再冷战。
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一句冰冷的话还是硬生生地扔了过来:“打了!”
“什么?”张幼仪不敢相信地抬起头,惊诧地问道,“为什么打了?我听说……我听说打胎会死人的……”在那个年代,医疗条件还很落后,如果不是被逼无奈,很少有女孩选择堕胎。因为堕胎的死亡率和风险系数都是极高的,没有哪个男人会拿着这样的事情当儿戏。
徐志摩微仰起头,将检查单重重按在桌子上:“你听说过火车吗?火车也常年出现事故,你见哪个人不坐了?”
一句话,又冰又冷。
她从未想过自己的丈夫会变成这个样子。明明是欢欢喜喜的一件事,在他眼中却成了厌弃的事,成了久挥不去的梦魇。
1921年9月的一天早上,徐志摩告诉张幼仪说今天家里要来一位客人,而且还是一位女客人。那一刻,她的心被层层忧虑塞满。女客人,会不会是他喜欢的女孩?又会不会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带着浓重的英国口音?
很早的时候,她就知道徐志摩的这些性子。他喜欢和洋人打交道,喜欢那些超越封建礼教的东西。也喜欢在碧海蓝天下,任自由的翅膀驰骋。他是一个随性的人,朋友很多,对他人更是慷慨大方。
可回到家里,面对守旧沉默的她,却怎么也好不起来。
张幼仪有时候在想,也不知道自己上辈子做了什么错事,才会让她最爱的男人以如此冷酷的态度对她。
那天清晨,在阳光漫洒的门外传来爽朗的笑声,透过碧绿色的爬山虎传进张幼仪的耳朵里。听清脆的声音就知道,女孩一定是极好的。也许这就是徐志摩心中喜欢的那种女孩,不受传统礼教拘束,是向西方文化看齐的新女性。突然间,她的心被一股自卑笼络,迟迟没有抬头看那个女孩的勇气。
袁昌英收起淡淡的笑容,轻声问:“想必你就是张小姐吧?”
张幼仪迟疑了一会儿,木讷地回答:“对,我是。”
袁昌英笑了笑:“不知道今天来有没有打扰你和志摩的生活。”
还没等张幼仪再说话,徐志摩忙接了一句:“你不来的话这里反而空寂寂的,少了原有的热闹。袁小姐的到来,瞬间使得寒舍蓬荜生辉啊。”
听到徐志摩的回答,张幼仪不敢再多说什么,她的视线只是在袁昌英的身上瞄了两眼。
一时间,阳光温暖地洒过来,照在袁昌英干净的衣服上。她剪着一头又短又清纯的发式,唇上抹着暗红色的口红。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而在穿着肉色丝袜的两条腿下,竟是一双穿着绣花鞋的小脚。
这样的装束明显与她新式女青年的性格格格不入。况且袁昌英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毕业,算起来也是极早接受西方传统文化的女青年。可是,她仍旧摆脱不了缠足的厄运,只能带着三寸金莲了此一生。
想到这里,张幼仪不禁暗暗叹息。一个人会有多少无法摆脱的过往,如同漫过苍穹的大雁,飞得越高,摔得越痛,又像断了翅膀的蝴蝶,再美丽再妖艳,也不过是断翅飞翔。她要坚强,因为除了自己以外,世上任何人都不会留下怜悯之心。她也要努力,让自己尽可能地改变,以适应徐志摩对新式女青年的向往。
送走袁昌英后,徐志摩突然把她叫住,脸上拂过一丝淡淡的憎恨,就像还没有融化的冰块,等待着热温的降临。他点着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又吐出大大的烟圈:“你觉得袁小姐怎么样?”
张幼仪想了一会儿,笑着说:“袁小姐落落大方,长得也很漂亮。她说起话来就像黄鹂鸟,反正我觉得挺好听的……”徐志摩叹了口气,不耐烦地说道:“你明知道的,我要问的不是这些。”
张幼仪哦了一声,不理解地压低声音:“那你……那你想问什么……”
徐志摩又抽了一口烟:“我想问你,对袁小姐的穿着打扮,还有她的装束有什么看法?”
原来是这些,其实她一早就看出来了。她不想过早地暴露自己的想法,更不想在徐志摩询问之前说出。因为她也曾裹过脚,也穿过脚尖细长的绣花鞋。在徐志摩的世界里,只要有缠过脚的嫌疑,一辈子都是被封建固守的人。
张幼仪想了好大一会儿,垂下头沉默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坐在大堂沙发上的徐志摩已经抽了两根烟了,明显没有了听下去的欲望。他在烟灰缸里按灭了烟头,刚想开口之际,张幼仪突然回应了一句:“她穿的衣服和打扮都是极好的,只不过小脚和西服有点儿不搭。”
徐志摩先是冷笑一声,继而露出愤愤的目光:“你一早就看出来了对不对?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
其实徐志摩心中一早就有了这个念头,如今每天看着不爱的张幼仪,他心中总是会出现一抹厌恶的感觉。
啪的一声,她手中端着的茶具突然摔在地上。
恐慌,惊悸。
那两个字如同飞针般刺到她的胸前,浅浅浮现殷红的鲜血。
疼,那是从来没有过的疼,隐隐作祟,泪水盈眶。她付出了那么多,为了徐志摩甚至不惜放弃所有能放弃的可能,但到头来终究躲不过离婚的厄运,他终究要弃她而去。
这件事仿佛乌云般笼罩着她,躲不掉也挥散不去。从此以后,徐志摩每次回家都会耷拉着脸。他不愿多瞧张幼仪一眼,甚至常常带着明显的不屑。
但对于张幼仪而言,一切又都是那么稀松平常。
每天清晨做好早饭,亲自盛好米饭放在他的跟前。徐志摩不喜欢吃中餐,她又学着做西餐,以讨他的欢心。中午的时候,他有时会回来得很晚。为了不让他吃剩下的饭菜,她直接将凉菜存起来留给自己,反而另做一份新的给他吃。傍晚时分,徐志摩常常喜欢泡个热水澡。张幼仪每天黄昏必然帮他烧开水,只为等他放学回来后有一个舒服的沐浴时间。
如果说爱一个人是不图回报,那么张幼仪就是爱他最疯狂的一个。但这样的日子没能持续几天,一周之后她又陷入无尽的困顿中,因为徐志摩像幽灵一般消失了,不回家也没有任何消息。自打嫁给他,张幼仪深深地明白了一个道理,他从来都是那么的随便,如果不想让别人找到,自然有各种方式藏身。
秋风扫过颓靡的街道,一片片落叶如细雨般缓缓坠下。她抬起头,看向蔚蓝色的天空。即便是空寂无物,却还有几朵白云飘飘然飞过。而她呢,终究是一个人,仿佛那把被遗弃的扇子,在秋风中瑟瑟发抖。
况且如今她的肚子里还怀着孩子,那幼小的生命是感受不到父亲的冷酷的。他只会潜伏在母亲的肚子里,想着有朝一日出来,想着看看这个世界,洞悉未知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