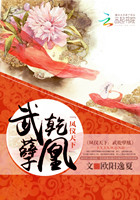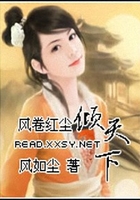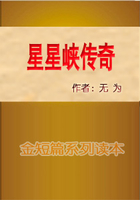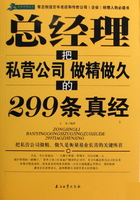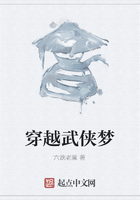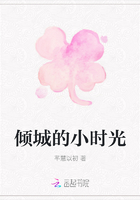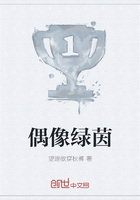笔迹,却是秦王的。
失窃的人家,是临安最大的富户袁家。秦王与袁家交好,众所周知。
缴获的赃物里,有一部分,甚至本来就是属于秦王府的。
袁家的人很快就被请进了刑部衙门。管事的媳妇很快就辨认出了其中一些失窃的赃物。但是对于那一封信,几乎所有的人——包括袁家的真正当权者,都摆出一副莫名其妙的神情,大呼冤枉。
孟士元束手无策。孟嘉龄向父亲提出:“袁家之所以不肯承认这一封信与自己家有关,不过是因为这一封信事关重大,而他们又想求秦王府能够相救罢了。如今之计,不如釜底抽薪。”
孟士元问儿子:“计将安出?”
孟嘉龄道:“袁家之所以收到这封信后不立即烧毁,一定是担心秦王日后得势,翻脸不认人,要拿自己家灭口。既然如此,我们不如暗地泄露消息,将袁家之人分开关押,只说秦王要置袁家于死地。有不明白事情的,必定露出口风。”
孟士元依计而行,拘禁了袁家上下百余口人,只告诉他们,他们涉嫌盗窃秦王府珍宝,理由就是盗贼从他们家盗窃出来的赃物。又让人含糊告诉他们,告状的是秦王府。秦王府深受圣上喜爱,刑部决定要重办此案,袁家灭门在即。攻心政策之下,有小仆人终于忍不住供诉:“所有珍宝,都是秦王秘密赐予,我曾亲手接受,接手之人是某某。”又有小仆人供诉:“我家老爷与秦王交往甚密,常有来往书信,我就曾亲手接送过,交接之人是秦王府的某某。”
孟士元要对袁家的几个首要人物动刑。孟嘉龄却阻止父亲:“尽管袁家的主事之人拒绝供诉,但是已经改变不了他们与秦王府交往甚密、意图不轨的事实。父亲又何必多此一举?”
孟士元到底不是笨人,儿子一句提点,立即让他恍然大悟。做刑部尚书,审理这样的案子,审理不出来,那是无能;审理太清楚,那又绝对不行。
如果真拿到了袁家的口供,那六皇子秦王是死定了。但是,六皇子毕竟是皇子,关系到皇家体面。如果不给皇帝留一点回旋余地,谁知道皇帝日后会怎样整治自己?
这就是政治。没有公理,没有法律。
但是,孟士元也有疑虑:“如今这一场,我们是将六皇子往死里得罪了。如果不将案子完全撕出来,六皇子有翻身余地……”
孟嘉龄微笑:“父亲,您不了解圣上。圣上是最有杀伐决断的人物,这样的情况禀告上去,定能够促使他下定决心。六皇子是再也翻不得身了,您只放心。何况就最近的情况来看,皇上属意的,是燕王,不是秦王。秦王即使在圣上的庇护下能保全一条性命,但是在政事堂的干涉下,他是再也没有继承皇位的机会了。而等燕王即位,他与秦王是结了死仇的,还能容许这位叔叔翻身?而爹爹今日的作为,已经为燕王立下大功。”
孟士元听儿子这么一分析,心中一块大石才落下来。又将秦王府的几个门客叫来问案。不过是施加了一点威压,那名门客就承认自己知道秦王通过袁家与一些江湖豪客隐秘交往的事情。尽管那名门客当夜就自杀了,但是口供已经录下,皇帝的钦差在边上旁听,这一案件已经是铁板上钉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