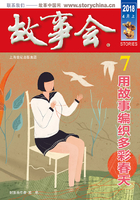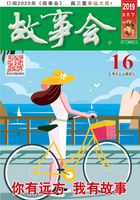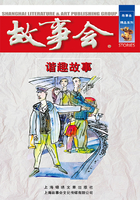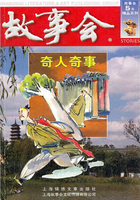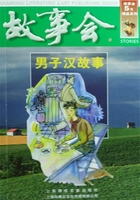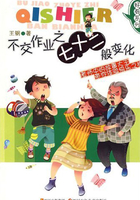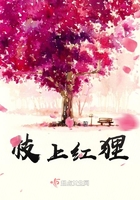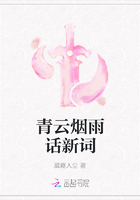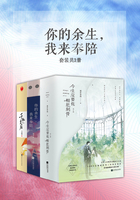《青年作家》:您的绘画创作和诗歌写作有一些共同点,比如都有一个凝结、蒸腾的过程,文学或者语言文字在其中是帮了您很大的忙的?比如您带学生做的乡村调查实践,还有您总是愿意写一些东西,它们是您逃离“潮流”的一个方法吗?
叶永青:我是对过程有兴趣的人,比如我们今天的艺术史或者文学史,都是以作品为中心的,“作品中心论”。对艺术的讨论,都围绕作品本身,比如说它的画面,它的价值,它在今天跟人的交往(互动),但是作品在产生之前,一个艺术家跟作品之间的关联性,跟时代、跟生活发生的关联,可能现在不太有人去关心,就是它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生态里面(产生的)?比如成都的艺术家跟这座城市的关联,它的社会的条件,它的文化的立场,这些东西慢慢就被遮蔽了,最后就是“作品为王”的判断。包括诗歌也是,比如北岛、芒克他们的诗歌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白洋淀这样的地方能产生这样的诗歌?为什么四川美院一些年轻的学生在黄桷坪那么边远的一个地方能爆发出影响中国美术史的东西来,它的社会条件是什么?这些东西慢慢地被今天的“成功学”遮蔽掉了。但是对我来说,我经历、见证过它们的产生,我知道今天被奉为经典的作品在圆明园当年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哪些作品可能更具有真正的意义,但是在今天可能就完全被人遗忘掉了,这个是我们不会忘的,我还能保持原来的那种观察,原来的视野。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回到你刚才说的把其它的方式也带到艺术里面来。这两年我开始回到像中国古人开始画册页的心态,我觉得这是最有意思和最鲜活的东西。我也回头去看一些像“明四家”文征明的作品,我一直都喜欢文征明这样的状态,他就是属于越来越老而弥坚的一种人,而且到后来对艺术、对生活的认知,包括对社会相关的常识,所有东西都能接入画中,到了游刃有余的地步。他们中间最生动的、最打动我的东西都是册页。比如唐寅、仇英、文征明作品里真正很正式地去画一个“鸿篇巨制”,那一般都是“订件”,画山水或者平原的那些图的时候,不约而同就会冒出老师的影响,就叫“仿古”、“慕古”的时候,他们的一个老师,叫周臣就会在他们身上出现,因为周臣太强大了,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座“大山”,所以总是能够看到周臣的影子。但是只要他们一出去,画一张在太湖或者洞庭游览,边走边看边写的状态,那是真正的精品,最鲜活的东西。那时候也没有别的东西,原来那个慕古的东西也不见了,就是那棵柳树,真正的,实实在在地在太湖边上长的树,那几颗石头,那些芦苇……唐寅画得最好的图示在我看来不是那些侍女,而是他画的《采莲图》,像这些就是在过程里产生的,它保持了一种鲜活,还会有一些偶得,那些只言片语,不知道从哪里来,就是在他可游可行可居的一个过程里面,就像偶然的收获一样的东西,这个是最有意思的。它不来自经典章节,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章法,但所有以前所受章法的影响又接入。
所以前一段时间我就一直想着用一种册页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比较方便,艺术又重新回到一个跟“我”的关系,就是我能够携带,成了能携带的艺术。我喜欢旅行,这样在旅行过程中艺术又跟“我”有关。九十年代我去欧洲,箱子里是一大堆做旧了的丝绸,去到任何一个地方,有一点时间,我就在丝绸上画画,画完了就放在箱子里;另外我带的是一些手工纸,是丽江抄东巴经的手工纸,一卷一卷的,所以那个时候画的画都是手帖,手帖上的故事有点像日志,有点像我们今天发的一个微信或者微博,都是片断的东西。
文字让我觉得写出来的不是恰当的,老是“错”的
《青年作家》:您有没有想过只从事写作,还是思考和经验的成果就直接归到艺术里面去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艺术家和诗人作家们的这些区别的呢?
叶永青:很有幸地我总会认识一些作家或者诗人,有时候不小心就和他们成为朋友,就像邻居街坊啊,耳濡目染会经常读到他们的作品。每次看到他们表达出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就心生敬意或者自惭形秽,我觉得我根本不是这方面的料。我无法把写作当一个作品,但可以同时把绘画和写作当一个作品,我是一个可以始终保持温度、保持感知、保持视野的这样的人,这更合适,我始终还是一个边走边看边想的角色,没有终点,一直都在路上的一种状态。另外就是我始终对文字有一个洁癖,画画我有规划,每一个阶段要做什么东西,画了就算了,比较简单,但文字让我很忐忑,让我觉得写出来不是恰当的,老是“错”的,(我写)文字老是在“纠错”的过程中,这个让我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自信”来。今天早上有一个五千字的文章我要
删到两千五百字,这个对我来说就很难。因为我没有什么文字写作的基础,我写出来的要么是故事,要么是温度,要么是场景,这些东西我要删掉就什么都不是了,我不是一个建立结构、框架,某种技术写作的技巧的人,可以把很多无关紧要的东西删掉。我写东西是很本能的,其实跟肉身有关,是跟你的体验有关系,而不是抽象出去的一个纯粹的语言化的东西,或者一种技巧。那么把这些东西取掉以后我真不知道能剩下什么,(可能)骨头也不是骨头,肉也不是肉,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弱点。
《青年作家》:我也喜欢看您的文字,它们非常均衡,直觉、思辨、视野,包括叙述,都相当精彩,没想到这也是一个您自我“博弈”的结果。
叶永青:嘿嘿嘿,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
《青年作家》:写重庆的那篇稿子您改了一上午吗?
叶永青:昨天就开始改了,昨天晚上回来想想又开始改,改到现在。我觉得改了真的就好了,原来是有点罗嗦。其实我不了解重庆,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但它就是和我没关系,我了解的就是一个叫“黄桷坪”的地方,但黄桷坪这个地方全部是像刚才我说的,需要你用肉身去体验的。我对这个地方有感觉是你一定要有好的身体,一定要全情投入。那个地方夏天很热,冬天很冷,还有那么多漂亮的女孩……要爬坡,要上坎,要渡船,全部要靠体力。所以在那个城市生活,要有幸福感的话,一定是一个身体特别棒,性格好的人。幸好我们是年轻的时候投入到这个城市里去的,它需要你用青春和体力去挥洒,包括它和成都完全不同的性格……我是想写出这样的感觉,它其实没什么意义。写作一旦为别人去写,它就有职业化的要求,你要了解这个杂志这一期的主题,它要两千五百字,跟我刚才的描述完全没有关系,我的写作还是要退回到那五千字去。两千五百字,那就是一个活儿,我就干不了这个活儿,是吧?文字上的这个东西和我们在绘画上艺术上是一样的,我也干不了为别人画画的活儿,只有回到自己在别人看来很累赘的东西上面去。但知道这样一个标准在的时候我们可以调整,原来你在写作的时候不太去注意的东西,比如说结构、节奏,主要的线索,段落的意义等等,自然而然你得面对,而且调整之后好像是要好一点,起码站在另外的角度看是更有意义的。
《青年作家》:但您刚才一谈到对重庆的那种感觉,我就“懂了”,张晓刚老师也提过,大概是说在重庆的学生岁月是一生中最“苦涩”的时光。
叶永青:我也写过,我们几个是重庆最早期的现代艺术“最苦涩”的种子,因为没有人做这个事儿,选择做这个事儿就是全靠自己,但是也有几个和你惺惺相惜的伙伴。
艺术家的身份其实还是关于是否真的“有话要说”
《青年作家》:做艺术和写作相比是不是要愉快得多,没有这么多反复的纠结的东西?叶永青:一样的。只是我现在的经历比以前好得多,就是我可以放得下所谓的艺术和写作,如果我做不出来,又不能放低要求,不能(通过作品)保持你和世界的关联,就只能放弃。现在我已经有了这样的心态,也有这样的尝试,我曾经长时间,有大半年或小半年完全和艺术没有任何关系。很多人都说叶帅不画画了,就去做策展,去写作,我就是没有感觉了。九八年九九年我开始回到云南,我真的觉得艺术没什么意思,这是对你原来觉得津津有味的东西的一个“出离”,换一个角度去看原来你觉得很有价值的东西,原来的很多东西一下子变得“索然无味”,这个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只有“放一放”,然后你又想回去完成画面上的东西,这可能是一种习惯。八十年代早期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我生活在重庆,但我的另外一个参照系是云南,所以当时在重庆每天都在画云南,画西双版纳,我的毕业创作,当时的很多画都是在画西双版纳,然后慢慢地重庆和西双版纳变成一个分不清的结合体,画了很多年。后来我去到北京,觉得这个城市实在是太无聊了,而且很虚假,就是完全活在一个靠想象的环境里,所以我是在北京开始画出黄桷坪的烟囱。原来我不愿意面对的东西,经过这种调整之后也许会在某一个时候会来临。“放下”这些东西的时候,并不是不做,艺术不需要你去“捍卫”,不需要每天用机械的工作去保持,(如果)跟思考没有关系,跟判断没有关系,还是一种浪费,一种懒惰,不过是在捍卫这个“身份”而已。但这个身份其实还是关于是否真的“有话要说”,能否寻找到一个满意的表达。体验是一回事,重要的是(通过)文字也好,绘画也好,你还是要把它转换成一种真正觉得自由的语言——只有语言能够穿越局限。
我做过好几个展览来讨论这些问题,第一个展览是《画个鸟》,画个鸟实际上是双关语,意思是《画个什么都不是》,画得不是东西,这是第一个境界;第二个境界,我还做过一个展览叫《非关鸟事》,画的这个鸟和鸟本身没关
《青年作家》:您后来作品里出现的“鸟”的形象,和“文学”有关系吗?
叶永青:文学也好、艺术也好,想象也好,人们对鸟这个形象的感受太多了,而且每个人有自成一体的解释。其实我是不知不觉地,在每个阶段的作品里都有“鸟”这样的形象发生。当时想出这个绘画方式的时候终止了好长一段创作的时间,我是九九年初开始想这个事情,在九九年末用新涂鸦的方式画出第一张“鸟”的作品。其实当时想出这个绘画方式的时候终止了好长一段创作的时间,也可以画别的,可以画一只猫、一只狗,画一座房子……但冥冥之中就选了一个鸟的形象,画完这个鸟就开始围绕这种方式展开。同时又开始画了模仿一封信,一个潦草的字条,或者一张手稿,但我还是又回到鸟这个形象上来,实际上我就一直在画鸟这个形象。这个形象每个人有一种固定的看法,我用另外的不一样的逻辑来呈现这个形象的时候,它好像更像一个“陷阱”,后来发现我在其中还是有一个情结,我一直喜欢古代文人的画,其中比较重要的两个大类,一个是山水,一个是花鸟,所以我画面上看起来用了很多现代的方法,但它呈现出来好像还是回到优雅和朴实无华的美学里面去了,朴素和华丽并置,还有极简,这样的东西是我画的一个基本面貌。
《青年作家》:说到“陷阱”,您画鸟是用极小的线条一点一点描出来、意会出来的,想给人的感觉一层层剥掉之后其实什么都没有?
叶永青:对,画的是“什么都没有”。我做过好几个展览来讨论这些问题,第一个展览是“画个鸟”,画个鸟实际上是双关语,意思是“画个什么都不是”,画得不是东西,这是第一个境界;第二个境界,我还做过一个展览叫“非关鸟事”,画的这个鸟和鸟本身没关;另外一个就是“像不像”,这是很多人对绘画很执着的想法,自绘画诞生以来人们对它的一个功能需求,就是它画得像张三、像李四,画个猫或者兔子,首先判断它“像”还是“不像”,这个功能后来照相机啊扫描啊,包括图像打印啊,科技发展都把它取代了,已经是这么多年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开始用概念艺术啊,抽象艺术啊,用非艺术来解构这一套关于“像不像”的艺术(执着),让绘画回到绘画本身,而不是一些功能性的东西,一些任何人从儿童的主观描绘变成画得像他爷爷、奶奶的描绘;换个方法来说,像不像“一段亲情”,像不像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是有含意的,比如说我们一块儿度过了一个小时,也可能你不在,我一个人度过了一个小时。我一个人的一个小时可能什么也没做,和你度过的一个小时我一直在说话,你一直在倾听。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情况,我度过的那个小时它不是完全不存在,它可能很无聊,这个无聊感你表达出来,可用文字可用绘画,能不能表达出来?那个无聊也可以是一个形象,对吧?这种滔滔不绝,用语言来覆盖的时间,它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我们今天的绘画,或者任何形式的创作,能不能与时间的感受对应,这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