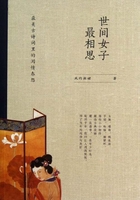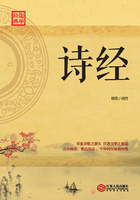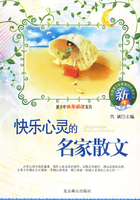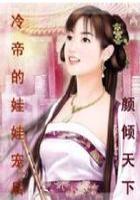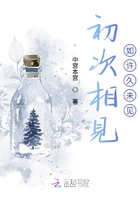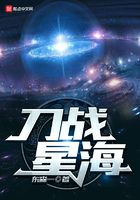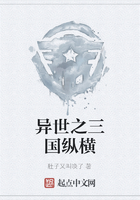对话者:文学批评家张钧
时间:1998年6月24日上午
地点:上海锦江之星浦东南路店
张钧:经商与小说写作,在你的生命中孰轻孰重?你认为两者的关系是协调的还是矛盾的?
夏商:经商就和你在大学里教书一样,只不过是个谋生的职业而已。如果不办公司的话,我也会找一份别的工作。
张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小说写作的?
夏商:写小说是从1988年开始的。其实从小就比较喜欢文学,在学校时文科方面就比较强,历史地理语文比较喜欢,很小的时候就向往着将来要当一个作家或者记者。小时候比较喜欢看连环画,至今我仍然保存着五六百本连环画册。这些画册还很新,以后还可以给我儿子夏周看。
张钧:那么是什么契机促使你走上文学这条道路的呢?
夏商:很偶然的机会吧。那时我开始写一些东西,自由地投稿,也没有通过作家和批评家的特别推荐,比较艰苦。当然后来局面打开了,情况好了一点。
张钧:据我所知,你在写小说之前,好像写过一段时间颇具思辨色彩的随笔之类的文字。
夏商:这个应该说是在写小说以后。我主要的一组随笔发表在《文汇电影时报》的“银色笔记”专栏,后来《华西都市报》和小说家刘庆所在的《城市晚报》拿去转载了。最初,我写的是有关电影的随笔,表达我对电影的一些看法。后来在这个基础之上扩展到对整个文艺的看法。
张钧:你的第一篇小说是哪一篇?当时,你是怎么想起要写那篇小说的?
夏商:我的第一篇小说应该是发在《山花》上的《爱情故事》,但不是一篇很重要的小说。我真正认为第一篇比较重要的小说应该说是《轮廓》。
张钧:你对小说有没有一种自己的美学观念?
夏商:有。但这是一个发展的观念,是一个过程,我估计目前我还在变。1996年的时候,我的小说在文风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为什么在你临从长春出发前一定要你读读发在《萌芽》上的那篇《轮廓》呢?就是因为那篇小说对我有一种特殊的意义。那是一篇很晦涩的小说,语言过于密集,长句子之类的。但是只有在你感受了我这篇小说之后,你才能知道我后来的小说的短句子呀,像杜拉斯这种很清楚很干净的句子呀,像约翰·契弗这样的一种很清淡的清清爽爽的一些东西,都是变化后的结果,但实际上我最早受的还是马尔克斯和法国新小说派西蒙的影响。
张钧:所以就有了《轮廓》这种繁复难读的小说?
夏商:是这样的。但是到了1995、1996年的时候,我的小说就开始变化了,形式上的东西少了,而且没有刻意要去追求什么形式上的东西。一夜之间好像就觉得小说应该是写得干干净净的才对,不要再去故作深奥什么的了。
张钧:所以你在电话里要求我读《轮廓》这篇小说之后,我就把小说带到了路上。我是在昆明读这篇小说的,读了半个上午,读过之后很困惑。这篇小说确实像你在电话里对我讲的那样不太一样,比如意识流式的叙述呀,回旋式的结构呀,一层层地铺展开来的那种感觉呀,倒是都有。但我觉得,也就不过如此而已。
夏商:但是呢,我觉得这篇小说对我来讲还是很重要的。它使我学会了很多东西,比如语言上的那种张力,再就是结构上的一些东西。那是那一个阶段训练的结果。实际上《轮廓》是那个阶段发表出来的一篇小说,还有一些没有发表的类似的小说,都是那个阶段的写作训练。而且当时这种复调式的写作也是一种时尚。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所走过的路还是比较全面的,什么样的写作方式我都接受了一点训练。从“新小说”到后来的魔幻现实主义,每一个流派我在小说中都有过借鉴。
张钧:就像学生一样走一遍?
夏商:对,走一遍。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的,这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我现在和将来的创作,我觉得都是很有帮助的。
张钧:刚才提到法国“新小说”,那么我顺便问问,你对法国的“新小说”怎么看?尤其是罗伯·格里耶,他的杰作《橡皮》《嫉妒》等一度在我们新一代小说家中很有市场,他的小说创作理论如“非人格化”理论在这一代小说家中产生过很大影响。他对你是否产生过影响?
夏商:应该说“新小说”曾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当时有一种非常时髦的说法,就是小说这样写才是小说,所以罗伯·格里耶是我当时非常喜欢的小说家。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想,我现在真正喜欢的小说是杜拉斯的小说。我特别喜欢她这样的作家。我觉得对我来说,有几个让我特别崇敬的作家,读他们的作品我就像读《圣经》一样,杜拉斯就是其中的一位。杜拉斯虽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新小说”派作家,但她的作品却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觉得“新小说”只是提供了一种技术上的东西,这一点西蒙做得是比较不错的,比如他的《农事诗》《弗兰德公路》都是相当优秀的。而在这一点上,我对罗伯·格里耶的评价不是特别高。
张钧:为什么?
夏商:我觉得他在很大程度上是瞎搞。我觉得小说还是得有一定的章法才行。他是一个很会投机的作家,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作家也是靠投机来打江山一样。我觉得小说它应该是常态一点才对,它从一个文本来讲应该是很常态才对。但是很多作家还是要靠一些外部的东西、技术上的东西来支撑。关于这个问题,我前一段时间在《新民晚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对史铁生、韩少功、陈村的三部长篇小说提出了一些我个人的看法。他们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家,但他们还是靠一些比较外在的形式上的东西来支撑他们的小说,像《马桥词典》是一个词典的结构,《务虚笔记》是一种解构,《鲜花和》是一个拼贴的结构。这种对于形式的外在追求,如果他是一个年轻作家的话我会宽容一些,但作为一个已经成熟的作家的话就不太应该。我觉得他们的办法不多,过分地在形式上找出路的作家是办法不多的作家。一个好作家应该是很常态地在好好地写小说,故事呀语言呀结构呀都很常态,这样的小说有力度,有一种控制的力量,就像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那样的小说,别总想着在形式上耍花招。
张钧:现在有许多小说家靠这种外部的东西支撑着,这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内在的空虚无力,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写作策略。
夏商:这的确是一种策略。但这种策略我觉得年轻作家用一用还可以,成熟作家就不应该多用,他们应该老老实实写小说。年轻一代通过这种策略发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声音以引起注意是可以理解的。
张钧:从我的阅读中,我感觉,你的小说从诗学的意义上讲,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隐喻、浪漫、伤感和悲剧性。当然,这几个方面它们有着内在联系。萨·拉什迪在一篇论述君特·格拉斯的短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隐喻”这个词,其希腊词根的意思是横越,指某种迁移,把理念迁移到意象中。而你的小说里,正有大量的这类“迁移”性的东西存在,比如《一个耽于幻想的少年的死》就是一个关于生命和灵魂的隐喻。
夏商:这里有一个关于命运的问题。我的短篇小说,尤其一些青少年题材的短篇,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一个耽于幻想的少年的死》,还有《出梅》《正午》和刚写成的《刹那记》等,我总是要把这些人物放到特定的情境中使他们体验着一种命运。
张钧:悲剧式的命运?
夏商:是悲剧式的命运。不过我觉得从哲学意义上讲,这种悲剧说是不能让人满意的。因为从整个人类的意义上讲,人是不希望自己被毁灭掉的,但是作为个体的人,最终还是要被消灭的。
张钧: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从哲学意义上讲人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人类对于无限生命的追求和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这一对矛盾本身就使得个体生命充满了宿命般的悲剧感。
夏商:这让人感到虚无,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了,尤其在小说当中。所以在小说中我只能拣一些小事,一些我所认识到的人和事,以及我小时候所体验到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听说的一些事情。但我的意图并不是要如何如何强化这些东西的隐喻性,而是要实实在在地写出来。
张钧:但是做出来的效果却是有了隐喻。
夏商:这是可能的,因为你一牵涉到命运,它就会有某种隐喻,某种寓言色彩。
张钧:所以,我认为《正午》也是一种隐喻:人生的隐喻。
夏商:我刚写了一篇叫做“短篇小说的秘密”的文章,我就讲,短篇小说对于题材来讲是有局限的,所有有关命运的东西在短篇中基本上都能出现,而且往往能够以小见大。
张钧:这让我想到一个关于小说的情绪化问题。你要以小见大,就要有所控制,不能情绪化。但是,也有写得很好的很情绪化的短篇小说。
夏商:对于我来讲,我确实是不想在我的小说里过多地出现我的情绪。我觉得小说不应该有情绪,小说就是应该没有火气,就是应该像茶一样,慢慢地煮,这就可以了。
张钧:你的《爱过》和《恨过》这两篇小说好像还是有些情绪化的。
夏商:这两篇小说创作的年份不一样,当时有一种想法,就是写一些好看的爱情故事。另外还有发在《钟山》上的《酝酿》,发在《作家》上的《我的姐妹情人》,都属于这一类的。
张钧:所以,它们给人的突出的感觉就是浪漫色彩和悲剧色彩。
夏商:我写的爱情故事都是悲剧,经常是以男主人公或者女主人公的死亡为结局。实际上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他们要死,但写到最后都不得不死。不过写这类小说的时候想法比较单纯,没有想到什么特别的哲学命题,就想写一个爱情,好看一点的爱情故事而已。
张钧:所以总体上给人一种煽情色彩。
夏商:也有自己真情的流露。
张钧:但我觉得《恨过》那篇小说后半部你没有写好。
夏商:后半部是没写好,有点过于离奇了,好莱坞电影的东西多了一点。当时由于刚刚从《轮廓》那种比较艰涩的小说中走出来,就想轻松一点,好玩一点,就这样写了。这种小说对我来讲都是一些过渡性的作品,从结构的东西走向故事。一度我们都拒绝故事呀,如果你说自己是一个写故事的人就是一个傻瓜呀。
张钧:这是一种偏见。
夏商:绝对的偏见。实际上现在来看,写好一个故事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当然这种故事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故事是不一样的,我理解它应该是某种带有情绪的情节的弥漫。过去的故事比较浅显,现在的故事比较暧昧。这种暧昧的故事表面上看并没有过多先锋的东西,但它实际上对传统故事的那种意义进行了消解。
张钧:当我读到《看图说话》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中篇还是很好读的,还应该算是一篇较好的小说。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将浪漫和悲剧并置呢?这是出于一种习惯还是有某种什么特别的考虑?
夏商:这也可能同我先天气质有关吧。我这个人有点忧郁。这并不是说我在生活和爱情中受到过多大的伤痛,但是,我好像在写小说的时候就自觉不自觉地要从浪漫走向悲剧,因为浪漫和悲剧本身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卖点吧。我从来不否认小说要有个卖点,小说必须要有一个卖点,这样读者才会去读去买。浪漫和悲剧,完全可以把它们分开来。但把它们放在一起,好像更有味道,更有力量,也更复杂化,所以我喜欢把它们搞到一起。另外,我还喜欢把一些侦探小说的东西搞进小说里,比如在《看图说话》里,我后来又让夏娃的母亲来了,把问题弄得既神秘又复杂。但从当初的写作意图来说,这篇小说还是很单纯的,仅仅是为了完成一个形式,因为我的小说形式一直做得不好。
张钧:除了以上所谈的之外,我觉得你的小说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小说与现实的互文性。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应该说是《看图说话》和《嫌疑》。《嫌疑》可以说是一篇关于小说的小说,也就是元小说吧。这篇小说跳跃性很强,叙述像迷宫一样,颇有博尔赫斯的味道,文本意识非常强。请问,你是为了文本意义上的东西才写这篇小说的呢,还是首先感到了某种现实如文本中所表达的那样扑朔迷离,才弄出这么个互文性的文本?
夏商:还是文本意义上的。这个小说发表于1994年,《花城》的文能说他比较喜欢,觉得也比较有意味。当时元小说的概念还不大被人说起,说得比较多的是近两年的事情。当时,我觉得这种东西是蛮好玩的,觉得作者和故事中的人物的关系是很有味道的。这同一般的写作上的虚构是不一样的,它需要作者参与进去,去体验一种什么东西。它对作者的刺激比一般的虚构更强,我也更加地在触觉上张扬一些东西。所以这篇小说我自己还是很喜欢的,它和《看图说话》的写作时间差不多。
张钧:《看图说话》的互文性是多重的。首先是“现实与梦境”,那张男童与女童的图片本来是夏娃梦境中的照片,却莫名其妙地成了现实中流传广泛的印刷品。其次是“现实与小说”,现实中叙述人“我”与夏娃的爱情故事是种让人拿不准的东西,飘忽不定,像小说中编造的故事一样。尤其到了后来夏娃失踪后“我”去寻找,却处处否认她的存在。再就是“现实与文化”,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的名字亚当和夏娃,与伊甸园里偷吃禁果的亚当和夏娃同名,放到世纪末不啻为一种隐喻,并且他们最后的归宿也是一个叫做“伊甸园魔术学校”的地方。
夏商:第一人称的小说有时很难写的,所以这么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张钧:在一些小说中,你喜欢用一种含有既定文化因素的符号来为你的小说主人公命名,比如《看图说话》中的亚当和夏娃,《嫌疑》中的小丑汉斯、维特和盖茨比等,他们分别来自于《圣经》以及伯尔、歌德、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你这样做,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是一种反讽,还是一种嘲弄?抑或如我上面所提到的隐喻?
夏商:是好玩。
张钧:仅仅是好玩?
夏商:可以这么说吧。在写《看图说话》的时候,还有另一个标题,或者说副标题吧,叫做“现代伊甸园”。后来觉得这样过于直白,就把它删掉了。小说人物的命名以及结构上还是有一点反讽的味道的。但是好玩,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张钧:我注意到,你在同我的谈话中,不止一次地用“好玩”这个词,你是不是认为,现代小说写作,“好玩”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夏商:这当然是。小说首先应该是好玩的,不好玩,让读者皱着眉头,有什么意思?再说,作者写作也不会有什么快感。
张钧:我想,这种好玩应该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一些表面的东西才有意思。
夏商:不过我认为只有表面上的好玩也可以,如果一篇小说什么也没有,只是好玩,也是可以成立的。它总比什么也没有又不好玩的小说要好一点。我们过去的小说就是太不好玩了。
张钧:这倒也是。不过最好是又好玩又有内涵。
夏商:无论是写小说还是读小说,对我来讲是一种休息。休息就应该舒服、好玩,不好玩怎么休息。当然在好玩的同时如果能有一种精神那就更好了,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另外,我还觉得一个作家一生中也许只能写出一到两部特别好的作品,而其他作品都将要被淹没。如果这些被淹没的作品连好玩都没有,还有什么意思?所以,我还是认为,首先是要好玩。如果我的小说浅薄,但是好读,并且有很多人在读我的小说,我觉得这就不错。我为什么要搞得那么深刻,搞得那么多思想呢?实际上现在人们的思想都是差不多的,你并不比别人高明多少。
张钧:你的《水果布丁》我觉得就是一篇写得有点好玩,但是又很浅的小说。
夏商:有一句话我可以回答你,我觉得平静的叙述有时会更有力量。这样一组小说实际上是我从去年开始写的,现在这组小说已经写了三四个了,像你刚才所说的《水果布丁》,还有《一人分饰两角》、《金陵客》等等。这组小说的背景都在城市里,并且是夜晚的城市,酒吧呀咖啡馆什么的。人物都是一些来路暧昧的人,故事结构也是模棱两可的。表面上看好像不知道要写什么,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意味的。因为这种平实的叙述,就是事件本身的叙述,当然这里面肯定已经有加工了。这种小说的力量可能要慢慢才能释放出来,可能要通过一组作品才能做到,而不是仅仅靠一篇两篇。所以我估计这类作品我会写到一定的量,也就是量要比较大一点。你提到这篇作品,说明你看得还是比较仔细的,这些短篇和我过去的短篇还是不一样的。
张钧: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人分饰两角》,与《水果布丁》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也让我困惑。可以说写了很多东西也可以说什么都没写,只写了某种状态,都市人的状态。
夏商:这篇也是写城市的,特别是上海这样的城市,写的也是咖啡馆。我是不太喜欢进咖啡馆的。可上海许多人很喜欢咖啡馆和酒吧,特别是一些女孩子,她们喜欢泡咖啡馆和酒吧,她们在咖啡馆和酒吧里能够找到很好的感觉,这是她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我虽然不太喜欢泡咖啡馆和酒吧,但我觉得它们是很好的生活舞台。
张钧:所以你要写咖啡馆和酒吧,写那里的人?
夏商:对。因为咖啡馆和酒吧里有许多暧昧不明的人与事,而这正好符合小说的要求,小说有时很需要一种暧昧的氛围。
张钧:或者说一种暧昧的故事。
夏商:这种故事有可能是被肢解了的故事,它很片断性。
张钧:所以《一人分饰两角》里除了一种状态或者说由这种状态所引发出的三个女人的心理恐慌之外,很难再让人感到什么。
夏商:我觉得这种小说它更多的是一些内部的东西,这些东西慢慢地会蒸发出来的。
张钧:但愿如此吧,只是我现在还没有感觉到。
夏商:这大概需要等待。
张钧:看来只能等待。
夏商:有一个广告的主题叫做“安静也是力量”。我这种小说也是要追求一种安静的力量。平静的叙述,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张钧:这需要作者有耐心,也需要读者有耐心。
夏商:我得尽量把这样一组小说写得好看一点。
张钧:谈到这两篇小说我就想,你生在城市长在城市,思考写作也都在城市,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讲,你对城市的理解应该说是骨子里的?
夏商:我觉得不应该这样讲,因为我一直住在浦东。浦东作为纯粹的上海的一部分是近几年的事,而在这以前它一直是一个城乡结合部。所以我虽然作为一个比较纯粹的上海人,但在过去体验更多的是一种郊区的生活。这反倒对我有些帮助。我觉得,作家不能过多生活在都市的氛围中,特别是大都市,那些过于时髦的地方,那样会使作家失去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张钧:什么样的东西?
夏商:会使人迷茫的东西。比如说一些青年刊物也刊登一些都市故事,但那些故事都过于时髦,缺少一种迷茫的氛围。而小说则需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在真正的城市里不容易被沉淀下来。相反在郊区,在过去的浦东那样的地方就比较容易沉淀,被感觉到。
张钧:但是你的小说写作给人的感觉都是城市化的。
夏商:这是没办法的,因为你还是生活在城市之中。但在内心我还是怀念当初的那种城乡的感觉的,它有一种诗意和神秘感,那种感觉很舒服,很安静,而不像城市那么浮躁。我对上海这座城市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喜欢,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很偶然的缘分而已。我是外埠移民的后代,如果祖辈没有到上海来,而是去了别的地方,那么我现在就是别的地方的人了。
张钧:你的祖籍是什么地方?
夏商:江苏建湖,是个很穷的地方。那个地方已经没什么亲戚了,只是祖坟还在那里。
张钧:你的父辈是做什么工作的?
夏商:我父亲出生在上海,是个船员。母亲在一个运输汽车公司工会工作,他们都已经退休。
张钧:你的小说中有许多巧合的成分,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巧合?
夏商:这也是在小说中一种很难避免的东西。在通俗文学和侦探小说中这是一种必需的东西,但在纯文学中如果运用不好就会弄巧成拙。但我认为,在生活中处处都有巧合,有时候比巧合还要巧合。我所知道的一些故事如果写成小说的话就会显得很假,但它确实就是生活中实实在在存在着的,这是没有办法的。
张钧:你这里所谓的“假”就是一种巧合、戏剧化?
夏商:对。但是我觉得小说如果离开了戏剧性,它就没有一个层次、一个跳跃的契机,就很难向前发展和推进。当然这有一个做得好与坏的问题,从主观愿望来讲,肯定是要把故事讲得好一点,但常常也容易弄巧成拙。
张钧:你在《小说的创意》那篇创作谈里,说小说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艺术,这一点我很赞同。
夏商:在那篇文章里,我实际上只是说了想说的一半。另外一半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把一个小说家比喻成一个垂钓者的话,那么他需要有两种可能性才能成功——一种,鱼要咬上这个钩子;另一种,他要有能力把这个鱼钓上来,有时鱼咬住了钩子你不一定能把它钓上来。
张钧:小说家不能仅仅是在钓鱼,还可能是守株待兔。
夏商:我认为钓鱼和守株待兔是两个概念。钓鱼是积极的,因为我是准备好了才来钓鱼的,是一种引诱性的行为,它已经在催化着一种结果。而守株待兔则是消极的,它只是等待。我知道,如果我在钓鱼,那么我总是能钓到鱼的,而守株待兔,则一点把握也没有。
张钧:你觉得,上海新生代作家与外地的新生代作家在写作上有什么不同?
夏商:我们上海应该说没有什么一个写作的新生群体,只不过有几个人在写作,平时有些接触。总体来说,上海作家比较独立,不太爱扎堆,所以大家小说写得不太一样,不像南京的一些作家有某种相似。
张钧:你认为新一代小说家的小说创作总体质量怎么样——我指的是新生代。
夏商:从长远来看他们当中肯定会出现一些比较重要的作家,当然也会有一些人过一阵子就会从文坛消失。这要看才华和运气。我可以开一个比较有希望的作家的名单,比如李冯朱文韩东张旻等人,他们是有希望成为大家的。因为他们的文学修养比较好,感觉也好。
张钧:你对你自己的写作有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夏商:应该说我的情况稍微有一点特殊,新生代许多人都从事职业创作,他们是专业作家或是自由作家,而我现在大部分精力还是用在公司上,所以我写的东西不是很多,要想客观地评价自己也很难。
张钧:今后你有什么打算?
夏商:今后我会把写短篇小说放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这是由我的情况所决定的。我刚写了一部长篇《裸露的亡灵》,我觉得长篇时间拖得太长,写这个长篇断断续续用了六年时间。公司还要办下去,所以就不可能再花这么大的精力去写长的——这是其一。第二,我觉得我的中篇没有短篇来得好,而我自己觉得自己的短篇要写得精彩一点。第三,我觉得短篇小说是更加纯粹的小说,它更加接近戏剧和诗歌的一些东西,我更喜欢这样的形式。今后几年我的创作量不可能很大,所以我对自己的作品会有一种更高的要求。我会对某一些主题和题材强化一些,比如对成长小说、都市题材等。也会写一些特别空灵的小品,像最近《青年文学》“上海方阵”中的短篇《童年的夜晚》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