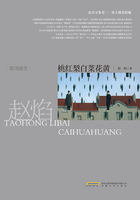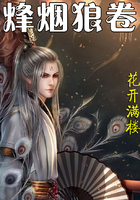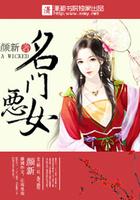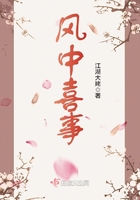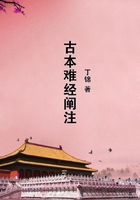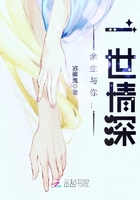对话者:文学批评家林舟
时间:2001年1月4日下午
地点:上海浦东众鑫大厦2301室
林舟:祝贺你的长篇《裸露的亡灵》出版,这部小说最初的创作冲动来自哪里?你在着手写它的时候,对形式是如何考虑的呢?
夏商:我想是来自关于死亡的思考。关于死亡,就跟爱情一样,是一个永恒的文学话题。小说写作的时间很长,断断续续有六年之久。期间也写了很多中短篇,因为时间有限,当写了前面一部分以后,再写的时候,拾起来,总觉得气跟不上,又没有大块时间。但是发表还是很顺利,两个月就发表了。是比较用功的一个作品。
至于形式,实际上我一开始没有特别想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可能到最后,到作品出来的时候,给人的第一印象可能是个形式感比较突出的作品。我的初衷倒并非这样,而是要刻画一个死亡的主题,当然当中会有许多其他的元素,比如爱情、人性、背叛等,会穿插在里面,但死亡还是第一主题。我是希望通过一个故事来把我对死亡的看法和分析穿插其中,使它能够比较直接地反映这个问题。
林舟:从创作的源泉角度讲,故事是否有什么来源?
夏商:没有,这是一个纯虚构的东西,只是题材比较特别。它是一个阴阳相间、人鬼共存的故事。事实上,人鬼故事的题材在文艺作品中并不少见,生死轮回的场景的确有一定的吸引力。通过这部作品,我发现了对那种非常态小说的兴趣。有一段时间我把注意力放在现实方面——对那种卑微的小人物命运的表现——特别是我的短篇小说,当然,这仍是我创作要坚持的方向。《裸露的亡灵》与我前面的小说,像《二分之一的傻瓜》《孟加拉虎》《沉默的千言万语》等相比,想象空间明显放大了。
林舟:我一直觉得你的短篇,写小人物的卑微命运的小说,着力于小人物因为卑微低下而被忽略的内心深处的情感世界的开掘。那么,你在写这部长篇的时候,短篇小说里面的这样一些东西是否也进入其中?不管是作为艺术修养的一个部分,还是对人性的洞悉发现。
夏商:我好像比较固执,我觉得长篇和短篇是两种类型的东西。长篇就是一场马拉松,给写作者带来的精神和体力上的压力非常大,而短篇就是一次速度跑,十天半个月甚至几天就可以搞出来,两者在思维方式上完全不一样。还有长篇和短篇的形式走向也不一样,我不太愿意在短篇上作一些形式性的努力,而对长篇在形式方面的努力多些。短篇应该把故事写得很扎实,或者反过来说,长篇利用形式不是为故事服务的,有时是为了藏拙——手法上的不成熟,或者你容易露破绽的地方,可以把它掩饰起来。我觉得作家无非是通过两种办法来确定自身的定位,一种是你写一个谁都看不懂的东西,甚至包括你自己,大家都吃不准的时候他就不能说你不好——在一个文学不是太成熟的时期,这是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还有一种就是很传统很扎实的小说,像巴尔扎克或托尔斯泰那种,没什么花花肠子,语言干净简洁,写法扎实,但这样的小说如果有破绽,很快会被看出来。我的短篇路子还是会延续原来扎实的路子,我觉得在八千或一万字左右的篇幅我能够把要表达的东西基本上没破绽地表达出来。但长篇我不敢这么说,我相信很多作家都不能把长篇写得非常圆满,没有破绽,前后的搭配和走势都浑然一体,这非常难。两者的用气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一股气,奔跑,结束;一个则是漫长的慢跑,对一个人考验非常大。所以我觉得长篇对我来说还是有障碍,并不是这个长篇出来以后我松了一口气,内心中我还是有点畏惧长篇的。
林舟:像这部小说中,如果从叙事的表层看,死亡是你主要的兴奋点所在。其他,对都市的边缘生活,迷乱的、外在的和内心的,像吸毒同性恋多重恋爱谋杀报复等等,这些东西在近年来的很多作家那里成为一种打造文学时尚的材料,你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这样一种担心,或有没有一种预警装置?
夏商:没有。从小说表面看,这里面包含许多流行成分,可死亡作为文学题材何尝不是一种流行成分,或者说卖点。但有一点很重要,我所牵扯到的这样一些东西不是一种客观叙述,它是暗写的,或者换言之,我没有具体描述一个人怎么吸毒,或一对同性恋怎么搞,细节没有过多触及,我只不过把它作为故事的一种情境来考虑,是为了故事的走向和复杂性而设置,而不是为了卖点。我如果加强它,可能会写得更细致一些,在阅读上更有快感。现在基本上是作为一个背景,用的是伏笔,表现这么一种人生的片断。这可能对故事有影响,但对小说的整体格调不会有影响。
林舟:作为表现死亡的一种方式,小说中亡灵的视角贯穿始终。
夏商:从一个女孩的猝死开始,到她成为灵异,几十个小时中穿插的一些回忆片断,贯穿故事的走向。随着女孩躯壳的消失,故事宣告终结。最初想把它设定在更小的时间概念内,即一天零一夜,即小说的最初名字。后来发现容量上有点问题,不过时间上还是很接近的。
林舟:两天多点儿的时间。
夏商:对。
林舟:从小说叙述的角度看,视角的这种选择有助于在有限的时间里浓缩更大时间跨度的内容,也就是叙述的当下时间和它所涉及的时间的处理。另一方面,它除了带来叙述上的东西外,是否更是一种死亡观念的表现?
夏商:死亡不仅对作家、知识分子而言是一个思考的永恒话题,普通人对它的思考也一点都不怠慢,书当中有几个对死亡的观点,或者对死亡探讨的视角,是平时我在同朋友的谈话中获得的,他们都不是吃文艺饭的。他们谈得很有意思。小说中有一段对话,说人如果要轮回的话,总量应该是一样的,而现在人的总量却在增多。这曾是我的一个疑惑,也是小说中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后来一次吃饭的时候,我问一个朋友,他给我解决了,他说你看现在畜生不是减少了么——非常好玩,很多动物都灭了,变成了人了。这至少成为我小说中的一个理由。虽然我是作为一个玩笑提出的,但他立刻回答了,有可能是闪念,也可能是平时有过思考。
我在小说中还提到那个少数民族的死亡与轮回观念,与中国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是非常贴近的。死亡永远是人类的一个伤痛,从整个人类来看,结局太悲哀了。个体的死亡固然可怕,但最可怕的是整个人类的最终消亡。我们创造的文明会因为人类的消亡而变得没有任何价值,小说音乐美术建筑,再也没有人欣赏,最后地球剩下的可能全部是老鼠。这从哲学上来说可能是最深重的痛苦,我们现在做的所有事情变得毫无意义了。
林舟:终极的无意义。
夏商:对,当然我们不能这么看。因为终极意义固然重要,但过程同样重要。
林舟:我们还是在有限的视界里看问题。
夏商:非常有限。所以我在小说当中刻画的灵异未必没有。我不是一个有神论者,但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种状态存在。
林舟:给它保有一块空间,一种可能性。
夏商:人这么聪明,忽然之间就没有了,我觉得有点说不过去。
林舟:这个小说的构成方面,实际上有许多并置的事件,开始撒出去,最后收拢回来。那么这个过程中,更多的是依靠一种小说外部力量还是循着小说叙述本身的规律?
夏商:可能两方面都有吧,既有小说本身走向的问题,也有我个人的主观努力吧。这个过程非常痛苦,现在想想有点不堪回首。小说时间跨度很长,细节千头万绪。所以我非常佩服那些塑造众多人物的作家,人物多的故事确实非常难写。
我在写作过程中一直把它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写,你看到所有的细节都是常态的,没有变异,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点怪异,但它的果实是正常的。因为隔一段时间要把它重新捡起来,在这个重新梳理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些变化,包括对死亡新的看法。小说最初出来的时候有十五万字。后来一些多余的线索被去掉。
林舟:这里面人物众多,而邝亚滴这个人物相对游离一些。
夏商:这可能还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小说中的一种平衡。小说没有戏剧性是不可能的,但过于离奇或过于巧合的话,有时候会削弱艺术性。一切过于机巧,工于心机。生活中的故事离奇的很多,但还原成小说的话不一定好。从安波的生活故事来讲,很多事情线索都是有联系的,在巧合上已经很可以了。我是有机会把邝亚滴并入故事线索的,但最后我故意让他游离开来,使故事看起来更接近现实性。
林舟:不要让他过于“故事化”了。
夏商:这个人在小说中篇幅是不小的,而且他本身没发生什么故事,主要就是心路历程,忏悔——一个被爱情抛弃的男子的心路历程。他的动作性非常小,整个就是回忆的东西。同其他人物相比较而言,他占的篇幅并不小,但又是个边缘人物。我想,以这样方式结构的小说,它更能撑起来。否则,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物的分离,整个小说就变成一大块东西。现在至少有两个支架,一个粗,一个细,互相支撑,可能更加完整。
林舟:就死亡来讲,你尝试了各种死亡的形态。最震撼人的我个人感觉还是少华和杨小朵的死,而且少华在所有人物中是最具思辨性的一个。在写作这个人物的时候,有没有更多的你个人的东西寄托在他身上?
夏商:少华身上是有一些我个人的影子,在整个对死亡的思考中,少华最深刻。他是最恐惧死亡的,同时也是最能够分析死亡的一个人。实际上写这篇东西的最初,我自己的身体也不好,倒不是有什么大的疾病,而是自己感觉不好,咳嗽不止。在那段时间确实对死亡思考得比较多,感触较多。后来身体慢慢好起来,好像一切都成为过去,但对死亡的思考还是在小说中有所体现。也就是说你有时得想象一下,如果濒临死亡了,死亡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当然我们没有死过,所以未必能够参得很透。但我当时的确把自己设定在濒临死亡的位置上去思考问题——如果发展下去,我的病情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实际上我从未问过医生,自己在那里胡思乱想。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有的进入得深一些,有的进入得浅一些,我有一个朋友老是担心自己生胃癌,其实没什么事,我看他胃口也很好,但他非常焦虑,老是生活在这样的恐惧当中。
林舟:少华对死亡的恐惧和分析都是正常的,恐惧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分析则是一种理性的切入,这两股力量在他身上体现得比较自然,能使这个人物的故事更具有深度一些。另外我觉得,从人物整个的故事上讲,安文理的色调似乎与其他人物有些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在于他似乎很少被死亡的阴影笼罩住,尽管他的爱妻爱女死掉,但他本人却是一个能够独立于死亡之外的人。
夏商:我在写这个人物的时候当时有一个闪念,很多人物都是升华的,唯独安文理是个俗人,我觉得他是世俗的象征,他所获得的很多东西是世俗里面比较辉煌的东西——从表面上看——但这样的人失去的往往是世俗生活中更重要的东西,而且他失去的时候往往是没有感觉的,或者等到有感觉的时候已经悔之晚矣。可能我对官的印象一直不太好,他官又做得比较大。
林舟:你给这个小说设定的基调是怎样的呢?
夏商:我这个小说整个的基调,首先是一个冷静的小说,这种题材必须冷静,才能把它做下来。动作性不是很强,整个人物没有大起大落的变化,包括在写死亡的一瞬间时,我也是尽可能控制住笔调,激动和喧哗的感觉都没有,整个小说读下来肯定是比较压抑的。
林舟:你谈到冷静,但我注意到小说中的眼泪比较多,不知你自己有没有注意到?
夏商:这可能跟我一度喜欢杜拉斯的小说有关系,杜的小说中老是有哭的细节。我曾研究过杜拉斯,她很多小说中都非常容易“哭”,而且很直白——不知是否翻译的问题,“她哭了”,“他又哭了”……修饰上非常简单。但我不觉得她啰嗦,我非常能理解她的那种多愁善感,和她整个的题材相吻合。在这个小说写到后来我意识到,好像比较容易哭,好像每个人都哭过,但这种题材不哭也很难,当中很多人都受到死亡的威胁,关键是怎么哭得更艺术化一点,我好像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在哭上我修辞用得比较少。
林舟:小说中你自己最喜欢的人物是谁?
夏商:整个小说里面其实我最喜欢的人物是杨叉。
林舟:但在这个人物身上你用笔较少。
夏商:是用笔最少的一个,直到小说即将结束时才出现。
林舟:一开始出现过——担架工?
夏商:对。后来我写到他的时候非常舒服,我觉得这个人是最有戏的一个人,但我把这个“戏”用一段叙述解决掉了。
林舟:另一方面,杨叉是否是对少华的一种平衡?我感觉少华的沉闷抑郁与杨叉的达观脱俗构成了某种对应。
夏商:杨叉身上也有我个人某些观念,或者说少华对死亡的思考是我的一半,杨叉对命运的态度是我的另一半。我喜欢杨叉的一半,不喜欢少华的那一半。我现在仍认为,人生是一笔大账,最后总归要结账的,结账后就会轻松。杨叉就是一个非常达观的人,他最后还去找他前妻,他觉得自己已经不欠这个世界什么东西,即使欠,也已经还掉了。看起来是消极的,其实是积极的,所以写到那一段非常快非常舒服。
林舟:所以在整个的阅读感觉中,前面的一段是舒缓的,甚至有一种漩涡的感觉;而后面有一种直流而下的感觉。在前后的节奏把握上有什么考虑么?
夏商:这个倒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考虑,最后可能有点无心恋战,在后面加快一些速度,使阅读更流畅些。
林舟:这篇小说整个的基调是比较简约的,明朗的线条,但我注意到有些地方,比如最初写安波的死,这种场景,你还是花了很多笔墨去渲染,尤其是少华和杨小朵的死,那些甲壳虫的意象,你是把它处理成一个死亡的前兆,还是有什么其他考虑?
夏商:这个可能是小说自然发展的规律,小说前面有个老师——容先生把甲壳虫弹出去,那是一个伏笔,当时写的时候没想太多,后来回到这个场面的时候我发现甲壳虫是一个很好的道具,密布的甲壳虫在玻璃上的话,它可能会变成一个骷髅,或者看上去是一个骷髅,会对本来绝望的少华的意识构成一个暗示。我觉得那一段写得还可以,比较绚丽,而且基本上在写作上是虚写。
林舟:接下来就是写吕瑞娘赶过去,借尸还魂。
夏商:对,这个小说在观念上还是传统的,受中国古代精怪文化的影响较大。我如果受另外的宗教影响,比如基督教,可能不会写这样的轮回方式,会以别的方式描述死亡与生存之间的交替。
林舟:楼夷和安文理后来见面的那一段,我觉得在情节上它的可信度不是太大,你是否觉得?
夏商:那个写得比较早,是小说刚开始时的一段。我可能在写作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这个问题,或者想到了也顺理成章,安波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小女孩,不一定告诉他自己是谁的女儿。这种东西在小说中可能不是特别严谨,但大概不会影响小说的走向。
林舟:作品结尾的小标题是“彩虹主宰着所有人的人生”,这种安排方式是出于心情的考虑还是整个的把握?
夏商:这个是故意的,小说幸好完成于最近,也就是世纪末,如果更早一点完成,那结局肯定不是这样。可能我对整个人生还是持向上的态度,如果把结尾也写得特别灰暗,人生可能就更没意义了,所以这个小说的标题和结尾都有刻意的成分,最后还是雨过天晴,整个大地非常光艳照人,彩虹非常漂亮。这可能在阅读上也更舒服一点,不至于一闷到底。
林舟:就与死亡的关系来讲,或对死亡的思考来讲,这里面的几个人物的遭遇都涉及现代都市的道德危机。
夏商:那只不过是个框架而已。
林舟: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那种道德的危机和情感的危机、人性的危机,它们与死亡之间还是有关系的。这里面死亡是否作为一种现世生活的结束,作为对这样的危机的化解?
夏商:在这部小说里,死亡不是一种结束,人的生存分两部分,阳间一半,阴间一半。
林舟:小说中少华和楼夷还有霍伴,他们的死其实是非常现世的,我们看不到他们的亡灵。
夏商:但我当时在写的时候是看到的,我不想再写了,否则篇幅就无限大了。或者如果写出来就太“满”了,每一个细节都交代出来,亡灵之间还要发生关系,从叙事的角度来说,太满,而且关系太多,所以我回避掉了。
林舟:那么你是否发现所有死后等着复活的亡灵全部是女性,男性一个都没有?
夏商:这可能是一个无意识。
林舟:我当时想夏商是否对女性更照顾一些。
夏商:你现在说了我才意识到,实际上是一种无意识。
林舟:我还想问的是,现世的结束,现实的各种各样的情感冲突,也就是死亡的各种原因或死亡的各种契机,它们与死亡本身,在你看来,是否可以纳入到“结账”的考虑?比如同性恋、情感的背叛、乱伦等是否作为人们恐惧死亡的产物?
夏商:我当时就是觉得如何评判一个人对死亡的看法,确实比较有意思,就像我小说中提到的,如果所有的人一起死亡,那么死就不可怕了,或者恐惧的程度就削弱很多。请想象一下,假如在一个孤岛上,有一千个人,他们已经生活了许多年,相濡以沫,然后突然有一天说全部要死亡了,一个都不活,我估计他们对死亡的感觉不会太强烈——反正是作为一个群体的彻底的消亡。但如果当中有一个人犯了罪,必须被处死,其他九百九十九个人还活着,这种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孤独的问题,一个人赴死和整个人类的集体消亡。死亡是自己和心理的一个战争,一次承受的问题。
林舟:小说在进行的当中,像楼夷这样的人物,对他们的经历描述,实际上你在避免道德化的判断,这个是否是有意识的?
夏商:这可能是我个人的人生观的反映。关于社会现象,除了特别明显的犯罪以外,我还是比较宽容。
林舟:你不把它看做一个社会的道德问题?
夏商:只要他不伤害别人。我觉得就像吸毒是人类欲望的源泉之一,人类很多东西上瘾了,无法戒掉了——我最近开始写新的长篇《乞儿流浪记》就是表现这个过程,比如食物,戒掉会死;性欲,戒掉会产生很大的问题;还有权力欲,也是没法戒掉的。而吸毒就是一个幻觉的欲望,也会上瘾,我甚至怀疑人在原始的时候是有过幻觉功能的,比如做梦就是遗留下来的一种幻觉方式。
林舟:做梦是遗留下来的一种幻觉方式,这个说法有意思。
夏商:可能人类曾经有过比这更高级的幻觉方式,只不过经过生理的进化,法理的制约,逐步消退了。然后通过某种药,比如大麻,把它唤醒了,所以我从来觉得“吸毒”这个词是不准确的,它应该叫一个“过瘾”之类的词。包括同性恋这样的现象,植物界还有“雌雄同体”等现象,它可能是我们人类还未完全认知的东西。在这个层面上我是非常宽容的,我在小说中没有写出他们的大是大非,有些看似过错的东西我也是一笔带过,我不愿从法理上或社会道德的层面对他们作过多的评述,更不想做卫道士。
林舟:从小说来讲,你把小说限定在艺术就是艺术这个范围之内,我想这可能也是这部小说之所以是纯文学的原因。通俗文学总有一个既定的观念去指导它,像“三言二拍”的惩恶扬善,而且这种主题是大众都接受的,不是超越现实之上的。你讲的这点我非常认可。但小说中涉及少华乱伦的一节,是以追述生平和忏悔的语调来叙述的,但轻轻带过,震撼力不是特别强劲。我觉得这里是有戏的,它跟一个人赴死时的心境是有关系的——有太多的因素让少华去死,他不得不死。病只不过是他生理上的一种原因,他表面上是一个很光彩的人物,实际上处于严重的分裂之中。所以如果这里能对他琢磨更多一点,也许可以表现更多的东西,譬如,人面对死亡为什么会如此恐惧,而如此恐惧的一个人为什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能够决定赴死。
夏商:对,一笔带过。可能也是因为当时无心恋战,到最后就收缩掉了。
林舟:还有一点在小说中我感到不太均衡的,有的语言色彩特别明晰,虽然它表现的是一个抑郁的主题,有时候叙述上却有些粗糙。
夏商:嗯,特别是最后的部分。
林舟:《裸露的亡灵》是从什么角度去命名的?
夏商:《花城》杂志首发的时候叫《全景图》,出单行本时改成现在这个名字。“全景”是一个很大的范围,我要表达的是很多人眼中的世界,这些人或这些鬼的眼睛看到的世界。在这些人的眼中,它是一个全景。
林舟:还有小说中与少华构成对比的,是安波死后见到的死神。死神的出现及她与安波的对话,表现了对死亡的超然。坦然接受,把它看成一个自然的美好的事情。
夏商:里面好像有一句话,死神看上去漂亮是因为她集聚了生命的精华,死人看上去很丑陋是因为耗尽了生命的精华。
林舟:很精彩。
夏商:死神这个形象我在海明威传记片中看到,其中不止一次地出现了死神,穿着白色的衣服,站得很远,非常漂亮,非常具有震撼力。而且我发现,死亡好像是跟母性有关系的,死神好像从来都是女性形象,男人外形的话,多半是厉鬼。还有我刚才想说的一点就是小说背景是模糊的,没有放在某个具体的城市,比如南京上海等,但它看上去是个中国的城市。
林舟:不仅仅空间的,具体的时间背景也是模糊的。
夏商:大致可以看出一个时间范围——上世纪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我的短篇也是这样。除了个别作品会出现具体的城市和时间,绝大部分我愿意虚写。虚写有很大的好处,我没有包袱,另外,更能符合一种普遍性。它是一个中国故事,而不是太具体的某个城市的故事。
林舟:从大体的性质讲,人物的活动环境之类,它还是一个都市背景下的故事。
夏商: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小说场景就是都市和乡村之间的地带,我觉得那是最神秘最出故事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出现歧义的地方——只有在城乡结合部,才会出现一些怪里怪气的人物,很多有意思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城乡结合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