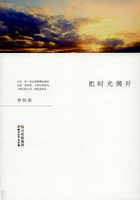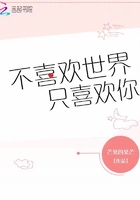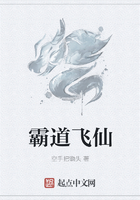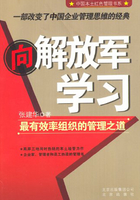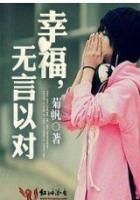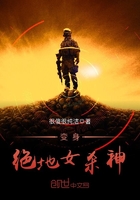1994年,我与家人从西安移居到美国康州的纽黑文(New Haven),至今已二十年整。haven一词义为港口,同时也隐喻“安全、避难和适宜休养的处所”。这是大西洋海域伸进内陆深处的一个海湾,隔一段狭长的水域,与纽约的长岛隐约相望,自古以来,Quinnipiac部落的原住民即生息栖居在此处。1638年,牧师John Davenport带领一批英国清教徒移民从印第安人手中买下这块土地,始兴土木,殖民建城,遂以“纽黑文”这个新名取代了原地名Quinnipiac。从此以后,这处安静的海湾日益成长得名副其实,经不断增加的殖民者长期经营,的确发展成一个安全、避难和适宜休养的海湾小城。比如在1660年,有两位曾签署英王查理一世死刑处决令的大法官在查理二世复辟后遭到追捕,他们逃至纽黑文,立马获得城主Davenport的庇护,被安排在城外西岩(West Rock)的山洞内安全躲过一劫。一战后大批意大利移民涌入该城。二战中大批犹太人相继移居此地。五十年代这里的教会人士和慈善机构大力救济穷人,又招致大量的黑人远道投奔而来。越战期间,有不少搭载东南亚难民的船只在此登陆,那些难民随后即被安置在这一带居住。小小的城区内,虽因地段不同,学区有别而存在着“好区”或“差区”的区别,但各个社区内的住户皆安分守己,自得其乐,基本上过着平淡闲逸的日常生活。包括我教书的耶鲁大学在内,据说其创建者当年也是嫌哈佛大学所在地波士顿都会繁华,城市嘈杂,相约几位志趣相投的朋友,选中了偏僻幽静的纽黑文,草创起这所在新英格兰排行老二的大学。
这所学校建校已三百余年,其校历严守建校以来的传统。每学年分春秋两季学期,每学期授课十三周,复课一周,考试一周。春季学期内有两周春假,学期在五月中旬即告结束,在九月初开学前放暑假长达三个半月之久。秋季学期内有一周秋假及感恩节假,学期在十二月中旬结束,在来年一月上旬开学前所放的圣诞节假也有二十来天。学生放假,教师自然随之停课,总括起来,我们教师每学年有差不多五个月都没有教学任务。在此期间,教师均可安享课外的所有假期。校方尤其重视每个教师的隐私权,不管各人的教职高低不等,所分的房间大小有别,每个教师总是会拥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室。我们东亚系中文部共有十来位中文教师,大家各去各的教室上课,各回各的办公室做事,门一关即把一切闲杂人员置于局外。每个人均在各自的空间内做自己的事情,自然大大减少了同事间互相干扰的是非和麻烦。教师们多住在离校园较远的郊外住宅区,东西南北,四散开来,各选各习惯喜爱的小镇租房或买房,课后无事即驱车回家,分别去忙各自的事情。一年到头,同事间很少有校外的人际往来。这种恬淡如水的人事关系正好让我这类独来独往者如鱼得水,其松散放逸之况味,恰如庄子所云:“鱼相忘于江湖,麋鹿相忘于林。”因此就我个人的情况来说,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回到家中,都有充足的时间阅读和写作。
我从前在国内教古典文学,写作的方向以古典文学研究为主。来到耶鲁当外教,专门教美国学生学习中文。这工作虽与古典文学教学相去甚远,但所融入的生活环境却让我颇有如往而复之感,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增强了我对古典精神的体认。谈诗词者常提到境界的问题,那境界不只显现于文本,同时也涉及接受者的心境及其身外之境。中国今日的城市,在某些方面的后现代化恐怕已远甚于欧美,而生活在美国的大学城及其郊外住宅区,在我看来,反而有不少方面让人联想到前现代中国的山林和乡野。对比起故国今日红尘万丈的都市,目睹这异域的草木烟云,很多失之东隅的经验,如今的我,竟意外地获取了得之桑榆的欣喜。这样看来,阅读和书写就不只是完全陷于文本层面的操作了,潜沉涵养式的玩味和领会,也可充实阅读和书写,别有其日常活动中的乐趣。总的来说,这里的人情是冷调子的,饮食起居是慢节奏的,社会状况稳定少变,生活习俗守成念旧,二十年来,除了物价上涨,路上的车辆增多以外,整个的市容和街景都维持着与旧为新的面貌。人与人相见,大都和颜悦色,善意问好,但相互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不可逾越的距离。可以说,正是这样的环境以及在其中涵养的心境,构成了我写这本随笔评论集的文化氛围和情意资源。
我从前在国内出版过几本文学研究论著,大都涉及有关情色和女性主义批评的话题。来美初期,仍沿袭原有的方向,曾一度贪读不少相关的英文论著,也写过一些评介西方性别理论的文章。这几年来,间或有出版社来信索稿,问我是否还有类似于那本《身体和情欲》的新作可供出版。我说我早已兴趣转向,多年来都在专注百年中国文化谱系的研读和论述,有关情色方面的话题,虽断断续续应约写过几篇评论,但远不足以凑够清一色的专题结集出版。收在这本集子内的几十篇长论短评,既有不少涉及情色话题的旧作,也旁及后现代文化语境中诸多有趣的现象和中英文畅销佳作的评论。其中大部分文章曾在《万象》、《南方周末》和《上海书评》等报刊上登载,也多被转发到网络上广泛传阅。现将这些文章分编为说诗、谈色、评书和创意四类,合为一集,定名为《诗舞祭》出版。取这个书名,是按近来书市上流行的做法,从集中抽取一篇文章的篇名来命名全书。它即使未必能涵盖全书的内容,至少也足以突显高光,聚焦出一个切中肯綮的亮点。
我练习写作始于写诗,硕士论文专攻唐宋诗词,出版的第一部专著即论述古典诗词。用《诗舞祭》这篇旧文的篇名做本文集的书名,也意在怀念一位逝去的诗人故友,祭奠我们生于四五十年代的一代人在八十年代初期为歌舞娱乐的正常化而付出的代价。读完此文,读者将会发现,本人不只曾一度热衷论述情色书写,也因介入某些娱乐场合而招惹过有伤风化的嫌疑。该文多年前曾在文学期刊《红豆》上发表,有位陌生的诗人阅读后惊恐万状,曾激动到夜不能寐的地步。他写了首长诗贴在网上,我现在把该诗节录如下,权充当我这篇短序的结尾:
凌晨 大概是两点钟 我放下书
光着身子 我要去厨房 抽一颗烟
为了平息康正果先生带给我的激动
《红豆》上有我的诗 我读不下去
也不愿意去读 写下就完了 便和过去彻底划清界限
我翻检着目录上的字符 在《诗舞祭》三个字上停住
很好,够形而上,说谁呢,胡宽
他好像也是一个写诗的人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知道的
但他死掉了,猝死,“命运扼住了他的喉咙”
所以有了这篇激烈的悼文 写得真好
首先我回到了那个年代 传说中恐怖的年代
但这些人却活得快活 无所事事 东游西荡
画画 搞艺术 跳舞同样跳到太阳扶山而立
他们同样付出了代价 “转型期的痛苦” 一个姓马的女人 他们固定的舞伴
被处以死刑 罪名是耍流氓和聚众跳舞有伤风化
这是真的吗 读到这里 我毛骨悚然
我想到了一个词:革命的先驱
伟大 英勇 永垂不朽 但没有一个是适合她的
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这个可怜的人儿
后来的文字 多是评论 ……
我只看到一些容易做到的优点:认真 真诚 不骑墙 不沽名钓誉
他看到的是一个诗人的死亡 一个诗人作品背后的世事乱相
他画出了一幅诗人以诗歌抗争的灰色草图
他的目的不是要争夺话语权 他不屑
争夺一个死者的诗歌遗产……
康正果
2015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