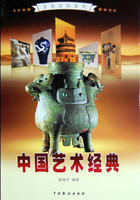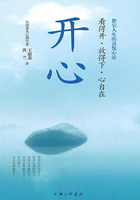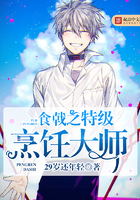一
我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舒芜先生的名字了。那是“文革”最激烈的日子,上海作为“一月革命”的原发地,风云时起。人心处于昂奋与惶惑之中,每天都在等待、盼望、紧张、害怕……那时我们常常步行一两小时,到地处北郊的复旦大学看大字报,那里永远是各种思想敏感的交锋地和集散地。大约在1970年吧,复旦揪出了一个“胡守钧反革命集团”(其实是一群曾经炮打张春桥的红卫兵),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里不断播放毛泽东当年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所写的按语。那时一个重要的攻势,就是敦促这些红卫兵反戈一击,向当年的舒芜学习。从大字报上看,胡守钧的某位战友还曾问过办案人员:“舒芜后来是什么结果?”回答是:“他与胡风划清了界限,没有作为集团的成员,运动后照常工作。但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他因别的问题,被划为右派。”从此以后,我就特别注意这个名字。
“文革”结束不久,《文汇月刊》创办了,在创刊号的目录页上,“舒芜”二字赫然在焉,他的作品是一组随笔《说“梦”》。这期刊物上全是当红的名家,从巴金到王蒙,济济一堂;别处看不到的名字,则除了舒芜,还有曾卓——后来知道,这两位都与当年所谓“胡风集团”有关,而他们的作品,恰恰是这期刊物中最具特色的。《说“梦”》即后来编成集子的《说梦录》中的篇章,是舒芜先生在寂寞岁月中所写的研读《红楼梦》的笔记,创刊号之后,它就成了这家杂志的名牌连载,几乎延续了整整两年。那天翻开杂志,我先一口气读完这组随笔,作者文心之细,艺术见解之独到,尤其是品味小说时常常迸溅出的那些充满历史感的思想火花,让我顿觉眼前闪亮。从这以后,我知道在所谓的“胡风集团”里,其实有着多么优秀的人物。
很快,我买到了舒芜在那一时期出版的各种书籍,除了专业性很强而文字依然清雅优美的古典文学论集外,还有一册薄薄的散文集《空白》(北岳文艺出版社版),一本更薄的杂文集《毋忘草》(湖南文艺出版社·骆驼丛书),另有与荒芜、陈迩冬、聂绀弩等八人合为一编的旧体诗集《倾盖集》(福建人民出版社)。从散文中,我读出了他的丰富的人生经历和过人的才情;从杂文中,我读出了他思想的敏锐和深刻的现实关怀;从旧体诗中,我更加体会到了他的旧学根柢,并理解了他在研究古典文学时何以能如此得心应手,四处逢源。当时《读书》杂志也不断刊出他的重头文章,更让人感到了他在文坛的举足轻重的分量。
在舒芜先生的文章中,有两点是最让人惊讶也最令人佩服的:
其一,是他对各种人物的历史旧账,记忆清晰,态度鲜明,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说必有据,毫不含糊。比如,对他长期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反右”和“文革”,对古典文学室的各位同仁,对老领导聂绀弩和王任叔(巴人),他都直陈己见。谈到“文革”与为害中华的极左思潮,他简直疾恶如仇。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初所写的讽刺当时与御用写作组“梁效”有关的四位老教授的《四皓新咏》,就曾传诵一时。这以后,在胡适、陈寅恪等日益走红的时候,他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看法,并将有些负面的看法直白地写入文章,并无退缩之意。我当然记得他在“反胡风”时的那笔旧账,我想很多读者也都会联想到这一层:他对别人要求如此之高,如此秉公直言,就不怕别人也这样来对自己吗?但他在写文章时似从未有此后顾之忧。在《毋忘草》中,有一篇《谈算旧账》,是他在此书的题记中专门强调的两篇文章中的一篇,书名的“毋忘”也与此文有关,文中所写的是:对周作人抗战时的旧账决不可含糊待之。此文写于1982年,改定于1983年,尔后作者从事周作人研究,第一篇长文《周作人概观》写成于1986年,中间仅隔三年,可见写《谈算旧账》时他已在从事这一研究了。后来多有人说,“舒芜研究周作人是要为自己开脱”,但事实是,他的研究近乎“酷评”,决无开脱之意,这样的研究明明在教人算“旧账”,又何能“挟私”?可见那些人云亦云的判断,多少都有些想当然了。
其二,是他对一些重要的思潮性的问题,常能提出自己的与众不同的见解,而且决不轻易更改,很有点“反潮流”的意味。比如对“五四”,对鲁迅,那时已渐渐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评价,而他明确地说,自己是“尊五四,更尊鲁迅”,并说出了一番令人信服的道理。又如对旧体诗,那时已渐渐热起来了,他自己早被公认为是写旧体诗的高手,但他公开撰文,称旧体诗不可多做,一做,就什么倒霉的情绪都泛上来了。由研究周作人,他开始了妇女问题的研究,其中涉及一些古代文化名人,如白居易等,因为他们在对妇女的态度上所显示的丑陋,他在行文时忍不住直斥其为“老流氓”。再以后,“国学热”风靡华夏,掩盖着一种“沉渣泛起”的事实,他看不下去,写了《“国学”质疑》,此文有振聋发聩之势,引起了重大反响,各种争论延续不断(顺带说一句,我是此文的经手编辑,我为能编发这样的文章而深感荣幸)。当然,舒芜先生影响最大的还是周作人研究。我至今记得1987年下半年的某日,北京一家报纸因《周作人概观》的出版采访舒芜,谈了“五四”传统的问题,我那时已调到《文汇月刊》,编辑部开会提及此事,大家兴奋不已。舒芜这本书和李泽厚的名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几乎同时于1986年问世,他们从不同途径,触及了同一个重大问题:“五四”传统中的很大一部分,被后来的历史进程掩盖了。这就是人的觉醒,个人的解放,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李泽厚正面论述了“反帝压倒启蒙”,重新提出“新文化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舒芜则通过对周作人传统的发掘,让人看到,缺少了这一面,“五四”精神就是不完整的——这是将周作人研究放到了历史和时代的大背景下,突破了一般文学史和作家论的框架,这一研究本身的思想史价值,是决不可低估的。在这些地方,舒芜体现了一个思想者的品格,他在新时期思想发展中的地位,我觉得,是可以和黎澍、王元化、李泽厚、李慎之诸人相比的(这样的思想者,我以为还有曾彦修、张中行、资中筠、陈乐民、朱正等)。
1994年,拙著《解读周作人》出版了,我没有想到,从未谋面也从未联系过的舒芜先生,竟会在《读书》杂志发表《真赏尚存斯文未坠》的长文,大加称许,使我既感且愧。他在文中多处说到:“今读《解读》,分明地照出我的不足。”“这些话说得真好,我就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还把研读周作人分为五个层次,并说:“对照一下,我自己的位置,大概刚刚够得上第四个层次,这就知道了今后提高自己的目标。”其实我的研究哪里能和舒芜先生比呢?正如金性尧先生后来推心置腹所说:“研究周作人,还是舒芜和钟叔河先开的头,你们都是跟在后面的。”何况舒芜的研究全面而深刻,为后人难以企及。但他看到后生晚辈的一点新见,就充分肯定,欣喜不已,居然还以此来对照自己的不足——这种境界,在今之权威学人中很少见到,在更年轻的一代中则更为罕见。
这以后,我与舒芜先生的交往越来越多,因先后担任了《文汇读书周报》的“书人茶话”和《文汇报》副刊“笔会”的编辑,我常能收到他精美的来稿,并经常有深入的探讨,一开始是通过电话和信件,再后来就是通过电邮了。他是对我帮助最大的前辈之一。
二
我一直想找机会同他讨论“反胡风”时的那段旧案,我知道他不会回避这一问题;而我经过多年思考,也研究了当时的各种资料(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想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研究中去),并结合了自己在“文革”中的体验,对此,我形成了自己的判断。
1997年春,舒芜先生的《〈回归五四〉后序》在《新文学史料》第二期上发表,引起轩然大波。此文讲述了他一生的思想经历,对当年写作《论主观》的前因后果叙述甚详,与胡风的关系也说得十分清晰,最为可贵的,是把自己从解放前夕到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思想转变过程解剖得相当深透。他理出了这样一条转变的主线:从外部看,是随着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看到实践越来越证明党的伟大,从而对自己与党内理论家们(如胡乔木)的分歧开始疑惑起来,正如胡风在1945年6月26日给他的回信中说:“嗣兴兄(即路翎)看过你底信,说你好像慌张了起来,急着想找教条救命似的。”从内部看,则是在参加国统区民主运动和解放初期的具体工作时,在群众运动的热潮中,革命激情升温,引发了对于过去在书斋里和小圈子里形成的思想的批判性思考,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自觉要求——当然事后冷静地看,那是把思想、文化、艺术全都与政治混为一谈了,是用现实政治的标准来裁决一切思想和学术。从外部看,那可以解释为一种害怕,怕被胜利者算旧账,这是他人的判断,却也很可能是当事人的一种潜意识;从内部看,却是一种新生,一种充满希望地迎向新生活的积极姿态。舒芜没有回避这一切,把它们都写入《后序》中了。我以为,从这篇《后序》里,可以读出一个思想者的真实的性格,那就是相信自己今日的思考辨析能力,对一切旧账都不含糊待之,而要一一反思清楚,并形诸文字。这一性格贯穿了他的一生,既是一种天真,也是一种认真,而事实上,也是一种读书人的真诚。
自20世纪50年代初起,舒芜和胡风周围的旧友们越走越远了,因思想道路的分歧也使一些矛盾激化了。但直至后来“反胡风”运动爆发,几乎每个关键的转折点,都是出乎他预料之外的,如他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按语和第一批胡风集团材料在《人民日报》发表时的按语(前者为胡乔木写,后者为毛泽东写),都曾使他大吃一惊;同样,当初的《论主观》在《希望》杂志发表时的按语(胡风所写),也曾使他吃了一惊。他半个世纪后才知道,《论主观》发表后,延安方面曾频频派高层要员到重庆了解情况,周恩来还召集胡风、茅盾、乔冠华等开会,询问此文的来龙去脉,但作为当事人的他一点也不知情。舒芜写《论主观》时才22岁(写《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30岁,到“反胡风”开始时33岁),他是双方交锋时的一颗有点莽撞的棋子,整个棋盘上的冲突和举棋者的深沉思考,他茫然不知,并没有太多的主动权。但在《后序》及相关的《又附记》中,他沉痛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虽非我始料所及,但确由我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确有沉重的历史责任……”把这场全国性的冤狱归结为“由我导致”,这不是轻易能下笔的。说舒芜先生从未认真忏悔,这也是与事实不符的。
《后序》发表后,报纸上出现了连篇累牍的批驳文章,但大多是一种情绪性的斥责,或道德上的贬抑、羞辱,很少有认真讲道理的。这时,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过一篇《阿Q的错误》,对此提出了批评:
近来……我从报刊上读到好几篇文章,都是批评某学者的五四研究的,说他没有“资格”研究五四,因为他历史上有过错误,必须把这段错误说清楚然后方可谈五四。于是我想,如果一定要从来没有错误或把以往一切错误全都认识透了的人才能谈五四,那五四恐怕就没有几个人能谈了。谁没有错误呢?被称为“伟大领袖”的那些人,不也有“三七开”、“四六开”乃至“五五开”之说吗?可见还是有错。当然错误有大小,那要错到什么程度才该取消研究的“资格”?我以为,只能有一个界限,那就是法律的界限,即看他是否已被剥夺了公民权。只要还有研究的权利,就应允许他研究,甚至鼓励他研究,因为这毕竟是一项有益的劳动。哪怕是五四时期臭名昭著的反派人物,哪怕是曹、陆、章本人吧,如果能活到现在,如万一当真恢复了公民权,我们无疑也会鼓励他们写回忆录之类,因这终究是别人无法取代的第一手材料。至于对错误的认识,那就要给人以时间,并要允许各人有不同的认识。一定要别人马上服从自己的认识,不然就不准干别的事,只能一遍遍地“交代”、“说清楚”,这就太过霸道了。虽说有这种想法者自己当年未必“干过写作组”,但这种做法实在容易让人想起那段已逝的黑暗年月。
舒芜先生对报刊上的各种文章,态度十分鲜明:“概不讨论,今后也不讨论。”对我写这类文章,他也是不赞成的。有一次他专门写信来,劝我不要把精力放在这样的争论中,“废时失业,得不偿失”,不如投入到自己的研究中去。在此前后,我还收到过张中行先生的信,也说了相似的意思。他们的爱护和期望之心,让我很觉得温暖。
然而我又觉得,反思这段旧案,从舒芜先生身上,的确可以引出重大教训。问题恰恰不是在道德上,甚至也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出在常识上、人情世故上,或者也可以说,它正显示了一个思想者的最薄弱的环节。
思想者有敏锐的思想,有严密的思维逻辑,他的“知”的一面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但这一面的发达,有时正以其他侧面的相对薄弱为代价。比如,在“情”与“意”的方面,在“知情意”三者的协调上,有时恰恰反而会不如常人。22岁到33岁,这正是人生最动荡的时期,也是最容易犯错的时期,人的思想可以在这一时期迅猛地发展,但人情世故很可能被轻易地抛到一边,“知情意”三者的统一在这时也最难做到。舒芜的《后序》为他的某些旧友所不能接受,甚至觉得不可理解,其中一个原因,是有的人并非同样的思想者,他们很难相信一个人内心的思想力量有时竟会排斥其他的一切。
比如,他的旧友鲁煤,在1951年12月28日给胡风的信中说:“他这种转变是在解放后两年实际工作中,和党的实际工作的领导人接触中体会、学习和摸索到的,所以,当然也会有无限珍贵之处。”在12月23日给徐放的信中说:“我冷静地欢迎他所有的变化和进步、积极性……但我现在还弄不清,虽然我感情上有一大部分接受不了他的新理论。”这是鲁煤到了南宁,与舒芜长谈后的真实心理。他没有像舒芜那样靠思想,靠推理,层层穷追,把难题理得一清二楚,而是采取了一种停顿和保留的态度。他能从理论上理解舒芜转变的思想逻辑,但“感情上有一大部分接受不了”,这就是发现了“知”和“情”的不统一,不统一时没有强求统一,没有舍“情”而独取“知”,这就是他比思想者舒芜高明的地方。
又比如,在《回归五四》一书中,附有当年向舒芜组稿,又向舒芜借阅胡风来信(正是这批借去的信后来成了“第一批材料”)的《人民日报》编辑叶遥的文章《我所记得的有关胡风冤案“第一批材料”及其他》,其中说到,批胡风开始后,报社文艺部负责人袁水拍提出要组批判胡风宗派主义的文章,另一位负责人林淡秋当即说:组织这种稿子,“难度太大”。袁水拍有同感,也认为“难”。后来叶遥接受任务,去找绿原、路翎、舒芜,她也是硬着头皮去的,顾虑重重。为什么?就因为不是胡风的朋友谈不出宗派主义,要能谈出来的,则一定关系很近,要这样的朋友谈这样的问题,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在这里,道理上没有任何障碍,障碍就在人情上,就在于要突破这一人情的“意志”上。最后,只有舒芜答应写这文章,这是他的“意”为“知”所牵了。
当初,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为何迟迟不下手,不为自己的父王复仇?并不是因为他不知情,也并非他不够勇敢,他通过多次试探早已了解了叔叔篡权的真相,但他还没有积累足够的仇恨,在他身上,“知情意”还未统一,这时,他无法像一个刽子手那样动手杀人。莎士比亚正是在这样的人物身上,显示了人文主义的萌芽。而舒芜先生在检讨自己时,勇敢地把朋友也带进去,希望大家能一起跟上时代(《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及了“吕荧、路翎和其他几个人”,当然还不可能不涉及胡风)。在写关于宗派主义的文章时,又大量引用了胡风的原信。这种时候,人情世故的障碍一点也看不到了,它们全都让位于思想、逻辑、新生的激情和对于旧世界的荡涤了。这可以说是“知”的片面发展的可怕后果,也是摒弃了人生的常识的表现。这是一个中国的思想者和哈姆莱特之间的差距;而几十年来革命斗争、群众运动、思想改造的熏陶,不正是要把人推到这样的境地吗?
三
这段时间,我和舒芜先生有很多通信,有的信写得很长。在1999年11月4日的信中,他十分动情地写道:
关于常识与思想,正好我们想到一处了。
最近一些日子,我常常想到坚持用常识看世界之重要,之不易,想到知堂强调“常识”强调“人情物理”之深刻意义,想到他反对“载道”的深刻意义。道,即意识形态。宗奉一种“道”,一种意识形态,结果必至扭曲常识,看世界非复本来真相。记得“大跃进”失败之后,凡是说了几句真话,说出一点饿死人真相的,统统打成“右倾”,说他们“未看到本质,未看到主流”,还归纳成箴言一联云:“一心记住六亿人口,两眼看清九个指头。”那时我暗暗怀疑过:本质和主流,何以成为这么难以看到的东西?然而我又立即自警:这是立场不对!还要痛下改造工夫!其实,皇帝的新衣,无非是反常识之极致;“他是光屁股呀”,无非是常识。安徒生的伟大,也就是在于坚持了常识而已。
……
确如尊论,当时我若尊重常识,便不会一下子把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等等,与个性解放混为一谈,一概抹煞;也不会真心相信思想改造是“与人为善,治病救人”,自己真心求改造,还要帮助朋友一同过思想关;而且,若多从常识看世界,便根本不会那样美化当时的一切,不会据此美化图景证明自己过去之全错全误。我完全不从常识出发,而是一切从思想出发,从理论出发,只有理论上证明其为正确的才想,才看,才做,习惯成了自然。
1957年成了“右派”,仍是自以为懂得了二百方针的真理,自以为参加“鸣放”是符合真理的行为,才陷进了“阳谋”。马思聪后来追述,他之所以在“鸣放”中一声不出,是因为他忘不了仅仅两年之前反胡风的教训,不相信两年之后就有了真正的言论自由。我很惭愧,毫没有他那种合乎常识的看法想法,我真心相信反胡风是一回事,“鸣放”是另一回事,从来没有把二者联系起来。
在同年11月23的回信中,他又谈到了他所熟悉的周作人:
尊论不入门户,“拿来主义”,只取所需,极是极是。回想知堂自称“少信的人”,即是此意。可惜当时没人听他的;我前几年也仍未深解此义,近两三年才回过味来,深佩其所见者远。坚持常识,坚持人情物理,谈何容易!前信说过,回想三四十年代青年之所以群趋于马列者,主要是相信它真正是“社会科学”,相信这一套严格的科学体系,可以一举而根本全盘解决中国的复杂万端的问题,相信其他理论、主义、方案皆非科学。当时青年闻知堂之论,莫不笑其浅,鄙其顽,知道他反“载道”,认为他根本不懂这不是一般的“道”,而是从古未有的科学,从古未有的无产阶级学说。……思想太多,压倒常识,是一面;爱憎太甚,也压倒常识,又是一面。“不以人废言”,人人会说,而极少人做到。章太炎不信甲骨文,说:“国而可卖(指罗振玉),学术何足信?”闻一多反对作旧体诗,说:“做旧诗的,无非是郑孝胥、汪精卫。”还有今之“厌恶家”,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确实是太厌恶,太反感,自然会那么想,不是故作激论。此刻现在,要我相信江青对京剧确较内行(汪曾祺说),我还是不愿相信。……总而言之,人都离不开种种“障”,事后谁都能做诸葛亮,而后之人依样能笑今之人。……
今日回顾,名人之中,百年来真有“独立性”者,恐怕倒是只有周氏兄弟近之。但也只是“近之”,不是全面的楷模。鲁迅晚年,固仍未真正“皈依”马列,但也不免有“左”障;知堂终于落水,固不能说是他的思想的“必然发展”,但终归是不足以自持其方。也许不要找楷模,各人自己“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吧!您以为如何?
2002年3月,舒芜先生写出了《百姓耳目之实》,作为我的一本新书《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代序,他在文中发挥的,大致就是前面信中所说的思想。但他更突出地批判了新旧理教“以理杀人”的危害,强调了“人应该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而到了他的晚年,思想又有发展,他甚至对真理的有无也表示了怀疑,因为谁自认掌握了真理,就可以左右他人,甚至左右一个民族,这是另一种“以理杀人”,不可不警惕。他这时的思想,有点接近于顾准的“彻底的经验主义”,也更近于知堂的“少信”了。一个少年时代的积极的思想者,一个昔日学界、思想界神童式的人物,经过一生蹉跎,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是不是有些苍凉呢?但谁又能说,他经过一生的实践和思考,不是更接近了人世的真谛呢?
舒芜先生是永远的思想者。多少代以后,他仍会是史学家们感兴趣的研究对象。他的著作,他的思想,还有他曲折的一生,则是我们后人永远的财富。
2010年2月19日,写于上海香花桥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