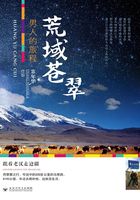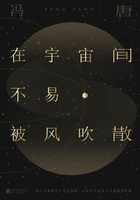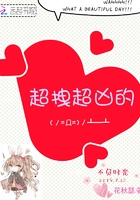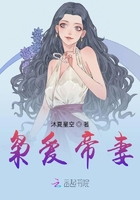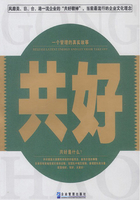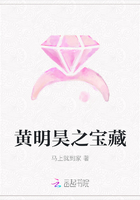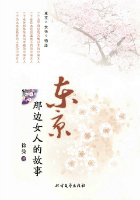为什么要写文?答案可以有很多很多。
为什么答案很多?因为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势而异,因境而异……
载道,文以见意,文以表志,文以寄怀,文以遣兴,文以会友,文以自娱,文以传情,文以致礼,文以应世,文以媚俗……哎哟哟,可真是五光十色,举之难尽。
若到了哲学理论家那里,那么一分析,一综合,大约就总结出两条来了。
哪两条?一曰为人,二曰为己。
就从这儿,就出来麻烦了。
写文而不为人,是为自私,谁爱看你那自私的文?写文而不为己,是为架空,谁爱看你那“遁形逃质”、“缺灵少性”的不见真心真情的文?
如此看来,两头都得管顾着,得有“双管齐下”的本领或“神通”才行。这可太难了。
所以,弄笔之人,总应该掂量自家的才力。学艺的还得讲究“手、眼、身、法、步”,学文的又懂哪几条“歌诀”呢?
这么一想时,真是心虚胆怯,自己拿起一支笔在纸上画些字句,就叫“文”吗?
文也得有“凭值”。虽然就在今世这种“洛阳纸贵,中州文贱”之时势下,写一千字也须“付酬”呢,岂不自量?
圣人早就叹息了:“觚不觚,觚哉觚哉!”咱们“非圣人”,不妨向他老人家学习,东施效颦,而发一警世之言——
“文不文,文哉文哉!”
所以,轻易言文,即胆子太大而近乎“妄”矣。
“文以载道”,硬说它不对,是“弄左性”,因为反对这个命题主张的人,他自己写文时也还是为了载他自己的“道”——只不过他的道与他批评的人家的道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了,用反对人家的道来载自己的道,就大言“文不载道”,那行吗?
要“载道”了,却又要先问了:载道,是为人,是为己?
似乎很好答——既载道,道总是大道正道好道,济世裕民,当然是为人的。
但是,思路一转,就“柳暗花明又一村”起来,他那道自以为是大道正道好道的,实际不如他所自拟自料,而是错了的坏事而害民祸国之道,那么事实就证明他不是真的为人,而是为己——为了宣扬自以为是的“私道”。不是为己又是什么?
所以,“文以载道”这四个字斤两太重,不宜轻言妄动。
于是,聪明之士就不再去考虑什么道不道了,且自谈文为妥为妙。
“非道”之文,在今日似乎就是“随笔”、“漫话”、“浅谈”、“戏说”之类的“文章”或“作品”了。似乎“杂文”较为特殊,多少还要载一点点道的。“散文”呢?好像那是更远些吧?我妄揣浅解如此。
提起“散文”一词,我又觉得它很有趣,也不可解。
文怎么叫“散”?“谁也不挨谁”?堆在一起漫无组织章法义理?
恐怕不是这个意思。
我忽悟及:原来我们历史上有“骈、散”二体,齐名并存的。“散”者,乃相对于“骈俪”即“四六(对句)文”而立名见称的。
于是,所谓“八大家”式的“古文”,其实就是唐时宋世的“散文”。散者,不对句配辞罢了。
那时候,骈文就没了吗?非也。比如打开《古文观止》,不是也收有才子王勃的《滕王阁序》吗?那脍炙千载人口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句,不是一种永恒的文之大美吗?
这种文,今世似乎早已绝迹灭种了。
奇怪的是,早没有了骈文,可还管这些毫无“对立文体”的文字叫作“散文”。这“散”又何所指称、何所寓意呢?
今时还有“杂文”。但又好像没有“纯文”这个称号。这种“一条腿”的现象,该当怎讲?有时有好学之士不耻下问,以此来“请教”于我,我只好回答说,你另请高明吧,我也还要问人呢。
答不上来,愧对问者,愧对自己,就暗自思忖了一番,悟出一个道理。虽未必正确,总比交白卷强些。我这“悟”处,是书呆子式的,因为看到自古的文论大家们都是先讲“文体论”,然后才各下评语。比如魏文帝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莫不如是,如出一辙。这绝非巧合。盖中华之文,最讲究“文各有体”,是并不混写胡作的。后世“创新”了,就不再懂什么叫文体之分别,为什么要分?分了有何意义?统统不讲了,于是提笔作“文”时,管你什么叙、咏、题、跋、铭、赞……都是一道汤,一个味,报纸杂志,报道解说,千篇一律,都那么一个“文体”,一个“笔调”,所以分不出什么是什么,无以名之了,只好就乱叫起来,尽管早没了“骈”,大家都“散”它一回,可谓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