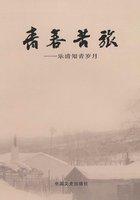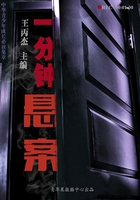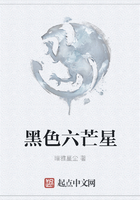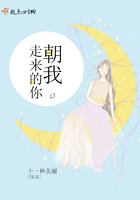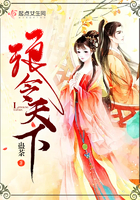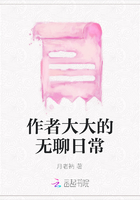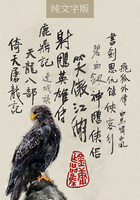那时的南开中学,真了不起,简直是个小学府。我不知道天下有几个中学能像它这样的有规模有气派,学生的知识来源、思想天地、生活实践,都那么不同于“高级小学”式的中学校。我这时的文学活动主要有三方面:研习宋词、写散文、练习翻译,都在校刊上发表过。
但这些刊物已不易寻检,如今仅仅觅得小词数首,于是就选录两篇附于文内,以见一斑,作为“凭证”可也。
浣溪沙
楼下频番见个人,轻帘薄雾看难真。钿车去后恨香尘。檐亚已无云幻彩,栏回渐有月雕痕。闲挑寂寞倚黄昏。
瑶华
辽空似洗,鞋软尘微,识前番新霁。攀邻闲访春寓处,见说西城桃李。轻衫侧帽,便何用、鱼书先寄。唯只愁暗织浓阴,密缀漫枝青子。酸眸不到南阡,早半亩香泥,一溪红水。花应有恨,如诉与、薄幸寻芳迟矣。晕销粉脸,问几载、人须相似。对四围浅浪轻风,十里麦畦翻翠。
我还试用英文译冰心的短篇小说。而且,对“红学”研究,那抽端引绪,也是在这个时期。
但是我们的学习、生活,不是十分安然的,侵略者的炮火硝烟味,似乎一天比一天的浓而迫近了。那时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激起了我们这些青年的强烈愤慨。一个寒假,我们一小群学生放弃了“回家过新年”的乐趣,南下请愿,可是铁路局不让我们这群孩子上火车,我们就下定决心用腿走。整整走了一夜,清晨才到了杨柳青。找了一个小学校“打尖”休息。一看外衣领子,自己呼出的气息已经在上面结成了一层很重的“霜雪”……
我们这级高中生,后来在韩柳墅当了“学生兵”,跟二十九军的营连排长们接受军事训练。除了对待学生是客气得多、照顾得多之外,一切体制都和真的新入伍一样,剃了头,穿上灰军装,发真枪(只不给实弹)。整天一刻不休地到旷地去学打野战,什么“散兵线”呀……当时都很熟习了。我的饭量大得自己吃惊,后来告诉家里人,一顿吃六个大卷子,他们都不信,说我说得太玄。
这时已到了“卢沟桥事变”前夕了,二十九军考虑到我们这一大批学生的安全,只好解散这个特别的青年军营。我们刚去时,自然并不都“舒服”,可是到了这时,我们都被集中到大操场,长官正式宣布因为侵略者的逼近,为了同学们的长远抗日救国的前途,决定解散时,泪随声下,我们一齐哭了。
我还记得那些军官给学生扛行李上车时,我们拉着手依依难舍……
爱国,对于我们这样的学生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诗曰:
门前日日看刀光,年少心胸志慨慷。
深夜步行期抗敌,敝衣曾结满襟霜。
讲早年的事,很费劲儿——几乎每说一句“老话”都得加上“注解”,不然,今天的中学生就会觉得茫然不知所云了。我上中学的时候已经虚岁十五了,那是因为我的小学时代太坎坷:军阀混战,军队一来先占学校“居住”,于是学生停课,一停就是几个月,复课遥遥无期;有时候还闹土匪,所以,加上“逃难”、“转学”,那经历可写成一部书!
我是天津人,出生于近郊的一个镇,离大都市中心有二十五公里路。虽然近郊市镇与农村大大不同,但若进入市里,仍然得被人看作一个乡下孩子。天津这个半洋式都市里的“阔绰派”中学不少,皆是富家子弟的乐园。我上不起,就得找一个省钱、校风朴素的学校。后来我考上了觉民中学,“觉民”的意思是“唤醒民众”。
这所初级中学校规极严,今天的人必定认为太怪了,住宿生有事外出,必须请假,倘若擅自出校门,记“大过”一次,三次“大过”开除学籍。这虽怪,也有好处:学生染不上都市的各种坏习气。还有个怪处,虽是初中,一进门就是三门数学课:小代数、平面几
我读中学的时候
何、三角学。而且这三门课一律采用英文原版书,一个汉字也没有。这下子,新入学的少年们可都“傻了眼”。仅此一例,可见那规矩大,水平高,要求严,真是一板一眼,扎扎实实。这个学校的唯一缺点是“读死书”,不让学生接触课外读物和其他有益活动。
我那时在学校是个“超级生”,每学期大考都名列榜首,同学们送我个外号,大意是“铁第一”。河北乡村来的同学视我为“天人”,老师们也都对我另眼相看。我其实不过是记忆力特强,平时功课不用“温习”罢了。
这三年中,我已经开始给报纸写小文章了。
1935年,我要升高中了,这可是个大关口。当时决意投考名校南开中学(周总理、曹禺的母校),结果入学考试名列第二,获得了奖学金,顺利入校。
一入南开,感觉大大不同,与觉民相反,学校注重“活动”,有社会视察专课,参观各类工厂,学木工铁工,大量接触课外书籍,了解新的文学思潮……
我本来是“门门一百分”的学生,一入南开,便渐渐发生了变化,在“数理化”与“文科”分组时,决意挑选了“文科”。我开始作英汉、汉英翻译(英译冰心的小说,汉译林语堂的英文随笔),也写散文、论文,刊在《南开高中》校刊上。我得到过翻译比赛的奖牌、银盾……
一句话,我从此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今天回顾起来,觉得这两个学校都对我深有教益。虽然觉民中学只让学生读死书,但我至今仍然十分感念母校的长处,严格的训练方法给学子们打下了坚实的课业基础,培养了学生严肃紧张的学习作风,一点儿都不弄虚作假。南开则是活泼开明、创造型的“教育培养精神”的代表,摒弃了“填鸭”式的硬灌,而让不同的学生有不同发展的可能与余地。
觉民是个严训班,南开是个小学府——它真像一座小型的“大学”:连课本都是教师研究自编自创、学校专印的,极富特色,这就不同寻常了。
南开中学门外有两个小书店,专售各种高质量的新书、杂志,学生们买书看书是方便的。除此,我们也喜欢订阅好期刊,那时我订的就有《中学生》和两种英文期刊;几家驰名的出版社如开明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纷纷竞出高水平的中学生读物。至于我个人,读得很杂乱,不足为训,在此不过聊举两三小例,如冰心的小说、何其芳的《画梦录》、外国名著《爱的教育》,还有《红楼梦》等一流的小说名著……可说是古今中外,兴趣很广泛,“胃口”很大。我读书缺乏名师指点,自己摸索,带着“随意性”,这当然是并不尽善的读书方法,不过也培养了我的博览的意趣,开拓了我的眼界心胸——这阶段的成长发育,对我日后的文学文化事业却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营养因素。
奖牌
母校,对我来说,早已成了“抽象的存在”,因为它只在我的“神往”的境界中出现,自从“卢沟桥事变”的侵略炮火把我从母校中赶出来之后,再也没有机会去看看它,把抽象的记忆重新“具体化”。直到今年“龙抬头”日——古谓之中和节,这才忽然回到故乡;热情招待我的单位领导同志问我想到什么地方去,给我提供一切协助,我说,哪里都不想去,只想到南开中学去一趟……
我的愿望实现了。交通工具、联系手续,都替我办好了,我顺利地回到了母校。我只觉得有点像是梦中,半信半疑地踏着我在三十年代经常走的那些地面。“这是真的吗?”我问自己。
“具体化”了。然而还是需要很多的“抽象”来帮助这个眼前的“具体”。我高兴,激动,可是又默然,惘然。人的感情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吧?我自己的感情经验,就常常是复杂的,交织的。
我回到北京,家人不知因为翻寻什么,捡出一件东西,送到我眼前。我一看,愣住了。这是一面小小的紫铜牌,基本呈长方形,上端有可贯皮带的“横梁方缝”,正面两边花纹的形象是蜡烛或火炬,中间靠下是一口钟的图案,斜向左,钟内的铃铛鼻子正击在左壁上,令人如闻响声。钟下还有一丛花叶。钟上是一行横斜排列的四个字:“业精于勤”。再上边,正中一个大篆体(可是方折笔)字:“奖”。
这是什么奖呢?我赶紧翻过背面来,看时,上面却又有五排横列的字迹。第一行是“英文翻译比赛”六个字,铸印凹方格内的凸字。第二行“第二名”三个字,铸法与第一行同。第三行,“周汝昌”三字,是刀刻的阴文,字方端好。第四行是“南开中学奖”五个字,铸法与第一行同。第五行是印就的小凹字,文曰“凤祥金店”。
这是哪年的事?我想起刚刚在津“返校”时孙正恕同志特别把老校刊《南开高中》翻开指给我看,那上面似乎有所记载……
铜牌发着一种像“烧蓝”锻过似的微黝而有“深度”的光,与当年我领到奖品时的光泽没有什么两样。
家人提醒说:好像还有一个小银盾?对,对,还有一个银盾玻璃盒罩——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随诸物不知去向了,比如“南开”的八角校徽的银戒指……都不敢留存的,或后来被人弄丢了。
这个铜牌奇迹般地没有“消失”,只是托衬它的那个小皮带,已不见了。
孩子问我,那时成绩不错呀!我苦笑着告诉他,当时得第二名是心中颇为怏怏不乐的,觉得不光彩,因为从小学到初中,不论何种考试比赛,从未得过比第一名低的成绩呢。所以那时领到这面奖牌时并不是十分高兴。我又告诉他,南开中学像这样的鼓舞学习、奖励成绩的活动是多种多样的。由制作这种奖品的情况来判断,不难看出那是郑重其事,拿着当“一件事”来办的,而不是“虚文故事”,或“草草了事”。
办事认真,是南开精神的一个方面。
铜牌向我闪着那带有“深度”的奇特的光泽。我心中说:你,偶然的幸存者,虽然体积不大,也不够个“连城之璧”式的贵重文物,可是值得珍惜,因为你是南开精神的一个小小的历史见证。
南开忆旧
一
难忘的南开,美好的南开。
在南开中学的岁月,是我青春最好、风华正茂的人生丽景时光,又是邦国危难际会——两者标志着我对南开学习生活中的无限之悲欢,难宣之感奋。
天津的历史,从建城计起,正满六百周年,而南开一校之史,占了六分之一,整整百年之久。仅此一端,令人在史迹寻踪中不禁深觉南开中学的足以自豪,足以显胜。
我和南开中学的负笈之缘,须由我四哥祜昌说起;而祜昌之所以能领引我投入南开,又须从我的老姑丈说起。
老姑丈姓李,“海下”高庄子人。高庄子李家,是那一带最富特色的一个村庄:那儿的教育事业特别先进而发达;高庄李氏的小学、女校,不但是一方仅见的私人办学兴教的榜样,就连市里的一般公立同级学校,也望尘莫及,其声名达于遐迩。
高庄李氏小学——区区一所村郊小学校,其设备之先进,教师之水平,办学思想及教育精神,在当时堪称一流。那么,那是受自何方的影响和感召呢?原来就是南开。
老姑丈和他兄长二人,皆是早期南开学生,与周总理正是同时学子、同窗契友。周总理在放暑假时,就到高庄李家去度假,原因是那儿环境优美,草木芬芳,更加体育设备好。周总理喜欢打篮球,又可在假期创作话剧剧本,于是就和李氏小学结下了一段因缘佳话。老姑丈曾有与总理的合影,正是那时风光的珍贵留痕,后来传为人们时常提及的话题。
——说到这儿,才轮到我再讲四哥:他步入南开中学、大学的小半生的求学良机,就是由老姑丈向父亲一力敦促、建议:必须投考一个好中学,而其首选非南开莫属。
父亲思想跟不上姑丈,把孩子送到了什么“木行”、“铁号”去当徒弟;老姑丈不以为然,从四哥起,这才下决心走上升中学的道路。
四哥在南开的成绩很好,每当假期回家,从校中给我带来了当时极新的少年儿童读物,如冰心、夏丏尊、茅盾等名家作品,也还有《木偶奇遇记》、《阿丽丝漫游奇境记》等译文名著;还有中英文对照的外国名著……他也常给我讲南开中学的学生生活的丰富多彩,令我十分神往而心驰,心里暗自羡慕。
正因如此,我又在他的影响下进入了南开中学的校园,得遂小时候的心愿。
二
寒家本来供不起子弟都在南开上学。我因成绩优异,是南开高中给了奖学金才得就学的——我的初中是河北大经路北端的觉民中学,是个最省钱的初级中学,学生多来自乡下,生活俭朴严格之至。和市里富家子弟集中的高等学校生活是差距颇大的。又正因如此,我一踏入南开,真像进入了另一个境界。
请勿误会:我并不是说南开中学的生活水准就奢华“高贵”了,不是这个意思;我指的是这儿的校风、办学精神,与觉民初中真是大不相同了。
我从觉民初中升入南开高中,第一个强烈感觉就是“南开精神”与众不同。觉民中学是个有名的“棒”校,课程水平高,校规十二分严格,学生“读死书”,课外读物一无所有,气氛沉闷单调。一个初中,数学和英文的教学水平高得令人惊讶——小代数、平面几何、三角学三门全部采用英文原版外国教科书;英文竟又分设文法、作文二专课,是与普通英语教材三堂课鼎足而立的,其水平可知。在这儿,学生只知重视考试“分数”、列榜名次。
一到南开,立刻不同了——在觉民,我这个“门门一百分”的“铁第一”(大考列榜,总平均分数九十八、九十九,没有低于九十七过),只是个规规矩矩的老实学生,也几乎是个“小老头儿”;一入南开,少年的精神这才很快焕发出来,变了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