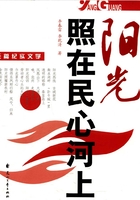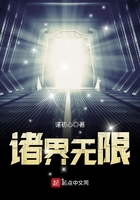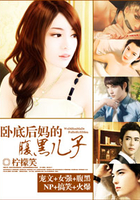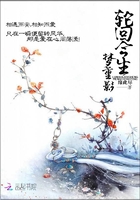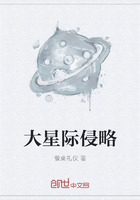高中试行“分组”了,我选了“文”组,因为天性喜文爱艺,于数、理、化、工相远。“文组”的学习、文化活动方式丰富活泼,“分数”不像理科那么“死板”,设比赛,争荣誉,有奖励,但已不同于抠一个死“分数”了。我就在英文翻译比赛中得过奖牌、银盾。奖牌是铜的,铸有图案、格言,皮质的佩带,可以挂在腰带上。
英语教师有顾先生、柳女士,水平都高,口语也稳稳当当,自如流畅。但我那时已经订阅英文报纸杂志,买《牛津字典》,不满足于“课本”范围了。
国文课最受欢迎的是孟志荪先生的讲授,从《诗经》到李后主的词,都很精彩。他一口道地的“津腔”朗诵南唐李后主的“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挥泪对宫娥!”同窗黄裳(本名容鼎昌)最喜仿学,下课后大声学那声调,抑扬顿挫,音韵铿锵,是我们课余的乐事和趣事。
我们的思想自由得很,什么新旧中外都接触了,如当时一批新作家的文学丛书、精刻本的《梦窗词》、洋文原版的名著……一时是兼收并蓄,无所关碍。也无人干涉。
我们的写作生活也展开了,因为有《南开高中》校刊是发表的好园地,我们经常有文章刊出,包括散文、译文、研究论文,也有诗词创作。我有一次将自作诗词送请孟志荪先生评阅,他在卷后写了两句,曰:“参透禅宗空色相,是真情种是诗人。”
我们也开师生联欢会;有社会视察课程,有各种形式的劳作练习。在日寇侵华毁校前,我与四五位同班步行“南下请愿”——要求政府抗日。那种爱国精神,也是南开教育的一大重点。
每逢春秋佳日,或夏季白天日长,课余多暇则晚饭后“溜墙子河”是一乐事,即出校门一直往南走,到墙子河旧址为终点,中间经女校的楼舍。记得与同窗黄裳是每晚必行,行一次则讨论乃至辩论,谈笑风生,旁若无人——主题最集中的就数《红楼梦》为第一位。
那时男女分校,只有到化学楼上大课,女同学才过来,常常是坐在后几排——那是当时唯一的“梯级座椅”的扇面形教室。教师要穿像医生一样的白外衣制服。
南开女中规定的校服虽无特殊形样,颜色则是规制的,一律是“藕荷”色,很好看,男生远远望之,不免有所咏叹,好像有的说那颜色如同晚霞,“哪得这般颜色作衣裳”!
三
南开有“社会视察”课,唐明照先生带领我们到各工厂、机构去了解社会情况,不作兴死读书、读死书。南开精神,毕竟不同于一般者大抵类此。
南开到秋天以菊花驰名津沽遐迩。有一处大花窖,王先生为主持,花种之富之美,不可胜言,每一种都有雅名,如“朝晴雪”、“醉舞霓裳”……十分可爱。
提起这,我还“犯过”“窃罪”:有一次,二哥来看望我,似是周末假日,到午饭时我自去吃饭,他独留于花窖,并无一人同在,他就将最可爱的一二种名花的幼芽从根上掐下来带走——原来菊之生命力最强,根下衍此幼芽甚旺,只要掐一小段,插在土里就会生根成活,长成大株,善养菊爱菊成癖的就如此“偷”取人家的名贵种色。我虽未动手“窃花”,却也做了“副手”,罪有应得。如今,二哥早已不在尘世,而王先生的菊种,不知还如昔年否?记此小故事,或可充为我在南开母校的“佳话”吧!
这些往事前尘,大约知道的人不多了吧?南开中学,美好的回忆,说之不尽。
高中母校忆当年
今年十月是天津实验中学建校八十周年的校庆之期。这所中学是我高中毕业的母校。我毕业于1939年之暑假前夕,其时年当二十二岁。六十多年前在校的情景,历历犹在目前。信笔追记若干片段,作为对母校校庆大典的献礼,那就太寒俭了,而对比我年轻的校友来说,也许有些趣味,或亦不是全无意义可言吧。
你如问我:为何迟至1939年才高中毕业?要回答这一问,可就说来话长了——在此不能详及,把事情简化成几句话:我幼少时所遇的那年代岁月,你是根本无法了解与理解的,连想象也没办法。我的小学时期,是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的民国年间,败兵窜来,占驻学校,要停课,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绑票匪闹得极厉害,民不安生,逃难逃到亲戚家……如此失学苦度岁月。熬到高中二年级,日寇侵华,平津沦陷,学校解散,又是更大的灾难。因为不受敌伪的“亡国教育”,我只能选觅当时在津的教会学校,于是选中了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工商学院的附属中学——这就是我执笔为文以表纪念的母校,亦即实验中学的“前身”。大家口中都称之
为“工商附中”。
工商学院设在天津马场道,校舍建筑很引人注目,最高的是教堂顶部的大钟,很神气。附中则在校园的西端,是平房,教室也很敞亮。但我是高中插班生,高三的教室和宿舍却不在西边,是属于“学院部”了。一切设备,都相当高级,胜过了南开中学。
你会又问:怎么又成了插班生?这是因为,我读至高二,不幸沦陷失学,如不升学,就要被敌伪组织搜去为之奴役,失学失业的青年处境最为危险。而我至此年龄,已到了最后一个考插班的机会,我坚决走求学之路,别无选择。
幸运极了!——问明工商附中这年(已到1938年)招高三插班生,是个少有的奇事。
投考了,——可真难忘却!
那天,上午考第一场“国文”。“送考”的人是我的一位表叔(名刘裕梁),人总是乐乐呵呵,从无戚容。我手执墨盒(现已绝迹的文房用品了)、毛笔等入场,表叔站在附近的一架“双杠”旁等候。不一时,他见我从考场中出来了,潇潇洒洒,向他走来,——他从未有过的惊讶惶恐之色现于面上,急问道:“怎么出来了!——不考了?”我说:“答完了,交卷了。”他不信:“怎么这么快?”我说:“太简易,我都熟悉。”
这下子,他立刻恢复了原有的满面春风,又添上了加倍的欣喜和赞佩之语气的容颜,表示“这太了不起”。
其实,这不稀奇,我从小的语文水平是可以的,尤其是诗词、古代汉文等,有些根底,与一般少年稍有不同,所以看试卷太容易了。
除了“国文”(那时不叫什么“中文”),我“拿手”的还有英文。记得这门考试是笔试与口试两次分行。大约是笔试够格的才要口试。那回,主试的是刘策恩先生。全部问答不过三五语,就满意地让我退场了。他说的第一句是:“Don't be excited...”意思是关照考生不要紧张,慢慢答话。我说:“Oh, no. I'm quite all right.”然后他只问我姓名和原在何校,何以插班。他见我对答如流,语音正确,频频点首,即表示“好了”,示意没有问题了。
以上两门的“光荣史”,却掩不过我在“数理化”方面的“不行”。尤其是数学,我简直忘光了。
我在初中(河北大经路北端的觉民中学),并不如此,那时我们小代数、平面几何、三角学三门全用英文版外国教材,我门门一百分,大考外号“铁第一”,棒极了,连老师都另眼看待,温言和语,视为“特殊生”。可是升高中后,我入了文科班,这些课程久已疏远,兴趣骤减,分数下降——加上失学荒废,再让我做这些复杂的“方程式”和“求解”,我真是“英雄莫论当年勇”,唯有叹气伤怀而已。
面对考卷,计无所出——灵机一动,想出一个“非常”的答案:这儿没“算式”等,却是一段文字!
那段话大意是说:我这种学程经历太不幸、太特殊了,客观所致,非一己之情愿;如其他试卷尚可,恳望数学一项许以宽容,视为特殊,以续我努力求学之路程……
大约这份试卷确实是打动了阅卷的诸位老师。榜发后,我竟被录取了。
这种历史经过,我如不记,谁复知之?
高三的一切条件、待遇,实际上是与大学的规格毫无分别了。晚晌自修的图书馆座位灯明地敞,学子自己用功,无人督促。宿舍每室四人,相处和睦。有好文的(如我),有好武的(运动员)。清晨须早起,而少年们“恋枕”,常常遇见老神父来“查屋”,他推门一看,见大家都躺在那儿看天花板,就以洋调的中国话喊“起来”。学生立即坐起——可他一走,就又躺下,再“享受”一会儿……老神父久而知其情,就第二次推门喊:“起来!”
教师很齐楚,水平也高。我心里有比较:绝不逊于南开,或有过之。英文刘老师,数学周老师,都负盛誉而孚众望,余者亦不稍弱。因是教会学府,所以有一门讲“道”的课,老师名叫申自天,德国人,脾气很好,满口汉语,自编的教材是用德文拼音写中文——坐在台上讲一点钟,滔滔不绝,眉飞色舞——可是谁也听不懂这长篇大论到底是讲的什么;好像也没有什么严格的考试。
另一个日语教员,是沦陷后校方为了应付,临时聘教的,没人真听真学,全是走过场,教员也明知其情,大家“默契”而已。
同学中似可粗分两大类:一是正规的本校生,走读,家在“租界”,富裕家的子弟;一类是老天津卫、近区外乡、饱经沧桑流转的续学者。前者年轻,活跃,天真,淘气,爱动,爱闹(课堂上小捣乱);后者老实,安静,沉默,不出风头,不打打闹闹,似伤“老大”,无复少小时的稚气与朝气了。此二者间似略有隔膜,了解不够——此皆历史时代特殊条件所造成的,今日幸福的学子们,又如何能理解那一切无词以形容的情景与心境呢?
淘气的学生“欺软怕硬”,脾气好的老师上课堂,他们几个就打趣取笑,一位萧先生,取外号叫他“萧二爷”;萧二爷从不发怒,他的特点是一边点头,一边摇手——点头是答问,摇手是“劝”那几个“别闹”。我冷眼看去,觉得十分逗人笑!
好了,又多讲了。我愿年轻校友对于上述“历史”,勿当笑谈,应予深思,你们的时年与学校,是得来非易的。比起我个人来是何等的幸福快乐,应当珍惜,应当努力,不负母校的培育,使自己成为一名有用的英才,为中华民族争取更多的荣誉。
我现存的母校纪念品还有三件:一是毕业证书。上面贴的照片留下了我青年时期的面影。此片亲友都说是我照片中最好的一张。
二是毕业纪念册。这是同学自编自印的,内容颇为丰富。其中有我的词曲和墨迹,代表着我那年代的“精神面貌”。
第三件是一枚银戒指,正面长圆形,有花边,花边内是“工商”二字。内面刻有“周汝昌”名字。还有当时首饰店的印记。记得当时印纪念册和制银戒指,一共才收了二元钱。
这都已成了珍品,是我平生学历程途上的痕迹,十分真实而亲切。
母校八十周年校庆献词
津沽振铎念前修,七二春波八十秋。
驰道马场存旧址,英才骏影树新猷。
工商宜纪富民史,实验方以报国筹。
胜业辉光逢盛典,长怀绛帐溯风流。
入伍
自顾平生,一名村童,经历却绚丽多彩:当过绑匪巢穴中的“秧子”,做过津海关“暂用”小员,教过小学、大学里的课,当过出版社的编辑,进过“牛棚”、“干校”,出过国开会、讲学,做学生时也上过舞台串过戏,在“文场”中弹过月琴……给“老外”讲过《红楼梦》……但最不易忘掉的是还入过伍,当过兵。
那是1936年在南开高中二年级,学生要接受军训。先是在校内,然后是全市各校集中在北部宜兴镇韩柳墅,正经八百地“入伍”。
先叙校内作为军训课程的概况。别校不知,只说我们南开,要统一穿军服,记得是浅绿色海军式制服,胸前是两排纽扣,海军帽,下肢却是打裹腿。派来的教练是正式军官,连长级,有文化水平,南方人,身着呢子军服,佩着军刀,脚蹬马靴,相当神气——这还是政府派来的,与二十九军不是一回事。
这时,军训课还限于做“操”,如行、跑、“跪”(这是一种命令口号)……种种集体动作。学生们非常认真,精神奕奕,军官为了显示成绩,命学生队伍出校上街,一声口号,行止整齐,严明之至!老百姓群立观看,那军官见“威重令行”,面上现出得意的神情。
还记得一位连长有一次唤我去为他写字——进他办公室,方知是为他小楷抄写工作报告。
过了一个时期,命令传来,要集中军训了。大家又都兴奋起来,因这与在校大大不同了,又有点担心,又很好奇,等待崭新的生活方式和“滋味”。
这回,可算“入伍”了,不只是校内“操场”的一门“课”了。
入伍什么样子呢?听我粗述梗概——
第一,学生们的“洋式分头”不得留,一律剃光!
须知,这群十六七岁的小青年,从未见过自己的与同学的“光葫芦瓢”,此时互视和用镜子自照,不禁同发一笑:原来“本相”如此!哈哈哈……
第二,发了军装,粗灰布单衣,有皮带。这并非“定做”,是真二十九军的兵服,调来让分给学生,各挑其合身的穿着,立即乔装改扮。
第三,发了步枪,每人负责这一新武器。只不发给子弹。那旧式老步枪,入手沉重得很,恐怕若是初中的同学会“承受”不了。
就这样,军训营在韩柳墅立起来了。最高长官是位营长,下面若干位连长、班长,各司一职。这些都是从二十九军精选调来的,他们身材高矮不一,面容各异,风度也各自不同,有严肃,有和蔼,有幽默……但对待学生却是一致的:爱护,训而不厉,教而不峻,知道这不过是一群青年学生,与旧时的“当兵的”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