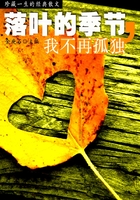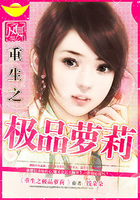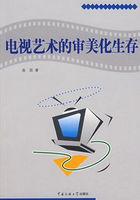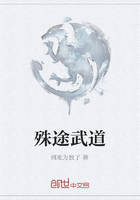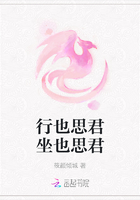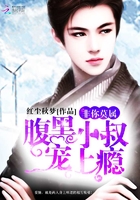因此我名居第二。得的奖品是个二号小银盾,而人家头名的银盾大多了,很神气。这回却有点“在乎”,心里不大是滋味——只因那大银盾太可羡。
平生失利,只此两例。
还有一例,但那与课业优劣无关。说来十分可笑:小学毕业后筹划升中学时,家计紧张,堂侄周大惠(字慕侨)在铁路局做职员,就介绍报考局办的扶轮中学。
我到考场一看,校舍、环境,与考的男女学生(大多数是同事员工的子女)等,印象俱甚可喜。第一天上午考得还是很“得意”。场后就发给了很丰富的食品,其中一个很大的高级面包,我这村童吃来甚为甜美可口。饱食之后,忘了这就是人家给的午餐,不多时即开考下一场。可我却迷里迷糊,走回旅店去和送考的四哥(祜昌)述说头场的“得意”。等我走回校,寂无一人!有点惊讶,推开考场门,见满室鸦雀无声在执笔答卷。主考者迎上来说:“你迟到了,不能再入场。”
这个“打击”不小。这回我未“泥金报捷”、“衣锦还乡”,灰溜溜地打道回家了。
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算不得。
其实,我的“光荣考史”倒是笔不胜书的。今只举一例,聊见“英雄”当年之“勇”——
那是1936年日寇炮击南开,学校封闭,我失学一年;隔一年为1938年,为了升大学,必须找个可以插“高三”的学校,接受这样插班的很难找,而且又想找不受日本势力影响的地方——于是寻得了天津工商学院的附中,是法国天主教会所办,故此日伪只能让它添一名日语教员,其他不能干涉。
这回热情送考的是我表叔。我进了考场,他站在校园一个双杠旁等候。
不一时,我轻轻松松地拿着笔墨出来了。他一见,面现惊愕,几乎“失色”——说:“怎么……怎么你不考了?”我答:“答完交卷了!”
他的面部表情立刻转了一百八十度,喜笑颜开!说:“没见这么快的!……”
此后,他逢人便“描述”当时我从容出场、他几乎“吓坏”的情景。
我自幼最不怕考,可谓身经百战,每战必胜。
诗曰:
聪明难得也难凭,自有灵机管浊清。
年少人人夸俊秀,不知人海有人英。
舞文弄墨
我“命中注定”不是飞黄腾达之人,定是一名文士书生。其“征兆”之一端就是从小喜欢“弄笔”为文。为文之际,还代人“捉刀”。
作诗填词要另谈,此处只讲一个“文”字。最早的“捉刀”之例是某乡古庙久荒,殿宇将颓,热心者为保存古建筑筹划修葺,这要有一篇“募化”的启事文。那位先生先是找了一个本地“能文”者作了一篇,不太满意,来求父亲。父亲对修庙不“内行”,为文感到语意空泛,有点为难。于是我就斗胆代笔。结果颇受鼓舞,以为比那已有的简陋不成文的启事稿好多了,既有辞藻,也能打动人的情怀。
一位设塾课徒的刘先生见了,甚加称赞,但他提出一个疑问:开头叙中华寺庙的起源时,用了一个“鼻初”的词语,说从未见过,担心不太妥当。我当时的理由是鼻字本有“始”义,故人称最早的祖先叫作“鼻祖”(似乎古谓人在胎中,最先成形的是鼻子)。如此,鼻初即最早的萌芽,怎么不可以?
“捉刀”之例也替父亲作过亲友间的挽诗,早不记得其词句了。到燕京大学时,我读西语系,却不知缘何有了“文名”。一次,名教授张东荪先生受友人之嘱托,要为一部书法史制序,张先生很为难,因为对书法并无研究,只讲哲学。于是想找个代笔人。其时整个燕园无法寻到能担承者。哲学系的吴允曾兄[9]就来找我。我应命交卷。
张先生很高兴,因素不相识,仍由吴兄做伴,邀一晚餐为谢。(记得我初到张先生家只有王钟翰先生在座,他是邓之诚先生的高足。)
再有就是不止一次为张伯驹先生代笔了,有七律,有信札。记得郭沫若贬《兰亭序》为伪迹时,张先生非常反对,定要上书与周总理,命我代笔撰呈函。我也作了,但心知这根本无用——周总理如何能管得了这样的奇事?
至于不属代笔捉刀的自己为文之例,也举二三,以存雪鸿爪迹,彩“豹”斑痕——
我还在初中之时,年只有十六岁,每逢星期日,二哥必来探看,因星期日可以不请假而出校,故偶尔相伴到附近走走。一次,在学校西侧隔马路不太远,忽发现一处鹿苑,空场中养着不少梅花鹿,有大有小,十分可爱。问知此乃乐仁堂老药店乐家的地方,养鹿专为取茸取角以为珍贵药材。二人观赏半日,不忍离开。
随后,二哥忽萌一念,可以说是本无可能的“妄想”。原来,我家一位老表亲刘子登,在吉林经营木行,他有一年慨赠爷叔(我父亲)一对鹿,养在我们小院里的西北角上木栏里。那鹿是用巨大木笼运来。因他只买到雄梅花鹿,配了一只不相称的高大的母麋鹿,而且在路上伤了后腿,成了瘸子——这不成“对”的夫妻无法生养小鹿。二哥的奇想是:向乐家主人洽商要一只小母鹿,不知能成与否。反正不成也无妨,他就让我写信去“撞”一回试试。
于是我得到了“弄文”的机会,依嘱写好付邮。
这本来是“异想天开”的事,也未敢真抱什么希望。谁知,乐家主人对一名初中学生的如此一份不情之请,竟然很快回信,慨然愿赠小鹿,嘱派人前去领取。
二哥高兴极了,马上信函报告与父亲。这一新闻性消息在敝乡传为罕闻的盛事佳话。
幼年往事,尚非真正本领;等到升高中,直到入大学,因家境不丰,难支费用,皆是靠成绩及一份奖学金申请书来办大事。
我的年级,不算小学的多次停课耽误,单说中学,本应是1937年毕业生,只因日寇侵扰,我到1939年方得投考燕京大学,次年入学,文学院院长是周学章先生,批准了“全免”的奖学金数额。抗战胜利后,1947年才又以“插班”身份再次考入燕大。这次入学,则周院长早已作古——我回燕大,先是向他夫人联系寻求协助的。重到燕大时文学院院长是梅贻宝先生(巧极了,周、梅二公皆津沽人也)。手续逐一办毕后,方见院长,呈上各种单据、选修课表请审核签字(方能交注册课,算是正式入学,否则无效)。我见梅院长时,他问了我两句话,用眼打量我,似有所思,然后签了字,我致谢而退。
以后,有同学张光裕兄者,为梅先生做助理工作,一见我,必然先说:“梅院长夸你是个才子!”我问梅先生从未看过我的文字呀!他说:“梅先生说你的申请书写得最好,怎么说没见过你的文笔?”
此言张兄特别津津乐道,仅是向我重复讲说,就不止再三了。
那时的文字,仍很幼稚,但能获梅先生的青鉴,却感很大光荣,至今难忘。
诗曰:
书生弄笔似寻常,奖学年年赖主张。
更有奇情兼盛事,梅花乞鹿乐仁堂。
“红学”之起步
人们见了我,最常发的一问就是你怎么走上了“红学”的道路?
既然大家对此话题颇欲一闻其来由缘故,我也不厌其烦地向他们陈说一遍,详略虽殊,事情粗具——大家的好奇心让我也深感这原来不是一件“小事”。
我治“红学”,既有很大的偶然性,又有深刻的必然性。两者相交,适成一种历史文化万象中之一象。
先说“偶然性”。
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真正关系之微妙难以尽究,最是耐人寻味了。比如说,我的“红学”开端是由于发现了胡适先生久寻无获的《懋斋诗钞》,这是很大的偶然性现象;但我不到燕京大学,怎能在那无比丰富的图书馆去发现它?这就又要问:我单单到燕大去读书,这是偶然性还是必然性?——这下子,就又牵扯到日军破坏我的南开中学母校与他们复又破坏我的燕大母校的侵华、抗日的无穷历史因由事故交织而成的特殊事相而“降临”到我身上的这段“传奇故事”了。
一切事情,细想起来,都包含着“万层”因缘,“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确实如此。你与某人某事无缘,就是近已“交臂”,也会毫不相干,连“失之”也谈不上,因为根本不发生“交臂失之”的那一要求与理念。而“缘”,又该如何作出“科学解说”?我至今还是极盼有人能开我茅塞。
因此我以为,假使我不入燕大,不曾发现《懋斋诗钞》,迟早我也“必然”以另外的方式去投入“红学”的研究。
这个“必然”何在?在于:一、我向学慕学,天生有“研究癖”;二、我自幼受母教,长大些受兄长启迪,爱文学,喜小说,初中高中时期已与《红楼梦》结下不浅的因缘——在高中时与同窗黄裳天天大谈《红楼梦》,我说我课余下功夫学英文是要将《红楼梦》译为外文,向世界介绍(如林语堂之译《浮生六记》);并且还说:我要创造一个新英文字:Redology——“红学”。
你看:我的“红学之路”是早就“走定”了,到燕大的后话,不过是一种“继续”或“发展”罢了。
如今且说《懋斋诗钞》。
如果把发现此书一事孤立起来看待,那就很偶然——也太简单了。
苦度八年抗战之后,1947年之秋于百般艰难曲折中重返燕园以续未完之学业。其时家四兄祜昌仕途蹇顿,失业家居,寂寞无聊中,以一部“亚东”版《红楼梦》(借到的旧书)遣闷。他读卷首的胡适的考证文章,引发了对雪芹其人的仰慕之情,见胡先生寻得敦诚的《四松堂集》,而敦敏的《懋斋诗钞》竟不可得,深以为憾,就写信来嘱我留意此书的踪影。
我接信后,几乎是立刻,即直入图书馆,去查卡片柜。
使我惊喜,此书竟在!
燕大图书馆好极了,只填一个小借书单,馆员用“吊篮”传送到楼上书库,不一会儿,“篮子”下来,书在其中!把借书证备妥,附在书的存卡上,签了名(或“学号”),就能抱回宿舍任情翻阅。我在馆中借书何止千部,未见老馆员有一丝嫌烦的表情。我至今感念他们。
此刻要说的有三点——
第一,记得原书卡上是空白,这多年来没有一人曾借过此书,一奇也。第二,粗读一过,就看见有六首诗是明文咏及曹雪芹的(敦诚的《四松堂集》,只有三首涉芹诗)。第三,这是清缮本,字迹工整,而由于此本的发现方又引出了原稿本的出世(今归国家图书馆收藏)。
如果你问:发现这么一本薄薄的小诗集,到底有何意义?
答复是:这标志了“红学”自1921年正式开端以后(约二十五年之久)的重新起步,也记录了“曹学”的一大进展。意义十分重大。
这句话是五十年后回顾学术史而得出的客观结论,不带任何主观夸张的色彩。
发现之后,我草写了一篇不太长的介绍考论的文稿,就放在宿舍书桌左肘处一堆书物的中间,心中并无多想,除去完成家兄所嘱的任务之外,即无他念——当时不要说什么“名利思想”、“轰动效应”之类,就连发表的意愿也不曾萌生。
隔了很久,燕大未遭日军封禁之前即在校任教的顾随先生,一次来信忽然提道:“你课余是否也可练习撰作文稿,如有,可代介绍发表。”
我即将久存“肘旁”的两篇小文寄与了顾师:一为考辨《皇甫君碑》并非欧阳询的“少作”,相反,正是晚期的杰作与奇迹。另一篇即此敦敏诗集中咏芹诗的介绍,题目将主眼放到了生卒年考订的方面。此二稿,顾先生交付与赵万里[10]先生,他正主编一家报纸的“图书”副刊版。
赵先生一见拙稿,立即编发了后一篇,而对考欧书的一篇置之弗顾。
文章刊出了,引起众多人的瞩目。在随后的第二期上,即又登出了胡适先生给我的一封短信。
胡先生的来信,是赵先生转给我的,我接到时他早已将此信札全文编发了。这当然引起了更大的影响。
我的“红学”起步,暂记到此,后文下回分解。且附记二事:一是我问邓之诚先生是否知有此诗集,他说:“我早知道;胡适早就来问过我。因我不喜欢他——已成‘半个洋人’了——我没告诉他。”此诚秘闻也。
其二是燕大藏本后为哈佛大学调去,遂藏在彼。今影印者乃原北图(今国家图书馆)之藏本也。
诗曰:
残编一卷懋斋存,母教兄言忆旧恩。
难忘师情群辐辏,百川归海大文源。
我与“红楼”有夙缘
我家与姥姥家都是“海下”养船的人家,母亲姓李,纯粹旧时家庭妇女,没有名字。母亲为独生女,当时她还没有赶上有“女学校”的时代,自幼深慕读书的堂兄弟们,偷听他们念书的声音,能仿效当时学生朗诵唐诗圣杜甫的五言律诗的声调——北方特色的抑扬顿挫的“美读”法。她因此发奋自学,竟能阅读一般的小说、唱本,也能学戏台上的唱腔。一句话,她是个酷爱文学艺术的村女。
重要的是,她有一部《红楼梦》。
奇怪的是,她的这部书(还叫《石头记》的版本)竟是日本版!
我第一次看《红楼梦》,就是看母亲的《石头记》。
怎么是日本版?原来,这书是她的堂兄(我的大舅)在她出阁之后前来看她时,给她带来的礼物。那是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母亲年方二十。那书后面印着“明治三十八年一月十三日”,绿色布面精装上下两册,带批语,绣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