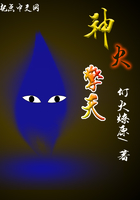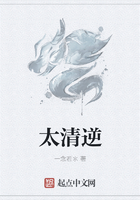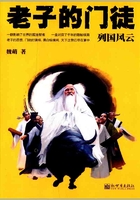最后一次见到幺爸是在春节以后,也算是有生以来第二次去给幺爸拜年了。以前,都因忙于学业忙于工作,很少去幺爸家,或者也只把幺爸家作为歇脚换马的一个驿站罢了。
幺爸家住在新都三河场,距成都新都两地都不过二十来里路。离人们熟知的《死水微澜》里的天回镇,那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幺爸其实并不是川西坝子里的人,是帮人帮去的,也算是万恶旧社会的一个产物吧!幺爸虽然是外来户,但人缘关系极好,在当地可受人们的尊重了。不管粘亲不粘亲,不管大人孩子,人们都习惯叫他涂幺爸。只要你到三河场,一提起涂幺爸,没有哪个不知道的。幺爸在这里不但受人尊敬,而且还很有威望的。自从成立人民公社,幺爸就在这里当生产队长,一直当到人民公社解体。不管怎么改选,人们就是信得过他,每次总是非他莫属。
虽然我们这个姓氏的人本来就是客居他乡的客家人,居无定所,世世代代过着游牧民族的生活,甚至有人称客家人为中国的吉普赛人。从湖广填四川开始,我们的家族才陆陆续续从遥远的广东湖南湖北,沿着滔滔的长江朔江而上,来到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
其实我们涂姓人家的祖籍一说在山西省榆次西南的涂水,在水一方;一说在安徽怀远东南一带的塗山,靠山吃山。不过这都是远古的传说罢了。时过境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谁也很难说清楚的了。
作为我们后辈人,最多也不过知道上头那么两三辈人的事。我只知道在我们县城大西街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涂家祠堂,那是涂氏家族聚居的地方。由于最近一二十年的旧城改造,涂家祠堂和其他古城街道一样在劫难逃。
在万恶的旧社会,我们这些穷家小户,帮长年,打短工,就像月亮搬家一样,今天从这里搬到那里,明天又从那里搬到这里。听前辈人说,我们家从县城搬到南山鼎锅湾,不知道搬了多少次,最后才在半边山向家沟居住下来。
民国十三年,我的阿婆涂廖氏丢下五岁的太爸(也就是我的父亲)两岁的幺爸和苦命的阿公撒手西去,苦难从此就降临到了我的家。那时,阿公忙于养家糊口,四处奔波,疲于奔命。抬滑杆挑加班帮长年打短工,挣钱养家糊口。在无法照看年幼孩子的情况下,阿公只好把太爸幺爸寄放在漆家坝的妹妹许涂氏家里。
日子在苦难中过去,孩子在一天天长大。阿公从妹妹家也就是我的姑婆家接出太爸,来到金堂云顶山帮人。那时,幺爸还小,做不了体力活,就只好继续留在姑婆家。姑婆带有一儿一女,女儿比幺爸小八岁,从小在一起长大,感情甚好,也可谓青梅竹马了。
阿公和太爸农忙时,就去给有钱人家栽秧点麦栽红薯收麦子打谷子什么的;农闲时,就去帮人挑加班抬滑杆抬轿子什么的。好不容易攒下两个钱,阿公就忙着给太爸张罗婚事。
那时,娶儿媳嫁女子讲究媒妁之言父母之命郎才女貌门当户对的,经人说媒,太爸找到了咩咩(客家人对母亲的一种称呼),也就是我的母亲。母亲家里也是八代贫雇农,在母亲还没有记事时,我的外婆就化着一阵清风到封神台去了。一个外公拉扯着三个女儿艰难度日,好不容易等待着女儿长大成人。可是,母亲八字歪,四柱里面就占三个虎。人们常说,女人属虎,有克夫克子之命。咩咩就像《骆驼祥子》里面的虎妞一样,过了婚龄还没有嫁出去。
母亲结婚过门后,一个家才真正像个家的样子。虽然租住着地主向理洲家的茅草房子,一到逢年过节一家人总可以团聚在一起了,总算还有那么一点点家庭的气氛。
时间一长,叔嫂之间不可避免会发生一些矛盾。一次,家里替地主向理洲喂的牛找不着了。对于一个佃户来说,丢了牛,这可不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小事。气得母亲狠狠地把幺爸骂了一顿,因为牛是幺爸去放的。幺爸感到责任重大,家门都不敢回,吓得只好一走了之。
这一走,幺爸的命运随之发生了改变。幺爸只身来到金堂云顶山,找到在那里帮长年的阿公。阿公想到既然孩子有十五六岁了,也可以出来闯荡闯荡世界了。就给主人家说,先让幺爸给他们家当放牛娃儿。
慢慢地,幺爸在外面见的世面多了,人也混熟了,心儿也就变得野了起来。他不安心成天放牛割草的日子,觉得太枯燥太乏味了。他翻过龙泉山,沿着青石板铺就的古栈道一路向西,进入了成都平原。看到这一马平川,幺爸可乐坏了。自己的家乡,那连绵起伏的丘陵,真正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别的不说,在这川西坝子了,走步路也要平坦得多啊!
来到距成都二十来里的三河场,幺爸找到一户大户人家,说,只要一天给他三顿饭吃,什么样的活儿他都可以干。这大户人家,看到幺爸长得高高大大,眉清目秀,干活儿也挺勤快的,不久,就把他作为长年对待了。
在这里一干就是十几年,眼看就要土改了。是回老家,还是留在三河场,幺爸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幺爸在这里分到了土地,还有两间茅草房子,终于在三河场也算有个家了。
那时,幺爸已经是而立之年的人了,早过了结婚的年龄。阿公非常着急,托人去跟姑婆商量,是不是来个亲上加亲,把她的女子说给了幺爸。姑婆满口答应下来这门亲事,毕竟幺爸是姑婆一手带大的,什么脾气品性,姑婆是了如指掌的。
真正见到幺爸,还是在我穿开裆裤的时候。那时,幺爸带着他的大女儿,来到老家,看望年迈的阿公。一次,幺爸用箩筐一头挑着堂妹,一头挑着我,去半边山赶场。看着漫山遍野的菜花和绿油油的麦苗,我和堂妹就像呢喃的春燕,叽叽喳喳快乐地穿行在乡间小道上。在街上,幺爸给我们买上糖果燥花生燥胡豆什么的,乐得我们什么似的。
阿公去世前后,幺爸推着鸡公车回到了老家。从三河场到老家,大约有一百七八十里路程。那时,虽然有唐巴公路,一天有一趟成都到中江县城的对开客车。但那时人们手头没有几个钱,哪里舍得坐汽车,到哪里去差不多都是步行。哪怕是挑着百十斤重的担子,也是如此。从三河场鸡叫头遍就得起身赶路,翻山越岭,过赵家渡,爬龙泉山脉的主峰三河庙,要到天黑了才能到家。那时生活紧张,在路上,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只有靠米糠馍馍充饥。黄昏,大路上传来了鸡公车(独轮车)叽咕叽咕的声音。不用问,我就知道幺爸回来了。因为,在我的家乡,除了肩挑背抗,是没有鸡公车的。
我急忙出朝门,朝田坝里跑去,迎接幺爸的到来。幺爸从鸡公车上取下一个用手巾包着的包裹从里面拿出一个馍馍,说,阿木,幺爸没有什么给你的,只有这个馍馍。我高兴地叫了一声幺爸,接过馍馍。馍馍虽然是用米糠做的,但这是我第一次吃糠馍馍,觉得很稀奇。虽然很粗涩,我吃得还是蛮香的呢!
许多年后,春节一过,哥哥就要结婚了,幺爸提前来到我家帮忙张罗筹办哥哥的婚事。那时,我还是黑湾小学的一名小学生。寒假还没有结束,也正是孩子们玩耍的时候。
父母亲第一次结儿媳妇,总希望把他办得热热闹闹风风光光的。七大姑八大姨远亲近临,坐拢来也有那么十几桌。
酒宴之前的准备工作可忙碌了,所需的酱油墨醋时兴菜蔬在乡场上是很难买齐的。要想办齐备,只有进县城才能买到。这样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幺爸的身上。
那天一大早,幺爸带上我,朝县城进发。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县城,自然觉得很新奇,心情也非常激动。在路上,幺爸交待我,他去买菜,我就在原地看好箩篼,别叫人家把买的东西拿走了。三十多里乡间小路的确很漫长,过染房新拱桥三百梯水拱桥南耙沟,好不容易才来到南渡口。
对三百梯这个我们进城的必经之路,在民间有很多传说。她也不过是人们常见的上山下山的石头阶梯罢了,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有的人一生经常路过这里,但从来也没有把这里的石梯数清楚过。不管你怎么数,到头来,不是多那么一两梯,就是少那么三四梯。我想她的妙趣也就在这里了。
一爬上南渡山岭,一条大河就展现在我的眼前。空旷的原野上,凯江河和御马河浩浩荡荡环城而流,古老的县城就位于两河之间;南北二塔就像两根划船的桨,远远望去,古老的县城就像一条船儿一样,正在乘风破浪奋勇向前。
这座县城自三国时期建县以来,已经有一千七八百年的历史。城墙高筑,四座城门巍然矗立。最惹人注目的还是县委的五层大楼,是大跃进年代的产物。她是全城的最高建筑,就像一座古堡矗立在一片青砖灰瓦之中。
来到南渡口码头,只见凯江河波涛汹涌,白浪滔天。这是进县城的必由之路。不管人畜,还是车辆,一律得乘渡船才能过河。渡口的河面上,有用人拉纤的渡船,有能坐三四个人的小鳅子船,还有船头站着鱼鹰打鱼的乌蓬船
来到珠市街,幺爸把箩篼放在街沿上,就到附近的菜市场买菜去了。我坐在箩篼旁,看着熙熙攘攘赶场的人们,一动也不敢动。等了大半天,幺爸好不容易才把所需的菜蔬买齐。
我跟着幺爸的担子,朝回家的方向走去。走出龙王阁,路边上摆着一捆捆甘蔗。我看着甘蔗发愣,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幺爸明白我的心思,就把担子放了下来。他左选右挑,抽出一根又大又红的甘蔗。我高兴极了,这是我最喜欢的食物。农村出生的孩子,上街只要能得到大人们的一捧花生胡豆,一根油条或甘蔗什么的,那可是再高兴不过的事了。
甘蔗摊子的侧边,有一个买针头线脑和小百货摊子。我看见摊子上的小刀,拿在手里把玩,久久不愿意放下。心想,要是有一把小刀该多好啊!叔侄之间,好像心灵相通似的。幺爸二话没说,向摊主问明价格,用五角钱为我买下了这把我心爱的小刀。许多年过去了,这把小刀还挂在我的钥匙链上,一看见这把小刀,我就想起和幺爸第一次进城的情景。
当我的表姐在哥哥的婚礼上第一次见到我的幺爸,她悄悄地告诉我,这个人怎么长得跟周恩来一个模样。我想了想,觉得幺爸跟周恩来确实有点挂像。高高的个子,有棱有角的五官,为人处事也是那么的谦和。不管咋说,从小幺爸就在我的心目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北京读大学期间,不管来去,我都要到幺爸家去。一到幺爸家,他对我比对他的亲生儿子还要好。除了一天三顿好酒好菜招待,还经常陪我逛新都宝光寺桂湖公园,到三河场茶馆喝茶,到菜市场买菜,送我到成都火车站上火车。一次,我的一位大学老师让我在四川帮他带一床竹编凉席。我把这事告诉幺爸后,他又陪我到天回镇去购买。我们从街头走到街尾,走了一个铺子又一个铺子,终于挑到了一床做工精细的凉席。
幺爸虽然在三河场呆了几十年,他始终没有忘记生他养他的故乡。而且,还经常带着他的儿女常回老家走走看看。有一次,堂妹用刚买来的自行车搭着幺爸回老家,路过我的大姐家。看到前面的道路没法再骑,顺便就把自行车放在大姐家里,就回老家去了。
幺爸每次回家,总是带着见面礼。这家两捆面,那家一封糖果。当然,最忘不了给爱抽烟的太爸带上那么一两捆用化肥浇灌出来的川西坝子里出产的叶子烟。这叶子烟灰白接火劲大,抽起来过瘾,还有止咳化痰的功效。这,太爸自然是喜欢的了。
第二天一大早,大姐夫就赶来报信,说,他们家失火了,堂妹的自行车也被烧得面目全非。在当时,自行车还非常的稀少,一般家庭还买不起自行车的。这辆自行车,还是堂妹的男朋友给她的订婚礼物。堂妹心痛得什么似的,但又不好说什么。毕竟是自己放在这里的,哪个知道会遇到这样的灾难呢!幺爸说,没关系的,自行车烧就烧了,只要没有伤着人就再好不过了。幺爸挂口没有说什么,还不断地安慰着大姐夫。
最难忘是最后一次见到幺爸的情景。那次去给幺爸拜年,走到幺爸家。一进门,我就看到幺爸躺在床上,不停地咳嗽。幺爸听说我来了,慢慢地从床上爬起来,披着棉大衣,陪我来到朱家茶馆喝茶摆龙门阵。我看到幺爸消瘦了很多,精神也不是很好,嘴唇发紫,还不时地咳着嗽。我的心里好像有那么一点点不祥的预感。
时隔不久,也就是阴历二月中旬吧。一天晚上,突然接到堂弟打来的电话,说幺爸过世了,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
我约上我的哥哥和侄儿,第二天赶到了三河场。一进门,看到院子里摆满了花圈祭帐,到处坐满了来吊唁的亲朋乡邻。堂兄堂妹及堂侄儿女们个个跪在幺爸的灵位前,在做道场的道士的指挥下不停地烧香磕头。
最令我感动的是,我的堂侄儿,也就是幺爸唯一的还不满七岁的小孙子,戴着重孝,跪在幺爸的灵位前,哭得泪人儿似的。听堂弟说,在世时,幺爸最痛爱这个小孙子,在小孙子身上,他看到了涂家的希望;但堂侄儿也最懂事,在幺爸病重时,经常到他的病床边端茶倒水,时刻记挂着他的阿公。
丧礼很风光,送葬的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人们用花轿抬着幺爸的骨灰盒,吹鼓手们吹吹打打,时而吹着哀伤的曲调,时而奏着欢快的乐曲,沿着三河场的大街小巷,向二台子幺爸的陵墓进发。